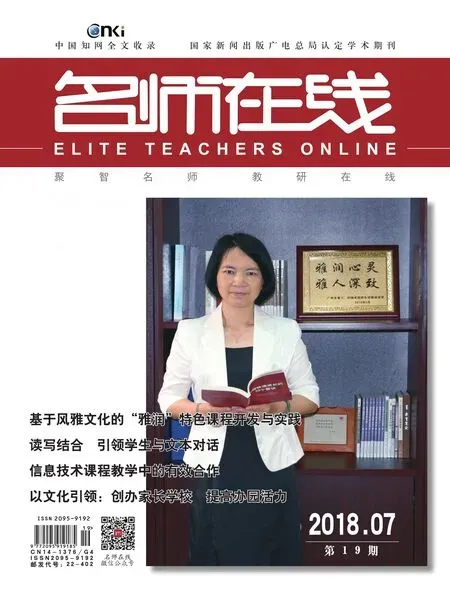多維切入 讓文本解讀回歸應然質態
王益蘭
(江蘇省南通市通州區興仁橫港學校,江蘇南通 226300)
引 言
注重切入式文本解讀,就是要試圖改變傳統教學中過度關注教師之教而忽略學生之學的弊端,切實地將學生這一教學主體落到實處,始終將學生的能力發展作為出發點,為挖掘全新的文本解讀之路奠定基礎[1]。
一、據點發散,在品析核心語詞中切入文本
詞句是文本構成的基礎單位,是閱讀教學中需要關注的主要范疇,創作者往往將核心要旨和價值意蘊就埋藏在文本的詞句之中,借助核心語詞展露自己的心境、抒發自己的情思。很多核心的關鍵性詞句起著重要的作用,這為學生深入解讀文本、設置合理的教學板塊提供必要的支撐。文本解讀就不能置這種核心詞句于不顧,而要緊緊依托課文中的人文環境和表達情境,深入體悟這些核心詞語所承載的價值。
如《祁黃羊》一文,作者借助祁黃羊兩次分別舉薦自己的殺父仇人解狐和親生兒子祁午繼任中軍尉的典型事例,刻畫了一個“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的形象。整篇文本借助祁黃羊和晉悼公之間的對話展開,尤其是人物對話過程中的提示語的選用,更加為凸顯人物形象增色不少。但在文本解讀過程中,不少學生就提出質疑:“祁黃羊為什么不先舉薦自己的兒子,而要先舉薦解狐呢?是不是他已經預算到解狐身患重病無法擔任,才故意推薦的,是為自己合理地推薦自己的兒子打基礎的?祁黃羊的這種做法顯然達到了名利雙收的效果。”學生的這種質疑雖然與課文中人物形象的定位背道而馳,但并不是毫無道理。面對這種質疑,盡管教師百般解釋,但仍舊顯得缺乏說服力,學生也沒有買老師的賬。該怎樣撥亂反正呢?教師引導學生從原生態的文本入手,引導他們細致閱讀“推薦解狐”這一部分中的語句,緊扣提示語中的“慎重”“壓根兒”“擔此重任”等核心詞語,感受祁黃羊推薦過程中的嚴謹與慎重;并讓他們意識到中軍尉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性。如果胡亂推薦,自己的家人也會受到牽連。從而感受到祁黃羊是本著對國家、對家人負責的態度推薦的,而并非是一己私心。沿著這種方向的拓展切入,學生才能從語言之源逐漸生發對文本人物的敬仰之情。
二、浸潤意識,在置換“標簽”中切入文本
2011版《語文課程標準》再次強調指出:語文課程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這就意味著語文教學既要在扎實的語用訓練中讓學生掌握運用語言文字的技巧,也要在這一過程中汲取、體悟語言所蘊藏的價值情韻,實現言意兼得的雙重功效[2]。但綜觀當下課堂,很多情感的體悟和道理的悅納不僅停留在說教的膚淺層面,更為遺憾的是教師將言語實踐與人文體悟一度割裂開來,兩者失去了關聯,文本解讀的真正效益并沒有得到彰顯。
如在教學《九色鹿》之初,學生初步閱讀了課文,對課文的內容和中心思想還沒有形成有效的認知,教師就匆匆要求學生提煉九色鹿、調達、國王和王后的人物形象。早已經司空見慣的四年級學生也已心領神會,分別冠之以“善良美麗、背信棄義、知錯就改、愛慕虛榮”的標簽。課堂教學的最后,很多教師還不忘借助“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做人不要……而要……”的句式,對學生進行一番道德綁架式的教育。深入反思,會發現教師雖然說得頭頭是道,但這種文本故事的內蘊真的被學生悅納了嗎?他們除了附和別人的概念認知外,內心究竟存留了多少有價值的東西呢?這些學生看似學懂的地方其實際效果并不明顯。鑒于此,筆者在執教時,則引領學生緊密聯系課文,對比調達的誓言與后來的言行,并結合皇榜探尋這種巨大變化背后的利益因素——即被皇榜中的利益所吸引,最終引領學生思考:我們從調達的言行中獲得怎樣的啟示?從而將文本中的故事遷移到學生真正的意識中去,起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三、洞察關聯,在深究文眼中切入文本
文本創作過程中,作者為了凸顯文本的價值意蘊,往往會設置體現文本核心的文眼,將整個文本的內在核心支撐起來。因此,在引領學生進行文本解讀的時候,教師可以借助這一文本內容的文眼深入體悟,從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如在教學《螳螂捕蟬》一文時,很多教師喜歡按部就班地展開教學。這種教學方式并沒有真正緊扣文本的表達核心,也沒有能夠真正理清兩個故事之間的內在聯系。課文中所蘊含的“利益”與“禍患”之間的關聯沒有能夠真正地讀通讀透,也就再正常不過了。而筆者在教學這篇課文時,引導學生彼此對應兩個故事之間的共性,從而思考:如此顯而易見的危險,它們為什么就看不出來呢?教師借助這一問題,要求學生結合課文中的核心詞語去真實品味與感受。
正是在筆者對文本文眼準確的捕捉與研讀下,學生對于文本的解讀脫離了按部就班的僵硬痕跡,不僅探尋出了兩個故事之間暗存的邏輯關聯,更激發了學生的探究熱情,提升了課堂教學的整體效益。
四、轉換視角,在探尋因果中切入文本
教師在嘗試文本的解讀時,可以積極轉換視角,從不同的側面和維度探尋文本故事中前后的因果關系,從而真正切入文本,實現文本解讀的立體化效果。例如,在教學《三顧茅廬》一文時,不少教師都在學生初讀課文之后,就引領他們率先提煉出劉備“求賢若渴”的核心形象,而后再讓他們套著“求賢若渴”的現成答案,從文本表達的細節入手尋求印證。這種做法司空見慣,但無法真正激發學生的探究動力。因此,筆者在教學中嘗試著變換思路,將整篇故事放置在文本時代背景下,引領學生探究故事發展的前因后果,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筆者首先通過敘述,讓學生明白在那樣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每個君主都想得到像諸葛亮這樣的人才;繼而深入思考:為什么其他君主都沒有能夠得到諸葛亮,而單單劉備能夠取得成功呢?劉備究竟是憑什么獲得諸葛亮認可的呢?帶著這一問題,學生再次深入文本,從訓斥張飛、下馬步行、快步走入等細節出發,形成劉備“求賢若渴”的整體印象。從故事發展前因后果的角度解讀文本,學生的認知思維才會得到真正的釋放,其學習的效果也可以得到明顯的提升。
五、圖文映照,在再現畫面中切入文本
借助教材中的插圖資源,引領學生探尋文字與圖片之間的內在聯系,是促進他們強化文本認知的重要方面。如在教學《第一次抱母親》時,筆者并沒有將教學的重點放置在對文本故事的體悟上,而是借助教材中的插圖資源悉心品味母子之間的濃濃深情。筆者首先要求學生觀察對比教材中的兩幅插圖,感受插圖中不同年齡段母親的巨大差異,一個年輕力壯,挑著重擔,盡管生活的壓力很大,但對生活充滿了希望;一個白發蒼蒼,臥在病床,其精神狀態也充滿了歲月的痕跡。
在這一案例中,教師正是緊扣教材中的插圖資源,引領學生從鮮活的畫面入手,逐漸深入到對生活畫面的探尋與感知上。如此的切入不僅簡捷有效,也為學生推敲文字、還原畫面和體悟真情創設了平臺、夯實了基點。
結 語
總而言之,閱讀教學務必要從文本自身的特質出發,智慧選擇、恰當取舍,才能探尋出最為適當的教學方法,讓語文教學回歸其應然質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