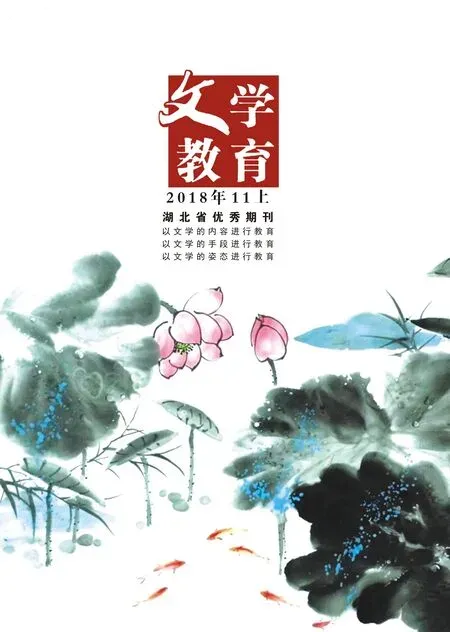變動不居:論臺灣新世代作家筆下的都市情境
劉偉云
“真正能夠把一個城市的那種魔力——我所謂的魔力,一方面是指怪誕的那種魔力,另外就是一種吸引人的欲望的魔力——這兩種混在一起的很少。”[1]122李歐梵研究中國都市文學時,指出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很少有小說能把都市書寫成一種心靈的、文化的、使人失落的迷宮,表現出這種迷宮的只有一九三〇年代劉吶鷗等代表的上海新感覺派。上海新感覺派創造了迷宮似的洋場文學,卻因戰時中國幻象似的繁華,不可能形成有序多元的現代都市圖景,而臺灣新世代小說家卻有了這樣一個舞臺。20世紀80年代的臺灣不僅意味著一個新的十年,更意味著一個新的社會和文化語境的形成,那就是媒體、資訊革命,以及快速成形的資本主義都市生活方式。政經、文化和科技各個領域表現出的變動經驗以一種不可抗拒的魔力吸引著新世代作家,這種魔力在新世代作家筆下演繹的是資訊網絡下的流動思維,是快速流轉的生活方式,也是涌動的欲望。
一.都市文化核心——流動的資訊思維
資訊社會最大的變化莫過于電腦的出現,作為資訊文明所在的城市的代名詞,電腦不只是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節奏,還帶來了資訊思考這一嶄新的意象和思維方式。陳思和評價臺灣新世代都市小說的特征時指出:“資訊結構是體現現代都市文學特征的主要標志”[2]347。新世代小說家所提倡的新都市文學是建構在一種新的思維基礎上的,不一定寫具體的都市景觀,而關注更多的是人在都市化語境中面對資訊紀元,對于自身以及世界新的思考方式。
處身于一個資訊無遠弗屆的都市社會,新世代小說家面對的不僅是一個復雜多變的網絡,還是這個資訊結構組成的人類生活的新結構與新關系,他們敏感到了后現代工業社會極速的資訊傳輸,時空與觀點快速跳動與切換的特點,自然選擇了新的觀察與思考方式,以資訊思維體現他們理解的都市文化,即終端機文化。這種文化使得都市中的人與物成了一個個零落的符號,并以流動的精密回路構筑了一個龐大未知的“迷宮”。林燿德的《一九四七·高砂百合》以發生在一九四七年臺灣的“二二八事件”為線索,打破了傳統線性的情節框架,運用時空、意象的快速跳換,在虛實之間展示了臺灣交織著西洋、日本、中國、二二八、阿泰雅族文化的混雜歷史;在張大春的《將軍碑》中,暮年的將軍不再指揮千軍萬馬,可是當回顧過去,一個個片段的組合,交織著過去與未來、虛構與現實的流動,記錄也是虛構了將軍的一生。資訊社會中全新的觀察角度與書寫,不僅呈現出非線性的、模糊虛實界線的特點,甚至是分裂式的流動思維特征,這種分裂式的流動思維在王幼華筆下表現得最典型。彭瑞金指出王幼華“所呈現的淆亂錯置、零碎而交雜的特性,很能映現作者內心紛雜而倒錯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作品中不斷以間歇性的方式,用自信、睿智而有譏諷性的語言、情節,慧黠而飄動的現實觀照展示他具思考、試探、智慧的特性。”[3]264王幼華的《花之亂流》講的是阿A在變成花的十五日前以錄音帶的形式講述的內心活動,從工作同事老黃到圣賢之道,從政治季節到地震,從拒絕人的靠近到語重心長的關懷,通過阿A的陳述我們看到,他的內心世界是破碎的,沒有中心的,正是這種分裂的、流動性的意識活動呈現了臺灣社會文化的變遷情境。而《都市之鼠》開篇講的是都市人如何處置老鼠的方法,然后直接跳換到一群藥品公司職員到海灘浴場的游玩。游玩過程中,有人發生溺水意外被救起,而后變成辦公室、媒體的話題。作品中,王幼華表達了即使是攸關生命的事情,在匆匆的都市生活中,最后除了變成制造新聞的談資,不會在人們的精神和記憶中留下任何的痕跡。
林燿德以“流動不居的變遷社會”定義這個迷宮式的都市,不僅呈現出臺灣都市文學具現代意義的宇宙思維寬度,同時顯示出了資訊社會中流動思維的輕盈風格。卡爾維諾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中關于盧克萊修的《物性論》以及奧維德的《變形記》的討論中指出,他們對世界的認識意味著對世界堅固性的融解,卡爾維諾在科學論述的啟發下尋找他心中的世界形象。面對臺灣都市社會崛起新出現的空間變化、政經亂象、資訊信息、消費文化、競爭人格等文化現象,一切都在快速流動,一樣面對著堅固性的融解,不同于盧克萊修引導人們注意無窮小、輕和游移的事物,也不同于相信任何事物都可以轉變成另一事物的奧維德,臺灣新世代小說家選擇了電腦思維,他們所踐行的正是在電腦科學論述幫助下的都市想象,從而探向都市文化的核心——終端機文化。也許電腦這種冷靜、跳躍的思維境界才能體現新世代小說家力圖表現人們在面對種種刺激時流動的、開放的思維特征。終端機、傳輸、符碼、亂碼、界面切換等等,影像的瞬時切換證明了多時空并列的可能;意象的跳接,時空的變換,虛實的交替,這種抽離現實時空的電腦思維美學,成了新世代小說家講述故事,鋪陳事件的法則,形構他們都市書寫新的美學特征。
二.非常的日常——流轉的生活情態
面對著一個活躍著少爺、姨太太、舞女、銀行家等都市人物,以及他們周旋于夜總會、電影院、咖啡廳、賽馬場等場所的都市情境,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等代表的新感覺派作家,他們將目光投向了物質生活豐富、聲色迷離的魔都上海,演繹了迥異于新文學主流形態的現代生活情態。1980年代臺灣的都市化,帶來的不僅是人口的快速流動,還有在高度消費社會中人的生活形態巨大的改變。新世代小說家延續新感覺派作家的現代特質,迎合電腦科學世界的資訊網絡,超越傳統的都市概念,以冷靜、流動、碎片化的都市思考,形成了流動性的開闊思維,在流轉變化中演繹他們非常的日常生活。
林燿曾德以“浪跡”形容臺灣的都市生活形態,表現都市生活的流動性,呈現了1980年代以來臺灣都市化進程中流轉變化人們的都市生活素描。在《大東區》里,林燿德描寫了一群生活在夜東區的年輕人,在物欲橫流的都市社會中追求鐳射光碟的旋轉、舞池的漩渦、性愛、飆車的刺激生活,試圖以快速流轉的生活方式彌合都市帶來的孤獨感以及人與人間的疏離感。在小說集《非常的日常》中,作者以日常生活的非常形式呈現了暴力、詭異、怪誕、荒謬的生活情態,其中的《龍泉街》講的是一對少年因互相看不慣相約決斗,他們義憤填膺,恨不得馬上一決高下,卻在目睹另一群人血肉橫飛的斗毆場面后斗志消失,頹然放棄決斗,最后戲謔的是,合抽一根煙感慨一起目睹的斗毆場面。龍泉街,白天是繁華的街道,晚上卻是不同族類用來斗毆的生命場,相約決斗的不良少年,互相廝殺的流氓,他們屬于自己的族類,互不干涉卻共同呈現了龍泉街的詭異的文化與風景,呈現出都市世界重疊的特征。
黃凡同樣寫出了都市化對于人們生活方式的沖擊,生活在大都市的人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新興事物的出現。在《東區連環泡》中,我們發現作者筆下不再有黃春明在《兩個油漆匠》和《溺死一只老貓》中表現出的對都市現實的無奈,而更多的是一種帶著喜感的戲謔,人們必須調整生活態度以適應“二十四小時快速餐廳”,“全天候電動玩具”還有夜色中“亮如白晝的廣場”,諷刺的是引起轟動的企圖跳樓者卻只是一個等待日出的觀光者。黃凡筆下這種帶著喜感的戲謔方式還表現在他的小說《到東區的500種方法》里。作品寫一個報社記者參加一個“改善生活品質座談會”卻陷入了不斷流動的交通陷阱中。途中見識了睡鋪巴士、直升機、滑翔翼、登山索具、屋頂快速道路甚至炮彈飛人等許多怪誕的交通名稱和方式,當他懊惱自己太遲到達會議現場時,卻發現他是最早一個到達的與會者。通過販賣地圖的小販口中得知,臺北已變成了世界有名的迷宮。黃凡以一個都市探險家的姿態反諷了臺灣交通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臺灣都市社會中許多不可思議的次文化現象,卻也反映出都市社會巨大的生命力。
林燿德的《大東區》、黃凡的《東區連環泡》等小說,將光明與黑暗,青春與死亡并置,將星際戰爭的抽象世界與防火梯旁的陰暗角落的具象世界共存,在他們的觀念里,只有以跳躍的快速變換的方式才能展現臺灣都市新區———大東區人類流轉的非常的日常生活情態。林燿德曾以《幻》描述人在都市中的活動:“人在都市,就像是馱載著螺殼的蝸牛,在長滿了符號、象征、暗示、密碼和圖騰的草原上,拉開一道繼繼繩繩的蝸篆,和他人的行蹤纏錯成一幅以虛無感為筆觸的抽象畫面。人是都市流動的文身。”[4]121這里的爬行的“蝸牛”象征的當然不是都市生活的節奏,以林燿德對都市“變動不居”的詮釋,或許象征的是人在都市中恒定的流動性存在,強調人在充滿速度、節奏和喧囂同時涌動著激情、力量和騷動的都市社會里的變遷流動。
三.都市之謎——流動的欲望
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不斷深化,帶來了經濟的富裕,也帶來了社會生活的現代化,一切都似乎成了可消費的景象:商品聚集的大型購物廣場,街道咖啡館,流動的汽車,巨型的熒幕,閃爍的霓虹燈……然而在景象的高潮之處,一種受壓抑的現實卻不和諧地出現了,“恰如伯曼所言:成為現代就是發現我們自己身處這樣的境況中,它允諾我們自己和這個世界去經歷冒險、強大、歡樂、成長和變化,但同時又可能摧毀我們所擁有的、所知道的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們卷入一個巨大的漩渦之中,那里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爭和矛盾,含混和痛楚。”[5]3-4這個漩渦就像都市之謎,讓人著迷卻又難以把握,人們在盡情消費現代景象及提升快樂中激發出了內心深處潛藏的欲望,處身其中,在欲望滿足的同時倍感迷失,無所依從。
在黃凡、林燿德合著的《解謎人》里,失去記憶的“趙達人”,從一無所知,到意識到自己是替罪羔羊——臺灣金融界最著名的經濟犯蔡新州,因保外就醫而被掉包,經過整容并被刪除了記憶。當忘記身份,蔡新州也曾想忘掉過去,做一個全新的公民,一切似乎重新開始。然而,在復雜的政經網絡中,他根本無法把握自己,就連自己最親密的女伴都是被安排在身邊的雙面間諜。猶如電影《楚門的世界》中,楚門面對的世界真實可感,有父母,朋友,愛人,表面的一切井然有序,卻都是虛假的電視劇劇情安排,一切都罩在一個巨幕下。當楚門發現真相,最后不顧一切,沖出了這個虛擬的世界。而《解謎人》中的蔡新州,因為失卻身份成了一個臺北的游人,開始了尋找自己身份的旅程,然而一系列戲劇性的跟蹤、謀殺、意外死亡使他忘記了身世謎團,一步步走向他人的安排里,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卷入了爾虞我詐的諸多事件中:臺灣奇跡背后潛藏著的仿冒、逃稅、走私、回扣等地下經濟,華揚國際投資公司,老鷹集團,美帝集團,可以無限透支的神秘賬戶,瑞士數億美金的信托基金,國際軍火生意,選舉,罷工,游行示威,臺北農民暴動……“我只感到自己被一股莫名的、恐怖的勢力所操縱,也許那是一只潛藏在我心底的魔鬼也說不定。”[6]227在權力與欲望中,即便失卻身份,這個魔鬼仍然如影隨行。當蔡新州“終于醒來”,才發現自己所有的努力與掙扎顯得如此渺小與可笑,他被整容、失掉記憶忘了身份,甚至他真實可感的女伴莉莉,背后都有著政府、軍隊、幫會、殺手構成的臺灣政經界和黑社會勢力的操控。蔡新州在偌大的權力與欲望之海里浮沉,他意識到自身充滿了罪孽,需要經歷層層酷刑才能洗滌罪孽,然而,在龐大的政經網絡下,越是努力掙扎,越是意識到自己的渺小與無力,他只是其中一枚小小的棋子,只能越發深陷無底的棋盤。
謎底一層層解開,蔡新州發現自己所有的努力掙扎,都無法逃脫棋子的命運,如影隨行的欲望魔鬼,使他最后只能像瀕死動物一樣發出痛苦的悲鳴。到底什么是真實,什么是夢境?也許就像作品中權力與欲望的象征“老佛爺”的忠實手下安廣豪一樣,在生命行將結束的時候,反而感到自己要回到一個既真實而又虛無的存有狀態中。每個人的努力似乎都在證明自己的存在感,努力的結果卻往往事與愿違,蔡新州最后的悲鳴似乎在告訴我們,他試圖解開的謎底以及要證明的存在感,在權力與欲望之海中,只能是一場幻影,唯一不變的謎底就是流動的欲望。
四.結語
在快速變遷的都市社會中,流動的資訊思維方式,非常態的都市生活情態,不變的欲望流動與追逐,新世代小說家以流動性的都市場域形構了他們筆下的都市迷宮。正如鄭明娳在《浪跡都市》序中論及都市文學時所提出的不停的處于變遷狀態的情境:“和市民文學浮面的都市風情繪相形之下,狹義的都市文學可說是都市文學的本格,此中的‘都市’并不是指具體可見的地點,更不是高樓大廈堆疊組合而成的布景,‘都市’其實是社會發展中,因各種不同力量的沖擊而不停的處于變遷狀態的情境”[7]4。在這個變遷狀態的迷宮中,一切都是流動的,甚至身份都是不穩定的,流動成了都市變態活力的源泉,都市人樂此不彼,“變動不居”成了臺灣都市最大的時代特征,臺灣新世代小說家在不斷變遷的都市情境中演繹都市的魔力,營造出了筆下變動不居的都市情境。
注 釋
[1]李歐梵.徘徊在現代與后現代之間[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2]陳思和.但開風氣不為先——論臺灣新世代小說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收入孟樊,林燿德主編.世紀末偏航——八〇年代臺灣文學論[C].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
[3]彭瑞金.探索的、反叛的漂泊者——王幼華的小說世界.收入高天生編.王幼華著.王幼華集[M].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
[4]王昶編.林燿德著.林燿德散文[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
[5]周憲,許鈞.現代性譯叢(總序).見[美]馬歇爾·伯曼著,徐大建、張輯譯.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現代性體驗[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6]林燿德,黃凡合著.解謎人[M].臺北:希代書版有限公司,1989.
[7]林燿德編.浪跡都市(序)[M].臺北:業強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