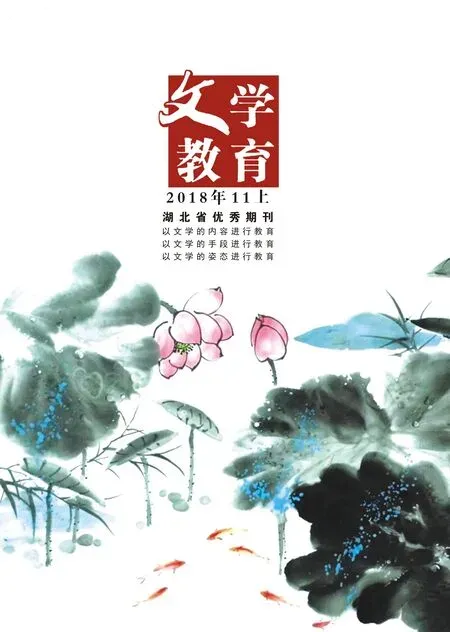淺析語言符號任意性說與象似性說
李 莉
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和象似性都是客觀存在在現代語言中,兩種性質既互相對立又互相關聯,科學辨證的認識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和象似性才能更好的對現代語言學科研究有所促進。
一.語言符號的任意性
語言符號的任意性最早是由現代語言學科的奠基人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提出的概念,而本書嚴格說并不是索緒爾本人所編撰,是在其過世之后由他的兩個學生根據他三次的對語言學講授中學生的筆記整理而成,并且索緒爾本人在三次講授這門課程的時候也并不是每次都一樣。而《普通語言教學》是他的兩個學生以他的第三次講授為主,輔以第一次第二次講授同學的筆記來整理而成,無法確保和索緒爾的所言所想一樣,這樣的“身世”也為該理論后來的遭受異議,備受討論蒙上了一層宿命般的色彩【1】。
索緒爾的學術研究提出了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即:表達具體東西或者抽象概念的語言符號及音響叫做能指,把該具體東西或是抽象的概念成為所指。能指和所指既成對出現,在概念上卻又是互相對立的,而索緒爾以這種二元論的方法解決了之前語言學術研究中尤其是文本中對語言符號所指代的音響形象還是概念的問題,消除了部分容易出現概念和音響形象混淆的情況。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是具有任意性的,而單獨的能指可能表達多個所指(多義詞),而同一個所指可能在同一語言中會有多個能指(同義詞)。這一理論的提出奠定了現代語言研究,使得后人在他的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展開了更加深入的研究。當然索緒爾對于語言的象似性也有所提及,如擬聲詞,且擬聲詞的能指和所指之間存在著對應的關系,以及兩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性的聯系。雖然在不同的語言結構中,有著不完全相同的寫法和讀音:如狗叫:汪,wow,woof等,都是對狗叫聲音的模仿,在各自的語言語音系統的導向,展現出了個體的差異性。他認為語言符號中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組合關系是任意的,不可論證的,不因個人意愿而改變的,當一個能指和所指配對了以后,流傳下來的都是群體約定俗稱接受的詞語,而剛剛提到的擬聲詞或部分的副詞等,因為數量太少并且人們在模擬自然或者人體情感所發出的聲音的時候,在音節,詞語的選擇上都是任意的,不可論斷的,也存在一定的任意性。這就是“現代語言之父”以及后人從他的授課中總結出來的語言符號的任意性。
二.語言符號的象似性
在現代語言學科的發展中,索緒爾的任意論及其《普通語言學教材》在其面世伊始就一直占據著現代語言學研究的主流,并且一舉奠定了索緒爾“泰斗”的地位。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在20世紀60年代左右,針對索緒爾關于語言符號任意性論的不同聲音逐漸多了起來,占據主流半個多世紀的語言符號任意性學說開始遭受到更多的挑戰和質疑。即語言符號的象似性。
最早提出象似性這一性質的研究者可以追溯到哲人皮爾斯,他對象似性是這樣描述的“由于與某物象似而代表某物的符號就叫做象似符號”,并將其推展到肖象繪畫,象形文字,隱喻,符號等。而后世對語言符號象似性的描述為:所指和能指之間,即語音概念元素組成與該物質或抽象概念中有某種必然的邏輯性的聯系,并且這種聯系是可以論證的。國內學者對于語言符號的象似性接受度普遍較高,因為漢語文既是對象似性最好的解說,由甲骨文發展而來的現代漢字,存在著大量的象形文字及擬聲詞,象形文字如:山,川,水,土,風,雨等,由甲骨文中對該物質自然條件下輪廓和形狀的直接描繪而來,能指與所指之間存在著直接的模仿關系。又如,漢文字根據物質的性質而加入的偏旁部首,如表達肉體生物相關的,“月”字邊:肥,腳,臉,腦,腔,胸,脾,肺等,表達服裝衣物相關的“衣”字邊:袍,褲,袖,襖,褂,襟,襠等。再如文字在其音響上也會和其所指有著一定的聯系,如表達奔騰一詞時,為表達其澎湃疾速的動態,[ben teng]兩字均采用爆破音作為聲母,而韻母為[en][eng]這種具有對聲母具有延續性的讀音,有力的描繪了奔騰一次帶給人的龐大,澎湃,疾速奔跑的感覺。再如依依惜別中“依依”二字就很好的表現了不舍從字體的形象上和讀音上都很好的展現了留戀,不舍的概念。所指與能指之間的互相指代關系明顯,不僅是索緒爾而提出的雙向的心理認知,而是在讀音,書寫上都有跡可循,有明顯關系的。而看似任意性很強的英語系語言同樣有很多象似性的痕跡可循,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任意所為,比如英文中帶有acid,acrid,acu詞根的多為表示酸的,尖的,銳利的相關的,如acidity(酸度),acute(尖銳的),acrid(辛辣的)我們可以看到對于這些所指他們的能指在詞的組成上也并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是由類似中文“偏旁部首”的詞根出現,此例中把“酸的”和“尖銳的”的放在一起呈現,這也和其它語言中對于酸和尖銳的混合不謀和,這也源于人類對這兩種概念的心理映射類似而來。再如ag-的單詞多指代“做,代理做”,如agent(ent代表“人”,代理人)coagent(合作者co代表“共同”,co+ag+ent=合伙人)。從舉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英語(或其來源拉丁語系)也是由不同的元素共同組成,并不是全部是任意性的。由以上例子我們大體可以知道,語言符號的象似性大概分以下幾個層面:
1.聲音(發音)的象似性。如著名哲學家羅素的一段膾炙人口的句子“An individual human existence should be like a river-small atfirst,narrowly contained within its banks,and rushing passionately pastboulders and over waterfalls.”這是一段羅素借河流的變化比喻人生的句子的節選,從音響效果上來看,第一句的時候元音以單元音為主,發聲位置為前舌音,音效輕巧,短促清澈,很好的表現了人生初始階段的“涓涓細流”而后半句的輔音多以爆破音和絲擦音,從音響效果上表現了河流噴薄澎湃的,拍打巖石,飛而成瀑的樣子。同樣我們把這段話翻譯成中文“人的生命應當象河流,開始是涓涓細流,受兩岸的限制而十分狹窄,爾后奔騰咆哮,翻過危巖,飛越瀑布。”我們發現同樣的音響效果和句子內容的配合也出現先中文的句子中,前半段是發音柔軟輕盈,元音多,后半段描寫河流奔騰的時候,同樣多有爆破音,音響效果短促,響亮,氣勢宏大。這說明語言符號在音響效果層面上,能指和所指之間也是有一定的關系的,在音效上語言符號是有很大程度的象似性的【2】。
2.詞匯層面的象似性。從詞匯上講,以英文為例主要分為兩種,他們或是直接模仿自然界的聲音,或是通過某些發音的詞根的發音對其所指有一定的模仿或是引發人們的聯想。直接模仿的最多就是擬聲詞衍生出來的如cuckoo杜鵑,knock敲,crash物體相撞的聲音,都是直接模仿自然界聲音從而產生的詞匯,或是前例中提到的ag-的單詞,多數都表述“做,代理做”,co-的單詞多表示“共同的”-ump多表示撞擊的聲音,以一種或一組發音來引發人們心理的聯系,對所指的聯系的雙向影響。同樣說明詞匯并非完全是任意促成的,而是由諸多元素共同構成的詞匯,才使得大家普遍接受,成為語言符號傳承下來。
3.句法的象似性。其它的象似性還包括距離象似性,順序象似性,數量象似性。沈家煊認為:認知或概念上接近實體,其語言形式從空間和時間上也想接近【3】。概念越接近在句子中的語言成分也會越發的接近,越是于句子核心內容無關的語言成分,在句子中也越趨于靠外。例如,從Mr.John
Smith可能熟了之后變成Mr.John又或者John又或者起個外號直接叫Jo,我們可以看到越是心理距離近的概念,去描述它的詞匯就會趨于更短。漢語這和使用中從李大壯先生到李大壯再到老李,大壯是一樣的象似性。而順序象似性揭示我們語言運用中難免的都會按照時間的順序來描述概念。數量象似性則定義為:描述組成越復雜的所指的時候,用的語言單位的數量也越多。比如lemon,lemontree,lemontrees,所指越復雜越多,我們用以描述指代它的能指也就越發的趨向于使用更多的字符。
當然,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索緒爾的任意性,現階段的研究中,人們還無法確定所有語言符號的象似性,無法確定所有語言符號的由來,應用的邏輯關系。象似性的研究以及成果的發現也都是坐落在索緒爾任意性的研究之上,從音效,語音,書寫,聯系,數量,距離角度層面來證明其象似性。而任意性的研究多著眼于單獨語素的研究論斷,所以這兩種研究誰都不能徹底的否定對方。語言符號是兼具著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在一方的基礎之上,承認吸收另一方的觀點,才是對語言符號研究工作進步更加應有的狀態。總之,象似性的研究和任意性的研究二者在著眼層面上不盡相同,象似性研究更象是任意性研究基礎之上的發展和補充,兩者既是對立的概念,又共同組成了現代語言符號的理論依據,分別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和作用,都是我們在研究學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