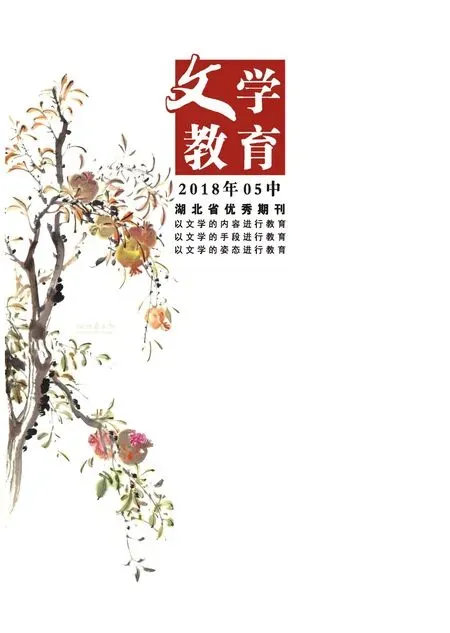《我的安東尼亞》電影改編之我見
何豐達
一.作品簡介
《我的安東尼亞》(1918)是美國作家薇拉·凱瑟最為人所熟知的一部小說,故事中的安東尼亞隨父親來到內布拉斯加大草原,后被哥哥強迫去到黑鷹鎮做工,遭遇拋棄后回到草原與庫扎克結婚,之后與他共同經營一個農場,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家族。作者薇拉·凱瑟向讀者展示出一個強健的女性形象——安東尼亞,體現了女性在極端生存困境下不屈不撓,歷經磨難,最終獲得女性性別身份上的超越的過程,是女性主義書寫的一個典型形象,表現出早期女性主義意識。
《安東尼亞家族》(1995)是荷蘭女導演瑪琳·格里斯導演的一部帶有激進女性主義傾向的電影,它講述了以安東尼亞為主的一家四代人的生活,包括女兒達尼埃萊、孫女斯拉西以及曾孫女莎拉。影片中的安東尼亞帶著她的女兒回到了家鄉,并接手母親的農場,通過勞動家族獲得了良好的經濟收入,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氣氛。電影以安東尼亞家族為主線,旁設一些無關緊要的男性角色圍繞她們,主要通過前三個女性對于男性的抗拒與蔑視來表達強烈的女性意識,成為激進女性主義的代表作品。
兩部作品在女性主題以及女性主人公的經歷上都有相似之處,并且都表現了女性的抗爭精神,但兩者蘊含了女性主義在兩個不同發展階段的女性意識,后者對于前者有所發展,并表現出自身獨有的特點。下文通過分別對比兩個作品中女性與自然,與男性的關系來揭示兩個作品的特點。
二.作品比較
(一)女性與自然
在兩部作品中,作者都把自然置于重要的地位。并且有意將人物與自然環境緊密聯系到一起,體現出人與自然的互動。但是在描寫人對環境的掌控程度上有不同的表現,也體現出不同的人物性格。
在《我的安東尼亞》中,安東尼亞跟隨父親雪默達爾背井離鄉來到荒涼的內布拉斯加大草原,在大草原上安東尼亞充分展現她獨有的女性魅力,她始終在自然的擁抱下感到幸福完滿,在這里安東尼亞成為了大地女神的化身,她在對自然的細心呵護中與自然相互交融。當她初到內布拉斯加大草原時,那里只有貧瘠的土地和荒涼的草原,只有構成鄉村的原料。可是安東尼亞卻從心底里感到一種生命原始的沖動,她感到了這篇貧瘠土地的呼喚。在一個深秋的下午,太陽落山時,安東尼亞“小心翼翼地把這只綠色的蟲子放在她的頭發里,把她的大手帕松松地系在她的頭鬈上。”[1]這時的安東尼亞仿佛成了無垠草原上的自然之母,撫慰受傷的生靈。
父親自殺后,為了貼補家用,安東尼亞離開了大草原,去到黑鷹鎮幫工。但是那里給安東尼亞帶來了無盡的傷痛,于是安東尼亞重新回到草原,她說:“我喜歡這里的每一堆谷物,每一顆樹我都熟,每一寸土地都是親切友好的地方。我要生活在這里,死在這里。”安東尼亞是天生的自然之子,唯有回到自然的環境,她才會綻放光彩。正如評論家薩皮斯尼克·諾伊爾稱:“草原的景致包含著她,她的存在亦離不開這片景致。”安東尼亞與自然是相互交融、渾然一體的關系。[2]
而《安東尼亞家族》則隱含著不同的認識。她們盡力切斷傳統觀念上女性對于自然的屈服,擺脫女性背負已久的“附屬品”的身份。
所以在《安東尼亞家族》中,觀眾看到的安東尼亞表現得更多的是她對于自然的控制與超越。這種超越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的自強。影片中,安東尼亞帶著她的女兒回到了家鄉,她接手母親的農莊,自己一個人獨立進行農作,包括耕地、播種、收割等農活。她有像男人一樣健壯的身體,強壯的手臂,田園四周風景如畫,安東尼亞的勞動則充滿了旺盛的生命力,她的肌肉向觀眾展示了她對于外界的的強有力的征服。她憑借自己的能力,將農莊規模逐漸擴大,使家族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從而在經濟上實現獨立,擺脫男性的束縛,體現出女性追求自我獨立生活的意志。
相較于《我的安東尼亞》,這部作品明顯弱化了女性與自然相互融合的傾向,而更加強調女性對于自然的征服,使安東尼亞處于絕對的高位,強化了女性克服自然困難,獲得生存的能力。
(二)女性與男性
在《我的安東尼亞》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較為卑瑣的男性形象,他們與安東尼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小說中,安東尼亞經歷了從大草原—黑鷹鎮—大草原的遷移過程。在不同的階段,她遇到了不同的男性。
第一個階段在大草原上寫了安東尼亞的家人并主要寫了她的哥哥,作者描寫他“褐色的眼睛小小的,目光狡黠,就像他母親一樣,但更狡詐,鬼鬼祟祟的”。[3]父親死后,她的哥哥讓她干繁重的體力活,隨意支使安東尼亞,但是安東尼亞并沒有被打倒,相反,“她整天把袖子高高卷起,她的兩臂像水手似的曬得黑黑的。她的頸子從兩肩之間茁壯地聳出來,有如草根泥上戳出來的一根樹干。”[4]安東尼亞表現出了積極向上的新女性形象。而哥哥心胸狹窄且待人刻薄,兩相對比可以看出作者對于安東尼亞的贊揚與對于男性的貶低。
第二個階段中安東尼亞被哥哥送到黑鷹鎮上做工賺錢。
安東尼亞開始住在哈林先生家里,但之后由于哈林先生對她跳舞表示指責,她便憤而離開。之后遇到了維克·卡特,他千方百計的算計安東尼亞,所幸安東尼亞意識到危險,及時逃脫。之后的拉里·多諾萬則在玩弄過安東尼亞后便無情的拋棄了她。經歷了無數磨難的安東尼亞最終決定回到她的大草原。安東尼亞無論怎么逃,都沒有逃脫男性的控制,在男性的社會中安東尼亞終于覺醒,她要反抗!之后在生孩子的時候,“她沒有喊一個人,也沒有哼一聲在床上躺下來,生下了她的孩子。”[5]
第三階段,安東尼亞回到了最初的土地,這時她遇到了丈夫庫扎克。他倆共同經營者農場。安東尼亞成為家里的頂梁柱,帶領丈夫和孩子們一起工作,創造財富。在這里,安東尼亞通過男性的挫折而逐漸成熟并超越自我,尋找到屬于自我人格的本質。
現在來看電影《安東尼亞家族》,主人公安東尼亞又是如何對待男性的呢?
電影中主要通過家族中三個女性的愛情觀來表現。
首先,安東尼亞帶著女兒回到鄉下接手農場,片中并未提及女兒的父親。后來,巴農夫來向安東尼亞求婚被安東尼亞果斷拒絕,因為她不需要當五個孩子的母親,而當需要男性的撫慰時,她則主動找到巴農夫,這時安東尼亞也僅僅是與他進行生理上的結合,而禁止心理上的融合。
到了第二代丹妮爾,她深受母親的影響成為一個不婚主義者。她想要一個孩子,但是不想要一個丈夫,于是母親帶她去找一個健壯的男性受孕,在這里男性充當了繁衍的工具,反映了女性對以往“生育工具”身份的反抗。之后丹妮爾與女兒的家庭教師產生了同性之間的感情,安東尼亞表示接受。
第三代是德勒薩。她擁有超常的智商,因此與凡夫俗子難以匹配,于是與哲學家孿手指產生了柏拉圖式的忘年精神戀。這表現出女性對于自由戀愛的追求,但是對于自己的孩子,德勒薩表現得很冷漠。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電影中的女性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異化成了“男性”,并迫使自己抑制或“被動失去”一些女性特征。比如將男性當做繁衍工具,這是對于女性傳統“繁衍工具”地位的反抗。另外,德勒薩缺少傳統的母性慈愛的特征,表現出男性式的冷漠。
所以與《我的安東尼亞》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以男性的阻擋作為推動主人公前進的動力,而后者則自動形成對于男性的阻擋,她們本身就具有強大的前進的意志力。她們試圖搭建出一個自己理想中的與世隔絕的女性王國,在這里男性成為女性的附庸與俘虜,在女性與男性的力量對比處于絕對失衡的情況下來完成女性的崛起,從而形成一個與“父權制”社會分庭抗禮的“女權烏托邦”。
三.總體評價
《我的安東尼亞》到《安東尼亞家族》體現了從自由女性主義主到激進女性主義的轉變。自由女性主義要關心的是自由、平等和正義,而激進女性主義則對性和性別給予了更多的關注。
在《我的安東尼亞》中,安東尼亞與自然和諧共處,顯示出她作為人的原始特征,也通過寬曠的大草原的背景向讀者展示出她旺盛的生命力。她與男性的關系則是在對立中進行融合,如對于哈林先生的抗爭,對于資本家卡特的抗爭,所以在她身上,出現了對立與妥協的交錯。
其中的對立性顯示出自由女性主義的初期特征。自由女性主義以自由思想原則為綱,主張人生而平等,從啟蒙主義思潮中尋求理論支撐,諸如“理性”、“自由”、“平等”等理論都為她們所用。這些理論對于女性平等起到了重要的支撐意義。作者通過安東尼亞這個形象的塑造對失衡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進行譴責,以喚醒女性沉睡已久的自我,安東尼亞通過精神的獨立而達到了人格的完整追求。
但是這一思潮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缺陷。因為她對于社會的適應始終帶著她對于男性不自覺的妥協,包括對于她的父親與哥哥的妥協,她的妥協實際上顯示出了女性身上根深蒂固的父權意識。這說明當時的女性對男性仍舊存在敬畏,對當時的男權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表示順從。這種順從已經成為了一種“集體無意識”,傳統社會強加的束縛內化成了她們自身的思想。
《安東尼亞家族》中的女性代表了激進女性主義一支,充滿著強烈的自我解放意識,她們反對以往的以男性為中心的思想,而提倡建立以女性為中心的理論與世界,但是同時,她們將自我處在一個與外界對立的位置上,包括上文中提到的與自然的對立,與男性的對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現與自我的對立。這種對立將她們置于一個相對邊緣性的地位,并獨自構筑起自我的女性王國。
從“自由女性主義”到“激進女性主義”,反映了在不同歷史環境下的女性意識的轉變,反映了女性主義在不同發展階段所要承擔的不同的歷史責任。總的來說,女性主義朝著一個不斷前進的方向發展,并且順應了時代的發展潮流。對于人類的進一步解放做出了重要貢獻,雖然在發展過程中會陷入誤區,但道路的曲折性無法阻擋潮流的前進,正如朱剛先生所言:“我們至多可以說盡管女性主義在艱難的向前邁進,它的發展是一條螺旋形的軌跡,充滿迂回和曲折。但是毋庸置疑,隨著時代的進步女性主義的發展更加平穩、成熟。女性不再會為一時的勝利沾沾自喜,也不會為不斷碰到的障礙垂頭喪氣。”[6]
參考文獻
[1][3]薇拉·凱瑟.《啊,拓荒者!我的安東尼婭》[M]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191,91.
[2]劉婷婷.女性·自然·和諧——從生態女性主義視角解讀《我的安東尼亞》[J].作家,2010(14).54-55.
[4][5][美]薇拉·凱瑟著.周微林譯.我的安東妮亞 [M].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85,218.
[6]朱剛.二十世紀西方文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