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
張隆溪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改革開放給所有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讀書人帶來新的生機之時,那小小的三十二開本的《讀書》毫無疑問是中國讀者最多、聲望最隆的期刊。一九七九年創(chuàng)刊首期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李洪林先生所撰《讀書無禁區(qū)》,宣稱中國人有讀書的自由,有選擇的自由。在經(jīng)過長期的封閉狀態(tài)之后,《讀書無禁區(qū)》那篇文章恢復了書的價值,讓中國人可以理直氣壯地讀書,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中,實在具有振聾發(fā)聵的巨大沖擊力。在這樣一個重大轉折的時刻,《讀書》以書為中心,討論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問題,其中刊載的文章可以說發(fā)出了絕大多數(shù)中國讀者和知識分子的心聲。
《讀書》一九七九年創(chuàng)刊時,我正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一九六六年我念完高三,畢業(yè)于成都九中(現(xiàn)在叫成都樹德中學),屬于所謂老三屆。“文革”當中上山下鄉(xiāng)、插隊落戶,在農(nóng)村生活了三年。后來回到城里,在工廠里又做了五年學徒工。在那動亂而且艱苦的歲月里,我一直沒有放棄讀書自學,而當時讀書,絕不可能想象將來會有什么實際用處,純粹出于興趣,出于對知識本身的渴求,所以那時候學習的動機真可謂純之又純,完全是為追求知識本身的價值而學習。“文革”后恢復高考,對于百廢俱興的中國具有根本意義,由此可以重建遭到嚴重破壞的教育,為國家培養(yǎng)急需的各方面人才。對我們老三屆那一大群人說來,那實在是生命當中一個具有關鍵意義的轉折點。當年我以“同等學力”直接報考研究生,并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大西語系英美文學專業(yè)。一九七八年進校,在北大這個中國的最高學府有三年扎實學習的機會。一九八一年畢業(yè)留校,在北大西語系工作了兩年。就在那時,《讀書》成為我們每個月期待著必讀的期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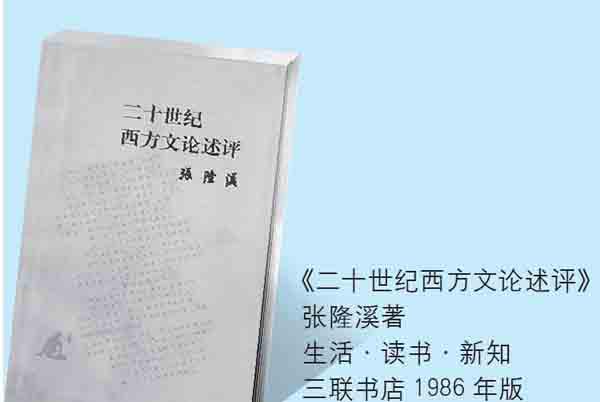
在北大學習,對我說來最重要的是有機會接觸到當時尚健在的好幾位前輩學者。在西語系,李賦寧先生、楊周翰先生都給我們研究生上課,與我們一起討論西方文學的經(jīng)典著作。我一方面由楊周翰先生指導,撰寫關于莎士比亞悲劇的論文,另一方面因為對文藝理論極有興趣,與朱光潛先生經(jīng)常交談,幾乎每天見面,從朱先生那里獲益極多。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陪同荷蘭學者佛克馬(Douwe Fokkema)教授去見錢鍾書先生,由此得以識荊,后來更經(jīng)常向錢先生或當面請教,或書信往來,這對我后來在學術上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也是由錢鍾書先生結緣,使我與《讀書》有一段特別密切的聯(lián)系,或曰緣分,因為我不僅是《讀書》的讀者,也成為其眾多的作者之一。那應該是一九八一年初秋,正是天高日晶,氣爽宜人之時。未名湖沉靜如睡,沿湖一帶草木蔥翠,不時可見有學生在湖邊散步交談,或捧著一本書坐在湖畔細讀。未名湖邊的備齋那時候是教工宿舍,我和一位姓陳的同事合住一間房。某日,《讀書》編輯部董秀玉女士到備齋來找到我,說是錢鍾書先生介紹她來,希望我為《讀書》撰稿。
那也正是比較文學開始在國內興起之時,由東語系季羨林先生發(fā)起,會同西語系李賦寧、楊周翰兩位教授,中文系樂黛云副教授,還有剛剛畢業(yè)、開始在西語系教書的我,我們一共五人,成立了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小組。又通過我去聯(lián)系,聘請錢鍾書先生做我們小組的顧問。當時國內對比較文學還相當生疏,于是我們辦了一份油印刊物,叫《北京大學比較文學通訊》(以下簡稱《通訊》)。此《通訊》由我主編,收集和翻譯了一些有關比較文學的文章,印好之后,郵寄到一些大學的中文系或外文系,以有助于推動比較文學在國內的發(fā)展。我把與錢先生交談中的一些相關內容,寫成《錢鍾書談比較文學與“文學比較”》一文,發(fā)表在《通訊》上。因為那是一份非正式的油印刊物,董秀玉便把此文拿去,正式發(fā)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的《讀書》上。當時北大的比較文學研究小組非常活躍,做了不少事情。我發(fā)動和我同一屆的西語系研究生同學們,翻譯了國外一些重要文章,編輯了《比較文學譯文集》;又與中文系同屆研究生同學溫儒敏合作,收集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編輯了《比較文學論文集》。這兩本書都交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成為北京大學出版社比較文學研究叢書最早的兩本。比較文學后來在國內發(fā)展得很快,成立了全國性的學會,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專門敘述中國比較文學史的著作問世,但當初我們那個小組的存在,現(xiàn)在卻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專門的比較文學史著作者也似乎茫然不知,少有提及。我在此略加敘述,也算是立此存照。
一九八二年春,我受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邀請,到中大英文系訪問一月。當時內地的新版外文書很少,就連北大圖書館也收藏有限。我就利用到香港的機會,購買了許多西方文學理論的新著。那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計劃編輯一部介紹國外學術最新動向的書,俄蘇文學理論一篇,交由吳元邁先生執(zhí)筆,而西方文論一篇,則想請錢鍾書先生或由他推薦一人來執(zhí)筆。錢先生推薦我來寫這篇文章,到香港中大訪問,恰好給我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使我得以購買相關的外文書,比較系統(tǒng)地閱讀了二十世紀西方文論的主要著作。董秀玉和我商量,決定在《讀書》開辟一個專欄,題為“二十世紀西方文論略覽”。于是從一九八三年四月開始,我每月在《讀書》發(fā)表一篇介紹西方文論的文章,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三月,前后一共刊載了十一篇。這個專欄從總覽二十世紀西方文論的發(fā)展趨勢,到具體討論精神分析與文學批評、英美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神話與原型批評、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接受美學與闡釋學等各派主要的文學理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的知識界從完全封閉的狀態(tài)走出來,對知識充滿了渴求,對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有強烈的好奇心和了解的意愿。我在《讀書》的那個專欄算是最早介紹西方當代文學理論的系列文章,所以頗受讀者歡迎。當時每成一篇,我太太薇林就工工整整抄在稿箋紙上,或郵寄到三聯(lián)書店《讀書》編輯部,或編輯部派專人到北大來取。在《讀書》上,我那些文章頗有點特別,因為每篇引用書刊和論文,都注明出處頁碼,而且有許多外文,全都排印出來。往往每篇一脫稿,便立即發(fā)排,沒有一字的改動或刪減。沈昌文先生在《閣樓人語》書中回憶當年辦《讀書》的經(jīng)歷時,特別提到“專欄文章”是《讀書》的特色之一,并且提到我和其他一些作者,認為我們“組成了一支堅強的作者隊伍,成為《讀書》的臺柱”。不過我那個專欄寫作的時間并不長,一九八三年四月發(fā)表第一篇,十月底我就離開北大,到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去讀博士學位。到美國之后,一方面因為學習很忙,寫作也變成以英文為主,另一方面在美國大學的學術環(huán)境里,發(fā)現(xiàn)文學理論逐漸讓位于表現(xiàn)激烈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批判理論,文學研究也逐漸被文化研究所取代,便覺得我已經(jīng)介紹過的文學理論—從美國新批評到俄國形式主義,從結構主義到接受美學和闡釋學—基本上都與文學密切相關,而往后西方理論的發(fā)展越來越激進和政治化,我自己需要去理解,也就沒有想要繼續(xù)寫下去的意愿。同時我還意識到,西方理論對各種差異的強調往往把東西方對立起來,西方人論及中國,也往往把中國視為西方的對立面,不利于我感興趣的東西方比較。福柯認為中國人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思維,代表了不可理喻的異托邦(hétérotopie);德里達認為中國的象形文字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沒有語音中心主義,也就沒有貶低書寫文字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最能夠充分體現(xiàn)他所謂的差異(différance)。這些都是顯著而有很大影響的例子。于是我的研究興趣轉向東西方比較文學,針對把東西方絕對對立起來的傾向,注重跨文化理解,更積極參與近年來興起的世界文學研究。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讀書》的作者和編輯可以說是十分親密的朋友,大家都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我?guī)缀醢选蹲x書》看成是自家園地,每成一稿,首先想到的就是《讀書》。這當然只是自己的幻覺,在《讀書》上其實有各種不同內容、不同風格、不同聲音,有時也有不同意見。我那時候剛開始寫文章發(fā)表,比較起許多知名作者,只算得是晚輩。我在介紹西方文論時,常常引用中國古典為佐證,就曾引起一位我很尊重的作者的質疑。我在評述神話與原型批評時,說最早的語言和神話都是一種隱喻,便引許慎《說文解字·序》依據(jù)《易·系辭下》的說法,認為文字就像卦象,都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創(chuàng)造成的。我接下去又說:“頭頂為‘天,人陰為‘地,就是用人的身體器官作比喻來命名宇宙上下。”這位作者看到我的文章,頗不以為然,就寫了一封信交給董秀玉,批評我說“人陰為‘地”完全是“毫無根據(jù)”。其實我那句話并非沒有根據(jù)。“頭頂為‘天”就從《說文解字》為依據(jù)。按《說文》釋“天”為“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從字形上看,是在“象人形”的大字上面再加一橫,段注就說“顛者,人之頂也”,所以我說“頭頂為‘天”。但《說文》釋“地”為“元氣初分,輕清陽為天,重濁陰為地。萬物所陳列也。從土,也聲”。這的確沒有直接說人陰為地,但段注說,“坤道成女,玄牝之門,為天地根,故其字從也”,便強調相對于天為乾,地則為坤、為女,并引《老子》第六章“玄牝之門,為天地根”一語,突出大地生育萬物,說明為什么“地”該“從也”,而《說文》釋“也”字,正謂其為“女陰也”。然而我說“人陰為‘地”,依據(jù)不是《說文》,而是章太炎先生討論文字起源的著作《文始》對“也”字的解釋。他引《說文》謂“也”為“女陰”,認為“此合體象形也”,又說,“人體莫高于頂,莫下于陰”,而且進一步解釋說,“足雖在下,然四肢本可旁舒,故足不為最下,以陰為極”。這一說法完全符合“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語言發(fā)展原則,即人在認識和命名事物時,往往最先用自己的身體器官去比喻所認識的外部世界。“頭頂為‘天,人陰為‘地”,就是用人身體最高和最低的部位來比喻至高無上的天穹和陳列萬物的大地。當然,對于“也”是否就是“女陰”的象形字,語言學家有不同看法。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里就批評許慎和章太炎說:“由于迷信《說文》,章氏跟著許慎鬧笑話。‘也字本是‘匜的古文。許慎偏要說是‘女陰也,章氏跟著錯,甚至說‘地字古文也當作‘也,因為重濁陰為地。這種議論是站不住腳的。”王力是著名的語言學家,但許慎的《說文解字》是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重要的依據(jù),而章太炎也是近代著名的大學問家。你可以贊同王力先生的意見,認為釋“也”字為“人陰”是一種誤讀,但你不能完全抹殺從許慎到段玉裁,再到章太炎的學問,不能說“人陰為‘地”這句話“毫無根據(jù)”。于是我用極平和的態(tài)度和尊重對方的語氣,寫了一封回信給我敬重的那位作者。據(jù)董秀玉告訴我,他接受了我的解釋。
回顧三十五年前這些評述西方文論的文章,覺得其中大部分內容到現(xiàn)在仍無須大改,我當時所持的看法,大多數(shù)也至今沒有改變。然而畢竟時隔多年,中國的社會環(huán)境和語境已有很大變化,如果今天來寫這些文章,有些地方行文一定會很不同。例如關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我現(xiàn)在仍然覺得把一切都歸結到力比多即性欲的沖動,是這派理論的局限,但我在寫《讀書》上那篇討論精神分析與文學批評的文章時,對弗洛伊德還沒有比較全面的認識。一九八三年我去美國留學,在哈佛大學圖書館里才真正讀了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發(fā)現(xiàn)他的文章不僅說理清晰,而且不像后來許多精神分析派批評家那樣簡單武斷。我在那本《比較文學研究入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里討論彼得·布魯克斯(Peter Brooks)的著作時,就特別提到他對弗洛伊德文章的精彩分析,說明“弗洛伊德很明確地意識到終結意識之重要,同時也意識到終結之建構甚至虛構的性質”。此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有些用語和語氣有當時的時代背景,現(xiàn)在很多讀者恐怕不能清楚理解。例如我在第一篇文章結尾提到“習慣于‘一分為二看問題的我們”那一大段話,在當時的語境里,明顯是帶反諷意味的口氣,當時的讀者大多可以領會。我說:“東方和西方不僅在空間上有很大距離,在時間上似乎也有不小的距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有機會走出國門,到外面的世界去,才大為吃驚地發(fā)現(xiàn),全世界大概多數(shù)的人都比當時的我們物質條件要好。所以我接下去更明確地說:“這種傲慢的態(tài)度最終是使我們自己受了損失。”像這類的話,到現(xiàn)在大概不會這么說,也不必這么說了。不過在當時,卻自有要這么說的道理。這也許是現(xiàn)在回顧當年與《讀書》的一段緣分時,可以聊做一點說明的贅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