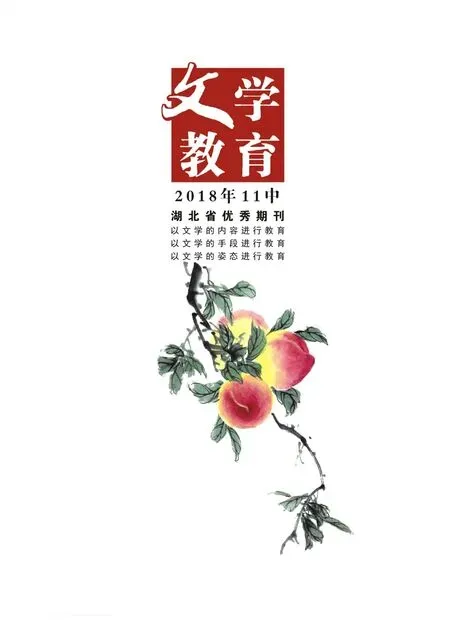淺述我國古代商人地位的變遷
向俊宇
從十六世紀世界步入大航海時代后,中國就開始逐漸走向衰弱,并逐漸被西方國家所超越,更在19世紀成為了列強欺凌的對象,曾經的天朝上國,世界第一,成為了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這是為什么呢?有人說原因是自從商鞅變法后就開始的“重農抑商”政策所導致的,商業不發展,商人社會地位低,造成了中國商品市場的不活躍,滿足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便選擇了閉關自守,最終自己是閉門造車,然后就被重視商人地位的西方國家給趕超了。筆者的觀點是,這是一種謬論,真正導致中國走向衰弱,讓中國“閉關自守”的,就是一直在叫屈的商人階級。因為重農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導致的就是不重視商業,不重視商人社會地位的表現。商人社會地位不高,即便商人們賺到了財富,還是希望去提高自身社會地位,或者去買田地,畢竟古往今來,最保值最具價值的東西,就是土地。然后商人們的目光不再投到擴大生產上,就導致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不能開花結果,中國也就失去了步入工業化時代發展的大好機會,然后就開始逐漸走向衰弱,并逐漸被西方國家所超越。
在原始社會后期,開始出現了以物換物的交換活動,到了夏朝,黃河下游的一個部落因隨大禹治水有功,被封為商,其六世孫王亥聰明多謀,很會做生意,在貨過程中被易族殺害,其子孫發兵伐易,商族為了削弱夏的國力,組織婦女織紗換取夏的糧食,把貿易作為政治斗爭的武器,最后滅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建立后,由于商部落農牧業的迅速發展,其手工業也相當發達,有了更多的剩余產品,商被周滅后,商族人由統治階級變成了奴隸,生活每況愈下,為了過上好日子,紛紛重操舊業,做起了貿易。久而久之,商族人就被視為做買賣的人,后來人們把做買賣的商族人統稱為“商人”,這一稱呼一直沿用至今。[1]
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了比較繁榮的商業市場,當時的商業活動,雖在市場上進行,即“處商就市井”[2],但據當時的管理制度,必須由政府來壟斷市場,掌控物價。據《左傳》載,鄭、衛、宋國都有諸師;魯國有賈正等官吏來管理市場。[3]可是因那個時候的戰時體制,一切都是為了強國強兵,為了戰爭而準備的政策,自然希望一切所得都能成為運轉戰爭機器的物資,主要保證奴隸主貴族的需求,不為發展和擴大貿易,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阻礙了當時商業和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春秋時代雖然以“官商”為主,但是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公有制即井田制度的逐漸量變,列國中也出現了有錢有勢和大商人。
春秋戰國時著名的六位商人是:白圭、子貢、呂不韋、管仲、弦高、范蠡。陶朱公范蠡堪稱歷史上棄政從商的鼻祖和開創個人致富記錄的典范。他曾是春秋末期越國的大政治家,在越國被吳國滅亡時,他提出降吳復國韜光養晦之計策,并隨同越王勾踐一同到吳國為奴,千方百計謀取勾踐回國,成為輔助勾踐滅吳復國的第一謀臣,官拜上將軍。但當越王勾踐復國后,范蠡萌生退意。退歸林下的決心已下,不久辭官而去。他到了當時的商業中心陶(即今山東的定陶縣)定居,自稱“朱公”,人們稱他陶朱公。在這里他既經營商業,又從事農業和牧業,很快就表現出非凡的經商才能。《史記》中載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財聚巨萬”。就是說在從商的十九年中,他曾經“三致千金”——三次散盡家財,又三次重新發家。堪稱“中華自古商之祖”。他的道、儒、法相濟的思想、人格特征與行為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4]
先秦每一位富商,無不與政治有密切關系,但戰國后期的商鞅變法革新,“獎耕戰、抑商賈”,把農業生產放在富國強兵的首要位置而對不直接生產物質財富的商業及商人采取了抑商政策,商人活動受到了很大限制,也出現了“賤商”的看法。晉人傅玄在《檢商賈》中就說:“夫商賈者,所以沖盈虛而權天地之利,通有無而一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對商人的態度極其矛盾,既分享勞動成果又鄙視其身份。[5]“重農抑商”的理論和儒家學說“重義輕利”的思想相結合,深入滲透到中國各階層意識中,“賤商”政策奠定了輕商思想基礎,長達兩千年。[6]
漢朝建初,也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從春秋戰國一直到漢朝統一,歷經了長達數百年的戰爭,漢初已經是一個非常虛弱,非常貧困,極度物資匱乏的時代,這個時候解決吃飽肚子的問題是最重要的。要想吃得飽,那么就先搞好農業生產建設,而無需去市場上交易,只有當自給自足的生產物質滿足不了或者有了剩余產品時才需要去與別人交易。也就是說解決了吃飯的問題后,再去解決精神文明上的事情,這個時候就需要發展商業。
文景之治后,商人的社會地位依然低,可是商業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商人的社會心理也隨之改變,當時俗諺流傳著“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7],甚至是對外貿易也得到了長足發展,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絲綢之路就是漢朝打通并發展的。西漢(公元前202年—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西北絲綢之路”)。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制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促進了歐亞非各國和中國的友好往來。
在漢武帝時期,又開始奉行“富國抑商”政策,漢武帝用政治權利將全國的物資統征到戰爭需求當中,商業受到了一定的打擊,直到戰爭停止,漢朝的商業又開始繁榮起來。
三國兩晉和南北朝時期,總的說來,這是一個亂世,一個開放的時代,也是一個棄舊圖新的時代,新舊交替,人民和時代都在不斷選擇中,并為未來的大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秦漢制度多數瓦解,世兵制、租調制、屯田制、府兵制、均田制、胡漢分治制等登上歷史舞臺,各個政權在新舊制度、治國思想、方法上進行了嘗試和選擇,以加強國力,進而統一全國。[8]這一時期政治割據,戰爭連綿,是中華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政治上士人大多追求清靜無為、自由放任、耽于清談。經濟上,士族莊園經濟和寺院經濟占重要地位。商品經濟水平較代,各民族經濟交流加強,隨著民族融合的發展,各族相互學習,促進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南北經濟趨向平衡,江南得到開發,開始趕上北方。為我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奠定基礎。[9]
隋唐時期,“開皇之治”為當時的中國積攢了無數的社會財富,老百姓吃飯問題得到了解決,即便經過隋末唐初的連年戰亂,李唐統一后,經過貞觀前期的幾年發展,就迎來了新的盛世。然后商業社會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最主要的表現是長安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繁華、最繁榮,商業氛圍最好的城市,而且沒有之一,李世民為了掌控國際貿易,滅高昌,威服西域諸國,通過一系列的對外戰爭獲得了西域霸權,控制了“陸上絲綢之路”,成為了隋唐繁榮的重要組成因素,成就了“開皇之治”和“貞觀之治”。中間由于唐高宗和武則天的短視和失策,西域霸權一度喪失。后唐玄宗重獲西域霸權,直至安祿山之亂。然而之后再也沒有恢復。唐朝時期開辟的中國到歐洲的商道,繼而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繁榮,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
大唐商業雖然繁榮,商人的日子過得很好,可是商人的社會地位依然很低,商業是從屬于政治的,商人地位是低賤的,是為政治服務的,而且商人并未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和有效的官商勾結,唐代商人的財富往往成為封建國家、權貴、藩鎮掠奪的對象。
唐朝的富商大賈很多,但最活靈活現的莫過于《酉陽雜俎》中描述的裴明遠了。裴明遠本是個回購廢品的小販,雖然姓‘裴’卻賺了大錢。有了錢之后,他在金光門外用極低的價格買了一塊滿是瓦礫的荒地。為了淸除這滿地的瓦礫,他想了一個好辦法,在地頭樹一根木樁,再掛一個筐,吸引少年子弟檢拾瓦片擊筐,中者有獎。沒過多久,地上的瓦礫便被孩子們一拾而空。不知道這是不是籃球的雛形,但肯定是商業與娛樂業相結合的最早記載。荒地清理出來后,裴明遠便在地里種起了果樹,同時租給牧羊人做羊圈,羊糞蛋正好又成了果樹最好的肥料。春天果樹開花的時候,他又在果園里養蜂采蜜,把一塊不毛之地變成了生機勃勃的現代生態園區。裴明遠的這套循環經濟的組合拳,不但折射出了唐代商人商業模式與商業思想的自由與成熟,也折射出了唐朝政府對待商業與商人的寬容與肯定。唐太宗聽說了裴明遠的事跡后還大加贊賞,直接調入中央當上了中書舍人、太常卿的大官。
不料,唐朝政府對待商人的這種寬容與肯定,卻也為自己的最后覆亡埋下了禍根。原來,致使唐朝徹底傷了元氣的安史之亂主角安祿山,牙人出身(現在叫做經紀人的商人)。商人做得沒什么名,卻差一點要了唐朝的命。牙人出身的安祿山最終沒能直接要了唐朝的命,但兩個私鹽販子卻直接要了唐朝的命。這兩個私鹽販子一個叫王仙芝,一個叫黃巢。這二位因為得不到販鹽的資格而走私,為有效走私而武裝,又因沒有出路而造反,最終成為唐朝最為重要的掘墓人。說偉大的唐朝成也商人,敗也商人,絕不為過。
唐朝是我國歷代經濟,外交都比較鼎盛的時代,當時唐政府鼓勵各使國來唐貿易,當時的經濟中心都城長安,吸引大食人、波斯人不遠萬里前來長安經商。其次,唐朝民風比較開放,對商人階級雖然不是很重視,但是也沒有明確提出反對,老莊的“無為而治”的道教宗旨在唐朝地位被確立為正統,為唐朝商人經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政治環境,也出臺了一系列扶商政策。在唐代,官商法律地位最高,商業受政治權力干預較強;商人實際地位遠高于農、工;到了唐中后期,商人地位仍在提高,但提高的程度有限;就整個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而言,唐代商人的法律地位,上承秦、漢之統,下啟趙宋之新局面,處在歷史發展的轉折點上。[10]
宋朝對抑商傳統有所松動,允許商人入仕,商人的社會地位也有所改善和提商,一些官吏也兼營商業。由于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經濟作物的進一步推廣,使農副產品和手工產品增多,宋代的商業繁榮起來。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六月,詔令:“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者,亦聽取解。”[11]長期以來受社會抑商觀念壓制、束縛的商人有了入仕官場的可能和依據。在中國古代全部建立的政權中,宋朝的政策把士農工商放到了平等的地位。所以宋朝的文化水平超過了歷代,達到了文明的巔峰,經濟發展也是歷代之首,從《清明上河圖》中可以看出當時北宋京城汴梁的繁榮程度。[12]
雖然宋朝的財力和經濟各方面都不次于唐朝。但它的政治環境和安全局勢限制了商人的發展,當時宋朝時刻處在大遼、金、西夏的包圍下,軍事上始終處于劣勢,北宋始終沒有統一周邊的少數民族,最終更是被金滅掉。南宋偏安一隅,更是沒有陸上外貿的條件,所以宋朝只能向東南沿海發展海外貿易,開創航海貿易。但是后世帝王都忽視航海,明朝航海淺嘗輒止。宋朝每年都要拿大量的歲幣交給外敵來換取暫時的和平,哪有財力保證一個穩定的經商環境呢,富商大賈可以通過科考、賄賂、買官、聯姻的方式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而占商人絕大多數的小商人更多的處于社會低層。他們是政府剝削、壓榨的對象,也是各級官員敲詐、勒索的目標。政府為了維持龐大的開支,就向利潤較高的商業開刀,通過提高商稅、壟斷專賣等措施強行分割商人的利潤。“州郡財計,除民租外,全賴商稅。”[13]“商賈往來,不出襄境,境內二十里而有三稅。”[14]
元朝建立后,世祖忽必烈全面推行漢法,采取一系列發展生產的措施,使全國工農業生產逐漸得到恢復和發展。隨著生產的發展,商品經濟也發展起來。表現在商品產量的提高和國內外商業的繁榮兩個方面。《元詩選》載,“吳中富兒揚州客,一生射利多金帛,去年販茶湓浦東,今年載米黃河北。”在商品發展的其礎上,元代商業十分繁榮,馬可波羅在其游記談到,大都的商品盛況“最稀奇最有價值的東西都來集于此城。”國內各省“百物輸入之眾,有的川流不息。僅絲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城內的商業區有米市、面市、珠子市、鐵器市等。大都大街小巷到處都有“各種各樣的商品和貨棚。”郊區建有許多旅館,以“供各地前來的商人和因事來京的人居留之用。”他說:杭州“在莊嚴和秀麗上,的確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每星期有三日為集市,“有四五萬人”帶著各種物品來此貿易。市場上的商品“不可勝數。”除大都外、杭州外,北方的西安、太原、大同、濟南,南方的揚州、集慶、鎮江等城市商業相當繁盛。元代海外貿易也很發達,就其通商范圍和貿易的數量上大大超過前代。南宋有海外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有51個,200種。據《(至正)四明續志》記載,元代達到140多個,品種250種以上。在元末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絲綢之路等。
元政府對于商人采取保護和鼓勵的政策。一是保護財產安全。在商旅往來的水陸交通要道上“遣兵防衛。”二是積極鼓勵通商。“減上都商稅”“置而不征”的免稅待遇。三是免除西域商賈憷泛差役。四是許多貴族和寺院僧侶經商有免稅特權。元朝的商人大多屬于“色目人”,他們在政治和法律上享有僅次于“蒙古人”的優厚待遇。元代商人遠涉重洋,經營海外貿易,為中國和亞非各國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元代大商人的社會地位十分優越,但中小商人地位卻十分低下,政府對他們管制嚴格,營運上沒有自由。特別是私鹽販子日子不好過。他們與政府經常發生禁止與反禁止、限制與反限制的斗爭,除鹽商外,其他中小商人為了反對元朝政府的剝削和各級官吏的百般勒索,也積極參加農民的武裝斗爭。淮東的張士誠原來也是個“以操舟運鹽為業”的小商人,他們天然的反抗精神和具有較豐富的斗爭經驗和社會閱歷,成為起義軍的領袖和重要骨干力量,在推翻蒙元王朝的斗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15]
轉眼就到了明朝,在明朝初年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卻爭議頗大的事件,也就是“鄭和下西洋”。歷史課本上對鄭和下西洋除了歌功頌德之外,最大的批評就是鄭和下西洋是做虧本買賣,鄭和下西洋是為了找建文帝,是為了送東西給番邦,換取他們來中國朝貢,滿足永樂大帝的虛榮心。鄭和下西洋確實有免費贈送一些中國的東西給東南亞、南亞,甚至是非洲的一些番邦國家,可實質為的卻不僅是永樂皇帝的虛榮心,而是要形成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朝貢體系。明朝生產出大量的物資,諸如番邦貴族百姓喜歡的茶葉、瓷器、絲綢等,同時明朝的貴族百姓也希望用上番邦的香料、奇珍、珠寶等,這就形成了巨大的商業需求,當時明朝與外國的貿易量是很大的,于是永樂帝就派鄭和下西洋,宣揚赫赫國力和無與倫比的強大武力,吸引番邦前來朝貢,朝貢的使者并不是只帶著幾頭大象,幾座珊瑚,還會有大量的隨從人員,主要是商人,這些外國商人帶著大量物資隨使團來明朝做交易,鄭和的寶船就起到了運送這些物資,及維護商路安全的作用。所以,在南北朝時期形成,在明末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與西北絲綢之路同時出現。可是雙方交易,掌控住什么能得到最大的利益呢?那絕對是定價權,現在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話叫做:三流企業做產品,二流企業做品牌,一流企業做標準。你夠強,你才能做標準,然后就能用標準爭取到最大的利益。而當時的大明王朝就是中外貿易的標準制定者,掌握著中外貿易的定價權,外國出口到中國的東西賣多少錢,要什么樣的品質,大明朝說了算,大明賣給他們的東西,賣多少錢也大明朝說了算。也就是說比如番邦商人一斤香料,他覺得值十兩銀子,可是大明朝說只能賣五兩,你就只能賣五兩。大明朝的一批絲綢,他們覺得只值一兩,可是大明朝要賣五兩,你也不得不買。掌握了定價權,大明朝獲利何止萬千。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對外政策中一直奉行的“朝貢體系”,在這種體系內,依然會給外國商人一定的利益賺,永樂大帝通過鄭和下西洋建立起的這套朝貢體系,謀取了巨額的財富,支撐著北擊蒙古,南伐安南,修永樂大典,通大運河,遷都北京……所以說,當時的對外貿易是一個巨大的蛋糕。為了奪取這份大蛋糕,大明朝時期形成的官商勾結利益集團開始組團忽悠皇帝,忽悠百姓,他們對永樂大帝的盛舉歌功頌德,卻不會告訴皇帝和百姓,做這些事是需要錢的,畢竟組建寶船船隊下西洋,一開始是需要朝廷撥款的,只有等船隊回國后,才能開始賺錢。說鄭和下西洋要投入很大的財力、物力、人力,是禍國殃民之舉,是導致永樂朝晚期朝廷財政出現嚴重危機,甚至到崩潰邊緣的最大原因。他們不繼續投資,然后一些根本上看不到鄭和下西洋所帶來巨額暴利的鼠目之士,還以忠臣自居,燒了鄭和下西洋的海圖,絕了朝廷繼續下西洋的決心。隨后倭寇問題越來越嚴重,利益集團忽悠皇帝說必須海禁,阻止沿海豪強或百姓和倭寇勾結。海外貿易這份蛋糕就開始分給了利益集團,主要是南直隸黨(后來稱東林黨)和浙黨的手中。熟知明史的都知道最大的倭寇汪直,其實是中國人的事情,他曾是海上霸主,平生最大的夢想就是希望朝廷開海禁,通過他的手及海外貿易,給明朝帶來巨額的財政收入,同時還能整治倭寇,他當時就是日本的一個王,曾說有能力將日本甚至東南亞都變成為大明朝的“殖民地”。胡宗憲答應了他的要求,然而,被忽悠上岸的汪直卻被殺了,胡宗憲也被將他捧上位的嚴嵩冤枉,最終自殺。汪直和胡宗憲的理想也隨他們的去世而煙消云散了。利益集團就通過走私的方式和海外貿易,從而賺取了巨額的利潤,諸如以清流領袖自居的徐階,他家族的財富比嚴嵩還多,單單土地就是幾十萬畝。后來的東林黨領袖錢謙益,“背禮”娶天下第一名妓柳如是并為她在虞山修了座壯觀、華麗且頗有情調的“紅豆館”和“絳云樓”。[16]不僅有東林黨和浙黨利益集團,在北方還有晉黨,嘉靖時的晉黨領袖人楊博,是晉黨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包庇他們和蒙古、女真人走私貿易,女真人強大背后有晉黨一大功勞,所以到了清朝,晉商還成了皇商。明朝中后期,利益集團開始了你死我活的權利斗爭,各利益集團也開始形成了對朝廷的控制力。在嘉靖皇帝的有意引導下,“朋黨”只要不是一家獨大,不威脅到皇帝的位置,嘉靖帝就踩平衡,各利益集團斗爭的同時也在妥協,通過手中的權利影響朝廷的施政方針,壯大自己的勢力,明朝末年徐階為首的東林黨滅了嚴嵩為首的江西黨,又打敗了浙黨,浙黨投靠了閹黨,導致了閹黨魏忠賢的一家獨大,于是崇禎帝又用東林黨滅了閹黨。東林黨為了自己的利益,通過朝廷政策的傾斜壯大自己,所以在明末江南依然繁華如初,秦淮八艷就是江南依舊繁華的代表,且不顧晉黨利益,要求朝廷對商人征低稅,對農民卻橫征暴斂,對北境邊防不重視,說遼東邊防出問題是武將不給力,將士不用命,反正就是拿著手中的權利,為自己謀利益而彈駭壓制其他勢力,于是遼東將士和北方人民不滿,晉黨也不滿,導致農民起義爆發,晉黨和遼東的吳三桂引清入關,明朝沒了,東林黨也被清人屠殺殆盡。
在明朝中期之前的中國,利益集團都是被朝廷控制的,他們能成為皇帝手里的一把刀,可以用來活躍商業,豐富百姓生活,也可以掌控他們的財富用于戰爭或其他需要。可是明朝中后期,利益集團掌控朝廷,為了自己的利益,建議朝廷海禁,中國外交及貿易開始弱后,但在境內,給了商人更多的政策傾斜,更高的社會地位。造成大明朝滅亡,造成中國走向衰弱的原因之一,是利益集團的形成發展,最后讓朝廷和利益集團的從屬地位發生了轉變而造成的。
清朝時,商品經濟進一步得到發展,一些大商人開始走上仕途,著名徽商胡雪巖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胡雪巖是晚清時期中國商界的風云人物,是中國近代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紅頂商人”。他能夠從一個錢莊的小伙計,暴發成為當時中國最有錢的人,而且還搖身一變,成為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書寫了一段離奇繽紛的人生傳奇。其經商才能、處世韜略,一直為世人所稱道。他精心創下的胡慶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價”的優良傳統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雪巖的一生,極具戲劇性。他以“仁”、“義”二字作為經商的核心,善于隨機應變,決不投機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初在杭州設銀號,后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陜甘總督后,主持上海采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余處,并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他經商不忘憂國,協助左宗棠西征,維護了祖國領土的完整;在救亡圖強的洋務運動中,他也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勛。當然,胡雪巖也未能擺脫商人以利益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極盡奢靡,但畢竟人無完人、瑕不掩瑜,胡雪巖無愧于“中國近代第一商人”、“商圣”的美譽。[17]
明清時代,以十大商幫為代表的地方商幫和大商人資本在中國興起,中國的商業與體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商幫崛起的地方,傳統的士農工商中的商也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棄儒從商。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鴉片戰爭使部分中國人意識到貿易之重要,中國出現了“紳商”階層。它是經濟實力與政治權力相結合體,有關學者稱,在政界與實業界“雙棲”是這個階層的最大特點。此后,“官督商辦”、“合辦”更加重了這個特點。
20世紀初,作為近代新式商人社團的商會成立,它是近代的產物,通過商會這一組織,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參與、經濟發展、社會改良等諸多方面開展了一系列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