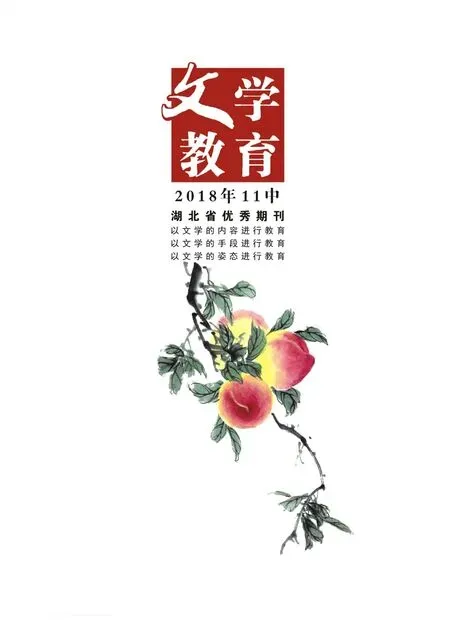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評普玄的《疼痛吧指頭》
王海燕
一.關于絕望的精神啟示錄
普玄的《疼痛吧指頭》雖然只有十來萬字,[1]卻是一部異常厚重的作品。孤獨癥,這個涉及上百萬家庭、戳痛無數父母、歷史短暫卻影響巨大的疾患,近年來漸漸進入公眾視野,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至今仍不得其解的謎一樣的孤獨癥,當它作為一個醫學課題和一個社會話題時,它是客觀的中性的;但當它作為為人父母必須面對的即將與孩子終身相伴的疾病時,它不啻是一場浸染著血和淚、烙印著疼和痛的災難。因此,從題目開始,它就在提醒著讀者只能以虔敬的態度去閱讀,輕松、輕浮、輕快、輕逸,一切的“輕”都與它無關,它的話題是沉重的,精神是厚重的,態度是莊重的。同是以孩子遭受的病痛、苦難為起點,相對于周國平《妞妞》關于生命本體、生與死形而上的哲學思辨,《疼痛吧,指頭》打動人的是那一份人間煙火氣的氤氳;相比于蔡春豬《爸爸愛喜禾》詼諧幽默掩蓋之下的痛苦,《疼痛吧指頭》吸引人的是那一份直面苦難的悲愴、以及對于家族、歷史與現實的反思。面對這樣椎心泣血的作品,純粹技術性的言說與闡釋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它是一部精神自傳,是一部遭逢絕望與絕望周旋又從絕望出發的精神啟示錄。它不是純粹審美的,也不是認識教化的,它是體驗的,它需要讀者以一顆柔韌而又慈悲的心去感受,去體察。雖然作品是以孤獨癥孩子為起點,但它所提出并探討的,并不僅僅是一己一家一個群體的問題,而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一個普通的生命,在無辜遭逢了苦難之后,將何以自處?《圣經》名篇《約伯記》對這個問題的探討至今仍然是人們爭論不休的焦點之一。對于信仰上帝的人們來說,無辜受難是一個關乎上帝與人之關系的宗教問題,而對于無神論的人們來說,無辜受難,to be or not to be,這是一個關乎生命與存在的根本問題。
作為一個有著豐富創作經驗的作家,普玄賦予了這部作品很強的形式感。雖然很多讀者都從“非虛構”的角度進行解讀,但因為它體現出來的對敘事藝術的精湛追求,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部“跨體越界”的小說,[2]它的內涵也可以因為期待視野的不同而在“問題小說”“家族小說”“成長小說”“精神自傳”等不同向度上得到闡釋。小說三個部分的敘述頗為講究,第一部分以“我”春節前夕去紫金小鎮接孤獨癥孩子為線索,大量的插敘、追敘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敘述密度,不僅有孩子從出生到現在的成長與治療線索,也奔涌著一條波瀾起伏的情感潛流:孤獨癥確診之前的焦灼、幻想、甚至自欺,確診之后家庭的解體以及艱難的治療過程,貫穿著對家庭、婚姻、愛情、生命的反思。多次出現的“我”作為父親的“淚流滿面”與孤獨癥孩子的“眼淚汪汪”讓這一部分有著濕漉漉的感覺,仿佛那些句子都是從這一對父子的淚水中打撈起來的,因為經受過人間至情的浸潤,而有著一種直抵人心動人肺腑的力量。第二部分宕開筆墨,以第三人稱敘述“我”的母親常五姐從年輕到年邁先后與三個殘疾人相處、與絕望周旋的一生。母親常五姐不相信眼淚,她以不竭的母愛、強悍的行動掩蓋并戰勝了面對絕望時的軟弱與迷茫,不僅給予了“我”和孤獨癥孩子絕地重生的大愛,更重要的是,她還引領著“我”一步步穿越了精神的沼澤地,成為“我”戰勝絕望的精神導師。第三部分以特寫鏡頭的方式展示了大年三十“我”和孤獨癥孩子回母親家過年的行程,極富象征性地寫出了父子二人是如何沖破絕望找到生機的心路歷程。小說敘事的形式特征、“指頭”的象征寓意、孤獨癥的社會意義等方面都已經有論者做過很精彩的分析,在此不再贅述,以下僅從精神歷程的角度對小說的主旨略作探討。
二.與絕望相遇:日常理性的崩潰
《疼痛吧指頭》是一部與絕望相遇的作品。雖然存在主義哲學的先驅克爾凱郭爾曾從宗教哲學的角度專門討論過“絕望”,但在通常意義上,“絕望”標示的是人的一種情感心理狀態,當人們渴望達到某種狀態,由于受主客觀因素的限制而無法達到目的而產生的一種極端心理體驗,與“希望”相反,比“失望”更甚。當我們的生活按照大多數人的樣子一樣在既定軌道上運行時,比如求學就業、結婚生子,雖然也會遭遇一些大大小小的坎坷和麻煩,一般來說只會停留在失望的階段。換句話說,作為蕓蕓眾生中的一員,只要我們的生活尚在我們賴以生存的日常理性之內,就不會走到“絕望”的境地。所謂日常理性,即支配人們日常生活的理由與理路,是倫理、道德、法律、民俗、知識、價值觀等多種因素的綜合。
敘述主體“我”因為孩子“孤獨癥”的確診猝不及防地與“絕望”狹路相逢。在重人倫血緣的中國家庭,孩子是家庭血脈基因的延續,是父母雙方情感最有力的扭結點,是一個家庭的希望與未來。就像“我”始終記得的,“小時候,在很多個夜里,村民們早早睡了,但是我們家的油燈或者桐子始終亮著,燈光很微弱,但是燈下卻永遠有幾個勤奮學習的孩子。那就是希望,那一盞油燈和無數個桐子照耀著我們兄弟步步升學,進入城市。”孩子是照亮一個家庭的希望之燈,這是日常理性中至關重要的一條原則。但是,對于“我”來說,孩子“孤獨癥,終身疾患”的診斷讓一切都因此而改變。“我們本來朝前跑著,看得見前面的路徑、目標和方向,現在突然出現了一條岔路,前面是什么?我們不知道。”“孤獨癥”不僅僅意味著孩子不能主動開口說話、讀書求學,完成普通人的一生,還意味著父母婚姻破裂、為支付巨額的治療費用竭盡全力的拼搏,還有與之俱來的精神上的孤獨與痛苦。就像克爾凱廓爾所指出的,絕望的折磨是求死不得,“當死亡是最大的危險時,人希望生;但當人認識到更恐怖的危險時,他希望死。所以,當危險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死亡成為人的希望時,絕望就是那求死不得的無望。”[3]這是一般人無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就如上帝選中了他正直的仆人約伯與撒旦打賭,而讓約伯遭受了一系列慘痛的打擊一樣,在小說中,遭逢絕境不只是一個屬于“我”的孤立事件,而是屬于這個家族的一連串事件。除了“我”之外,父親、母親、大哥也都遭遇了各自生命中的絕境。父親與大哥本來有健康的身體,卻都因偶然事件落下了終身殘疾,父親在無辜被批判之后絕望過,大哥在打人事件受到下跪檢討的懲罰之后絕望過。而承受最多最重的絕望則是母親:在她通過考學離開農村的夢想破滅之后,她選擇了嫁給一個有文化的殘疾丈夫,在丈夫身上賭命運,沒想到丈夫挨批下放若干年;她在孩子身上賭命運,老大卻因鏈霉素過敏打聾了耳朵,導致終身殘疾。從不向命運低頭的母親和兩個殘疾人一起拉扯大了其余的五個孩子,并讓他們接受良好的教育,功成名就。但在晚年時她又遇上了一個孤獨癥孫子。這個一生都在與命運搏斗的老人再次選擇了堅強。“她不能去死。她要告訴她的兒子,告訴那個孤獨癥孩子的爸爸,怎么和她一樣,一生和殘疾人相處。她還要告訴她的兒子,怎樣去過令人絕望的生活,怎樣在絕望里面,尋找生機。”
每一次絕望伴隨的都是日常理性的崩潰。殘疾父親一生沒有“狼氣”,盡管滿腹詩書,他懼怕任何的權力,在現實生活中無力保護自己,更遑論家庭?殘疾大哥一生沒有婚姻家庭,孤獨癥孩子也無法過正常人的生活。他們遭逢的超常的痛苦不僅使他們本身,也使最親的親人成為了異于常人的孤獨個體。世間的功名、榮譽、幸福、歡樂都無法共享。這樣的絕境,因其超出了一般生活經驗的范疇,它也就成了日常理性無法應對的難題。很多人選擇了逃避,而作者的選擇是——接受!“接受一種事實。不單單是孤獨癥,還有其他的一切一切。把衣服一件件脫掉,脫光,全身赤裸,沒有面子,沒有隱私。”[4]日常理性就是保障我們展開日常生活的“衣服”,當你和這個世界赤裸相見的時刻,就是日常理性崩潰的時刻,同是也是對這個世界無所畏懼的時刻。這是一個轉折點。它既可以向下沉淪,也有可能向上超越。
三.從絕望出發:宇宙理性的覺醒
日常理性其實是一種實用理性,按照李澤厚的解釋,實用理性乃是經驗合理性的概括或提升,它關注于現實社會生活,不重思辨理性、超驗價值的追求。而人作為精神的存在物,在被日常理性拋出經驗的有限世界之后,只要他有足夠的勇氣與堅韌,他還有可能走向一個更闊大更深邃的生存之境,他會發現在熟悉的日常理性之外,還存在著更玄妙更神奇的宇宙理性。宇宙理性,簡言之,也就是天地和自然之道,而不僅僅是人之道。由絕望走向宇宙理性和真理本源,甚至也是很多哲學家的成長之路。俄國哲學家舍斯托夫在研究克爾凱郭爾時發現,“對于克爾凱郭爾來說,哲學絕不是心靈的純智力活動。哲學的基礎不是像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教誨的驚奇,而是絕望。人的思想在絕望和恐懼中得到再生并且獲得新的力量,這種力量把人的思想引到對于其他人來說不存在的真理本源。”[5]
在小說中,首先學會從絕望中出發的仍然是母親。在她三十歲那年,十歲的大兒子被確診為“終身殘疾”,得知消息之后,“奶奶夜里沿著漢水往河西走。左邊是她四十二歲的殘疾丈夫,右邊是她十歲的殘疾兒子。她走幾步要一根煙吃,沒有煙吃她走不動路。”但她接受了這個事實,因為她那時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她不能倒下。她讓大兒子輟學回家幫她種地養活弟弟妹妹,將希望轉而寄托在其他孩子身上。當最有希望的“少年之星”三兒子、也就是敘事主體、孤獨癥孩子的爸爸在高考前因寫情書被學校開除之后,巨大的絕望幾乎擊倒了她。母親離家出走了一個多月,最終,她又回到了這個家。她以帶著孩子們觀看父親和大哥墾荒的方式讓三兒子及所有的孩子都明白了一個殘酷的事實:他們是靠兩個殘疾人供養著上學的!這是小說的敘述者“我”第一次深刻感知并體驗到“絕望”。這也是母親開出的一劑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猛藥!“那個干燥的東西就是絕望。絕望是干燥的,絕望是繃緊的。絕望和面前山坡上秋天的枯草一樣,一望無際,靜默無聲,一點就著”。幾十年后,他從一陣鈴鐺聲中悟到那是母親教給他的生存之道,“它告訴我,絕望要盯著看,你盯著一塊石頭和凝固的堅冰。但是到消失的時候,再堅硬的東西也會一下子消失。”
在對待孤獨癥孩子的問題上,也是母親先有覺悟。“這孩子有福”,“憑什么是你養了他一輩子?憑什么不是他養你一輩子?”在“我”還囿于日常理性陷在悲傷、絕望、沮喪之中時,一生與殘疾人生活在一起的母親率先跳出了日常理性的束縛,打破了世俗經驗的價值體系,這既是母親對她自己一生反抗絕望的生存經驗的總結,也是母親宇宙理性的覺醒。在母親的點撥下,“我”也漸漸學會以更宏闊的視野去重新思考世界和人的關系,去反思苦難之于個體的價值,無論是在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都獲得了全新的體驗。“應該有很多個世界,包含在我們這個世界之中,或者包圍著我們這個世界,應該有比我們更大的和更小的世界。”當人跳出了日常理性的束縛,以宇宙理性去看待生命存在時,你會發現,處處都是生機,萬物都各有其價值,包括孤獨癥在內的苦難也只不過是宇宙萬物無數奧秘中的一個。“你會發現災難沒那么可怕,惡人沒那么可怕,死亡也沒那么可怕。你會發現那些災難和惡人,他們沒那么強大,他們還有些慌張,他們到底心虛,他們原來是一個紙人。你會發現,你這個時候不再需要退路,也不會孤單,你永遠不會被拋棄。因為你面對的是天地和自然。”[4]創作談表明,作者其實已經洞悉到日常理性的有限和宇宙理性的奇妙,那一串串奧秘正等待著歷經考驗的人們去領悟,去破解。
克爾凱廓爾認為,消除絕望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自我本身的力量,一是通過信仰上帝。但是他的宗教背景使他否認了前者,認為對上帝的信仰才是對抗絕望的永恒安全的抗毒劑,因為上帝是萬能的,在上帝那里一切皆有可能。[3]對于并無基督教背景的敘述主體來說,他選擇的是第一條途徑——“你是你自己的神,你的心就是你的世界。”在絕望的時候,他會去看兒子,“我問他我該怎么辦”,“但是和一個無法回答的人說話,你會得到另一種回答。因為你實際上是在問自己,你是在問你那顆心。你一次又一次地問,其實答案已經在你心中。你是你自己的神,你的心就是你的世界。你一遍一遍把自己問安靜下來,你會得到正確答案。這個答案在當時可能是不可思議的。”這個看似悖謬的過程正是宇宙理性的覺醒。中國哲學中最具宇宙理性的老子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人的心靈本來是虛明寧靜的,但往往為情緒、欲望所蒙蔽,因而觀物不得其正,行事則失其常。一旦使它回到虛明寧靜的狀態,就復歸到人之本性和自然常道。在“我”和孤獨癥孩子的對話中,那一種更接近世界本原和生命真諦的宇宙理性得到了越來越清明的呈現。
當“我”從孩子的孤獨癥中走出來,覺醒了的宇宙理性仿佛賜予“我”一雙特別的慧眼,類似于舍斯托夫所謂的“第二視力”,它不僅能夠洞察生命與人性的深度,也能看取世界和宇宙的廣度。所以,全書并沒有僅僅沉溺在一己的悲傷之中,不僅挖掘到了家族之中那一股潛藏的不屈的生命力,也從各式各樣的醫生、保姆、托管家庭中領略、體味到生活百態與生命存在的真諦:有世事的蒼涼與無奈,也有人性的善良與溫暖;有遭受苦難的慘痛與悲愴,更有捍衛生命尊嚴的激情與榮光。它向我們呈現出無辜受難的個體依然可以有尊嚴地生活著,依然可以從深淵走向光明!在作者舒展自如的敘述之中,既有形而下的城市與鄉村的比較、婚姻與家庭的反思,也有形而上的對生命與自然法則的敬畏、語言與世界之關系的思考、愛和理性的體悟,所以,全書單純但絕不單薄。讀者看到,敘述主體那個越來越深厚博大的靈魂經過血與淚的冶煉而變得越來越有光澤,一個突破了光明/黑暗、希望/絕望二元分別的精神世界正變得日益豐贍。這也再次驗證了魯迅翻譯裴多菲的那句話: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