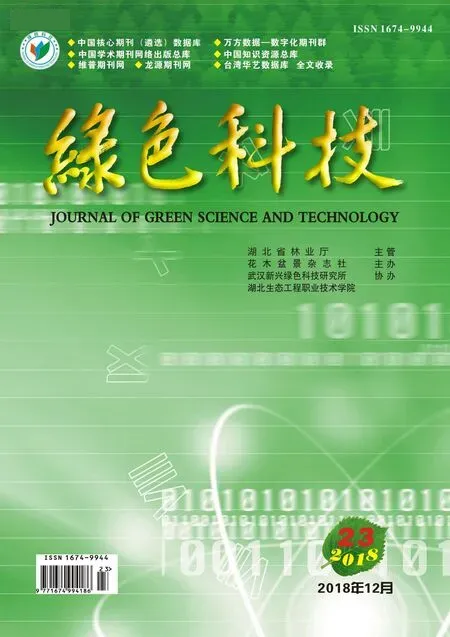中國高校學費制度研究
李 婧
(鹽城師范學院,江蘇 鹽城 224007)
1 引言
清末“新政”時期大學建立, 高校學費制度隨之出現,一直持續到國民政府時期,新中國成立后即被廢止。在多次推動教育改革的同時,是否實施學費制度的爭論也開始了。學費制度共分為4個階段逐步實施,具體過程如下。
2 大學學費制度變遷過程
2.1 大學免費教育階段:1949~1988年
1949年中央政府調整大學結構,強制廢止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使其與國立大學合并,辦學模式也從美日轉向前蘇聯,并取消了學費。國家通過高考,按計劃招生,不僅承擔一切費用、供獎學金,還統一分配就業。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免費教育,是國家統一管理人力資源的手段。國家作為唯一的利益主體,依靠強大的控制力推動大學發展。高校接受政府全額的財政支持,在政府限定的教育目標和計劃下培養人才,實際上是以不均衡的交換關系代替市場的等價關系。改革開放后,計劃經濟已不符合時代的發展,國家通過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改革來完善不合理的體制。在這過程中,學費制度的改革也應運而生。
2.2 大學學費試行階段:1989~1993年
1989年,國家物價局、教委和財政部一起頒布《關于普通高等學校收費學雜費和宿舍費的規定》[1],從此大學本科和專科新生(師范高校除外)開始繳納學費。1989年教育部發布《關于高等學校畢業分配制度的報告》,指出“除特殊規定外,大學生需繳納學費。裁定繳納學費時,要考慮家庭經濟水平和實際承受能力,規定學費每年100~300元是相對合理的”。
1993年中央和國務院公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調節政府和大學、中央和地方、 教育部和其他部門的關系。高考招生制度從政府計劃性選拔中脫離,調整為國家指令性招生(包括公費生和定向生)和社會調節性招生,而委托生和自費生所占比例逐漸擴大。綱領中明確規定“改革學生上大學由國家包下來的做法,逐步實行收費制度。高等教育是非義務教育,學生上大學原則上均應繳費”[2]。
2.3 大學學費形成初期階段:1994~1997年
1993年以東南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為試點,經歷3個階段落實高校學費制度。第一階段,1994年中央部屬50所高校率先施行;第二階段,1995年在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46所高校中實施;第三階段,1997年除農林、師范等大學和專業外,其他大學和專業開始實施。
1995年,國家相關部門頒布了《國家教委、國家計委、財政部關于1996年普通高等院校收取學費的有關問題通知》。普通高等學校的本科生,一般專業學費標準調整為1500元;藝術類院校學費分為3種情況,收費標準分別為2640元、4000元、6000元;外語等專業是一般專業的兩倍以內;其他特殊專業,原則上不超過一般專業的50%[3]。另外還規定了師范、體育、民族、航海和農林等專業的學生,仍按國發〔1989〕19號規定免繳學費。
1996年頒布的《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學費包括學費和住宿費,住宿費收費標準按照實際成本確定,不得以營利為目的。學費標準須由省級部門提出方案,報省級人民政府批準后執行。學費收取實行“老生老辦法,新生新辦法”,按學年或學期收取,不得跨學年預收;屬地化原則,即同地域的高校都遵守當地省級政府的規定。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應酌情減免收取學費。強化學費管理和監督,嚴肅處罰違規行為。
2.4 大學學費全面實施階段:1998年至今
199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高等學校的學生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繳納學費。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可以申請補助或者減免學費”, “高等教育實行以舉辦者投入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擔培養成本、高等學校多種渠道籌措經費的機制”[4]。從此開始,大學學費制度進入全面實施階段。
自2001年起,國家發改委、教育部和財政部又多次聯合發文,一再強調“高校學費和住宿費標準必須要穩定在2000年的水平上,不得提高”。
2007年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意見》,文件中明確規定“今后5年各級各類學校的學費、住宿費標準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的相關標準”。
2012年,關于學校收費標準的國家層面系列政策相繼到期,有些省份就開始啟動了高等學校收費標準的制定工作。
國務院于2015年印發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中,非常明確地要求“按照平穩有序、逐步推進原則,合理調整高校學費標準,進一步健全成本分擔機制”。這就意味著開始從國家層面,調整高校學費,增加投入。
3 高校學費制度的影響
3.1 高校自由度加強
高校學費制度的實施規范了政府、高校、學生之間的利益關系,是同高校招生制度、高考制度等高校改革并行的。脫離了計劃經濟體制下、隨中央的指令性計劃培養國家所需人才的體制。開放的、順應市場經濟的人力物資管理,教學研究、專業體制和自由競爭機制被激活。
3.2 高等教育機會擴大
中國經濟急速發展,居民所得的增加改變了家庭消費觀念,家長對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愿望更加強烈。高等教育不是義務教育,學生在接受教育的同時要負擔相應的學費。財政全額承擔的體制下,高等教育是精英模式,教育機會被家庭經濟較好的個人占有。學費制度實施后,政府和社會投資增加,更多人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為教育機會擴大、社會公平實現提供了契機。
4 高校學費制度的問題
4.1 政府介入
學費制度在中央主導下、采用上命下達的方式推進。雖然政府充分考慮了各方的利益,但當今中國政治體制和民主化不成熟,政策制定只能偏向權利集團。高校也屬于利益集團,雖沒有學費制定權,但所提出的學費標準不僅沒有政府的反對,政府和物價部門反而使學費標準正當化。這反映了計劃經濟下形成的政府強力介入,如今依舊起作用。
4.2 經濟負擔加重
從2000年直到現在,中國的物價水平持續不斷地提升,各個高校辦學成本自然也會大幅上升,然而定死的學費標準讓各個高校感到較大經費壓力。據公開的信息顯示,2013~2014年,很多省、直轄市不得不調整本地高校的學費標準,大部分專業的學費漲幅在20%~35%。上漲的學費給渴望高等教育的家庭和學生更多的經濟負擔,越來越多學生無力繳納學費。
4.3 財政支援不足
2000年的時候,中國的公共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不但沒有達到法律規定的4%,和前幾年相比,還有所倒退。2002~2005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所占GDP比例逐年降低到2.8%左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約為7%,而發達國家平均達到了9%,經濟欠發達的國家也平均達到了4.1%。公共教育經費的投入不足形成了嚴重的教育欠缺,這種欠缺又導致了教育公平失衡、學生家庭經濟負擔過重等社會問題。
4.4 解決對策缺失
雖然制定了多種政策法規,但效果并不理想。助學貸款和學費標準問題一直懸而不決。①助學貸款問題沒有改善。社會兩極分化嚴重,農村和城市貧困生因學費而輟學。貸款申請限制太多,只有一部分學生能夠申請,實施過程中公平性問題無法保證。②生均教育培養成本沒有全國標準。例如,教研、教學設施等教育經費是否應包含在內的議論一直存在。因此,全國高校學費標準千差萬別。
5 措施和對策
5.1 改善政府和大學的隸屬關系
應該將學費裁定權下放給高校,高校可以自由裁定學費。現今,政府和高校的利益關系并不明確,在政府宏觀控制和高校自由度不高的情況下,政府不會將學費裁定權下移。高校應強化自由度,完善多種制度措施,在市場經濟形成過程中成為獨立運行的法人。
5.2 分層次分專業調整學費
區分學校層次和專業分類,以此為依據對學費進行結構性調整。如湖南,一本學校漲幅在18%~30%,二本學校漲幅約為6.7%。加大各個高校自主制定不同專業學費標準的權限,體現熱門專業的價值。結合就業導向和市場經濟的調節機制。不同專業的學費應該依據就業市場的實際供需來確定標準:供不應求的專業可以考慮適當的逐步提高學費標準,就業前景、招生不足的專業降低收費,非國家必須保留的專業可以考慮停辦。
5.3 提高教育經費支出
《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規定的教育預算要保證達到4%。高校的收入一般來自于:政府撥款(根據收支兩條線原則,學費收入不直接給學校)、社會捐款和經營性收入。絕大部分公辦高校還是主要依賴于政府撥款,而政府對大部分高校的撥款原則是“中央與地方共同承擔,但以地方財政為主”。在此前提下應該多渠道募集資金,推動高等教育快速進入大眾化階段。
5.4 建立多方聽證會制度
目前并沒有統一、全國性的學費標準,標準制定困難重重。同時,與學費緊密相關的政府、高校、家長,三方的利益關系存在一定的矛盾。眼下,我國一些省市正準備上調高校學費標準,但上調學費標準,遭遇質疑,要回應質疑,就必須公開學校收入來源、辦學成本,列出充分的漲學費理由,舉行家庭、學生代表可以參與的高校學費調整聽證會。
5.5 為庭經濟困難學生提供救濟
從各個國家級管理部門出臺的系列文件,到各省市自行制定公布的學費調整方案,基本都明確提出:“不能因學費調整而影響大學生的正常學習和生活”。國家、省、市有關部門應該完善有關“獎、助、補、減、免”的政策,進一步明確資助標準和規定,研究如何救助絕對貧困生,如何減少學費上漲給大學生帶來的經濟壓力,相關部門要制定出更完善、更具備可操作性的貧困學生上大學的費用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