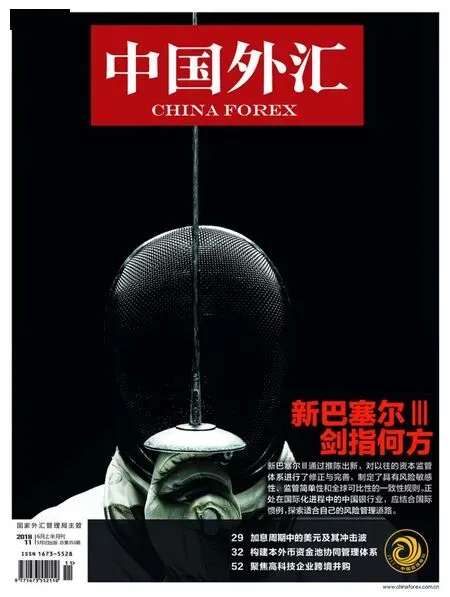新巴塞爾Ⅲ劍指何方
文/本刊記者 孫艷芳 王莉
新巴塞爾Ⅲ推陳出新,對以往的資本監管體系進行了修正與完善,集中體現了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的監管新理念。
福之禍所倚。歷史經驗證明,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是其監管改革日臻完善的重要機會,巴塞爾協議也不例外。
此巴塞爾與彼巴塞爾的異同
1974年,前聯邦德國赫斯塔特銀行和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倒閉,直接催生了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成立和第一個巴塞爾協議的誕生。此協議經過兩次修改,最后于1988年形成了巴塞爾協議Ⅰ。該協議為銀行業建立了國際通用的資本充足率標準和監管原則,在推進全球銀行監管一致化和可操作性上具有重要意義。
巴林銀行倒閉事件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則是巴塞爾協議Ⅱ誕生的重要背景。該協議在2006年定稿,為全球銀行業搭建了基于資本監管、外部監管和市場約束三大支柱的統一監管體系,并將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提升到了與信用風險同等重要的地位,提供了更為全面的風險管理框架。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再次反思管理理念,并于2010年年底推出了巴塞爾協議Ⅲ。之后經過長達七年的研究討論,2017年12月8日,巴塞爾委員會又發布了《巴塞爾Ⅲ:后危機改革的最終方案》(下稱《最終方案》),并將于2022年開始正式實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巴塞爾協議的演變,正體現了此精髓。那么最新出臺的《最終方案》向我們傳達了哪些新的監管趨勢呢?
專家普遍認為,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并重,是《最終方案》最大的特點。范小云、王道平在《巴塞爾Ⅲ在監管理論與框架上的改進:微觀與宏觀審慎有機結合》一文中指出,之所以在巴塞爾Ⅲ中注重微觀與宏觀審慎監管的結合,是與二者的特征分不開的:微觀審慎監管防范的是單個金融機構的風險,并不考慮單個金融機構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因而在控制標準設定上,其方法是自下而上的,個體之間的相關性常被忽略;而與之對應的宏觀審慎監管,是為了防范金融系統范圍的風險,在審慎控制標準的設定上,宏觀審慎監管是自上而下的。
每次金融危機都會揭示出不同的金融風險。在微觀審慎監管方面,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中,巴塞爾委員會發現,系統流動性會瞬間枯竭。這提醒監管當局從流動性風險角度加強監管的重要性。從監管指標的范圍看,各國監管者已不再將資本作為唯一關注的指標;從監管關注的情景范圍看,監管者已也不再僅關注正常市場條件下的金融安全,而是對極端壓力情景下的金融穩定給予了更多的關注。所以微觀審慎監管主要從資本質量、透明度及風險覆蓋、杠桿率及流動性要求方面進行了改進。而在宏觀審慎監管方面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一是在時間維度上,處理金融體系隨時間變化的整體風險,強調金融系統的“順周期性”;二是在橫截面維度上,重在某一時點風險在金融系統內部各金融機構間是如何分布的,關注相關的破產風險。
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殷紅告訴記者,《最終方案》還有兩個值得關注的地方:一是進一步強化了資本約束的理念。從巴Ⅰ、巴Ⅱ到巴Ⅲ,都是圍繞資本進行監管。銀行是經營風險的,如果經營的不好,會帶來損失,包括預期損失和非預期損失。其中的預期損失可通過撥備進行吸收,而非預期損失只能通過資本吸收。所以巴塞爾的核心要義是資本監管,強化了資本約束的理念。二是更加重視通過資本的管理促進銀行以及監管構建風險管理體系。在殷紅看來,“這個風險管理體系包括風險管理架構、制度、流程、信息以及內部監管和外部監管,可以不斷優化銀行風險管理能力及不斷提升監管部門對銀行的監管水平”。
全球銀行業是否同此炎涼
《最終方案》的發布標志著巴塞爾委員會完成了資本充足率監管三個基本要素——資本工具合格標準、風險加權資產計量方法和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的改革進程,也意味著后危機時期資本監管國際規則改革的塵埃落定。那么,《最終方案》的實施又會對全球銀行業的運行產生哪些影響呢?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總體上,巴塞爾協議每修訂一次,對國際銀行業來說,其實都面臨著新一輪的風險體制改革的調整,包括新一輪新規則的修訂和適應,和新一輪風險管理系統和數據搜集系統的建立。相比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銀行業,發達經濟體的銀行業擁有更好的數據積累和種類更全的金融產品,所以他們有更多的話語權。不過,巴塞爾協議關于風險管理的框架也在客觀上為新興經濟體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水平快速向先進水平的靠攏提供了一條捷徑。”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丁志杰認為,《最終方案》也有利于銀行間的公平競爭。他解釋說,《最終方案》的修訂主要是完善風險資產的計量,針對過去內部模型法運用過程中與標準法之間的差異,對內部模型法進行了約束規范,以解決資本充足率計量的套利問題。從過去使用內部模型法的情況看,大銀行使用得多,因為模型法計算出來的風險資產要比標準法低,對大銀行有利,而且不同地區的銀行內部模型法計算出來的差異也很大。鑒此,2017年版巴Ⅲ規定,銀行采用模型法計算出的風險加權資產的結果,不得低于標準法結果的72.5%。這有利于促進不同規模、不同地區的銀行間公平競爭。
殷紅認為,相較而言,《最終方案》對我國商業銀行的短期影響不大。因為我國銀行業務結構相對較為單一,資本充足率水平較高,達到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并不難。但新規則對我國商業銀行的長期影響則不可小覷。原因在于我國商業銀行盈利模式主要還是以規模增長帶來的息差收入為主,國內資本市場還不夠發達,經濟持續增長和經濟結構轉型對銀行信貸的依賴還很嚴重,加上近年來監管要求不斷趨嚴,因此中國銀行業對資本的渴望將更為強烈。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也指出,對于中國銀行業來說,核心一級資本、一級資本和資本的趨同,一直是資本結構的特點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有效創新工具造成的。長期看,這將直接加大銀行的資本壓力。
新巴塞爾Ⅲ能否包治所有風險
在巴塞爾協議Ⅲ之前,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已經先后誕生了兩個巴塞爾協議,對全球銀行業的監管也在不斷強化。然而,恰恰在同一時期,全球性的或區域性的金融危機卻頻頻發生,大銀行和金融機構時有倒閉。那么,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催生出的巴塞爾協議Ⅲ,又能否真正實現對銀行整體風險水平的管控,有效避免未來發生新的金融危機呢?
對于這些質疑,可從風險管理手段、資本充足率等方面進行探討。
魯政委表示,風險管理手段很多時候都是走在金融業務的后面,所以,很難說巴塞爾協議Ⅲ的修訂能夠讓銀行和金融體系未來不會出現危機。
丁志杰告訴記者,《最終方案》的著眼點還是資本充足率,將資本要求作為銀行風險水平控制和外部監管的基礎,應該對金融穩定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也不能過高估計其作用,而且正面作用也不是自發就能實現的。在過去40年里,巴塞爾協議不斷發展變化,作為外部監管的核心——資本充足率要求不斷趨高;但現實中,無論是微觀層面還是宏觀層面,金融穩定并沒有明顯提高。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不斷提高趨嚴的資本要求也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如銀行為了維持資本利潤率而從事新的高風險業務等。這會導致金融不穩定而不是更穩定。
正如原中國銀監會審慎規制局副局長王勝邦在其《后危機時期國際金融監管改革》一文中指出的,金融體系始終處于演變之中,甚至會發生突變;因此,金融監管改革雖然有助于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及影響,但無論改革多么徹底,都不可能阻止金融危機的發生。他認為,監管當局必須警惕宏觀經濟、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行為變化可能導致的新生風險。未來一段時期,影響全球體系穩定性的潛在風險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回歸常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以及可能誘發的金融市場動蕩,如2018年2月,全球股市出現的過度波動。二是金融科技發展帶來的挑戰。科技與金融的深度融合不僅引入了新型的金融市場參與者,而且還會推動傳統金融機構轉變經營模式,而這些對金融穩定的潛在影響需高度關注。三是杠桿率居高不下的隱憂。近年來,發達經濟體公共部門去杠桿進程乏善可陳,新興經濟體私人部門杠桿率也持續攀升,顯著壓縮了宏觀經濟政策空間,增加了實體經濟增長和金融市場運行的不確定性。
具體到中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產業升級與區域金融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李虹含告訴記者,從中國資本監管與風險管控的監測指標中可以發現,在巴塞爾協議Ⅲ實際操作過程當中,銀行的企業融資業務創新了多層嵌套、通道業務等多種表外融資模式,以減少銀行資本消耗,并盡量減少風險資本計提。而監管部門在發現了上述非標融資多層嵌套與通道套利之后,也下發了多項文件以消除監管套利空間,如2016年原銀監會的82號文、中國人民銀行的《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及銀保監會的《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等。然而,銀行總會圍繞監管指標尋找新的合規經營模式,因而在巴塞爾協議Ⅲ中國化的道路上,也仍需監管部門協同金融機構群策群力,不斷發現銀行經營與資本監管過程中的不足之處,以加以彌補。李虹含強調,雖然銀行加強資本監管可以提升表內風險的管控水平,但對于表外、表表外和非標、非非標類為應對監管而生的新型融資手段和相伴而生的風險,仍需繼續加以關注。
中國銀行業如何迎接巴Ⅲ
根據巴賽爾協議Ⅲ的要求,并結合中國銀行業改革發展的實踐,中國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審慎資本監管框架。2012年6月發布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形成了涵蓋最低資本要求、儲備資本要求和逆周期資本要求,以及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等多層次的資本監管框架,并整合了巴塞爾委員會在風險加權資產計量方面的核心要求,拓展了風險覆蓋范圍,提高了監管資本的風險敏感性。
此后,相關監管部門還發布了一系列細化和配套的規范性文件,包括《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關于實施〈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過渡期安排相關事項的通知》《中國銀監會關于商業銀行資本工具創新的指導意見》《關于商業銀行實施內部評級法的補充監管要求》以及《關于商業銀行資本構成信息披露的監管要求》等十余項文件。從中反映了中國版“巴Ⅲ”的特點:一是資本的規模與質量并重,讓銀行有足夠的損失吸收能力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危機;二是調整和完善風險權重體系,如根據中國的情況,上調國內銀行債權三個月以上的風險權重等。
中國版“巴Ⅲ”實施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實力持續充實,風險管理能力和風險抵御能力進一步提升,“逆周期”經營能力和經營的穩定性也有所增強。根據原銀監會的數據,2010年(巴塞爾協議Ⅲ公布當年)至2017年,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凈額增長2.15倍至16.78萬億元人民幣,資本充足率從12.20%升至13.65%。
但隨著資本約束越來越強,中國銀行業以往靠規模擴張的路徑將受到嚴峻挑戰,內涵式發展之路有待破題。殷紅認為,銀行對此可從三個方面著力:一是持續關注國際監管動態,積極做好應對準備。二是進一步拓寬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渠道。我國商業銀行應在《關于進一步支持商業銀行資本工具創新的意見》的指導下,合理規劃資本補充計劃,加強固定期限資本債券、轉股型二級資本債券等資本工具的創新力度。三是加快銀行轉型,形成資本集約型發展模式。商業銀行應借此機會實現從“重資本型業務”向“輕資本型業務”的轉型,改變過去對規模擴張的高度依賴,重點發展理財、結算、銀行卡等中間業務,培育新形勢下的新增長動力,形成“輕資本”的資本集約型發展模式。
我們應清醒地看到,雖然《最終方案》通過推陳出新,對以往的資本監管體系進行了修正與完善,但實踐已一次次證明,外部監管并非萬能的風險防火墻。而且根據西方和歐美發達國家銀行業經驗所確定的監管指標,能否精準地刻畫中國銀行業所面臨的風險也有待檢驗。正處在國際化進程中的中國銀行業,應結合國際慣例,探索適合自己的風險管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