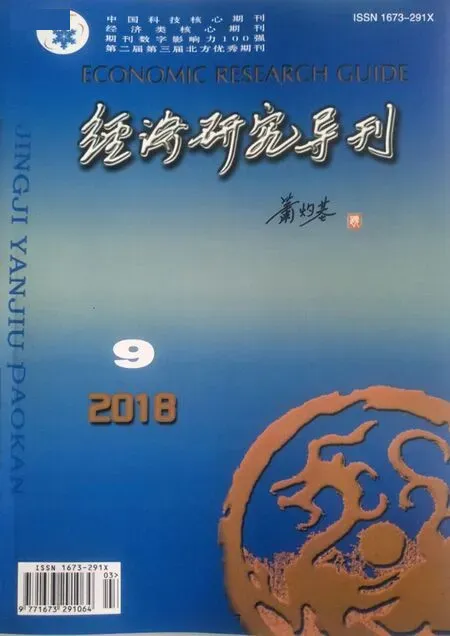關于政治成本與環境信息披露的研究綜述
李彤彤,孫興娥
(山西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太原 030006)
一、政治壓力與披露動機
對于上市公司披露有關環境信息的動機,DeVilliersC(2006)認為可以用合法性來解釋。合法性最早由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他認為合法性是所有組織存在的基礎。環境信息的披露正是組織遵從合法性的體現。然而事實上,正如Orsato(2006)的研究表明,環境信息的披露并不會給企業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為了塑造環境友好形象,企業改進生產設備和引進環保技術反而會增加企業的經營開支,因此企業缺乏主動提高環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動力。同時,環境信息的披露也可以給企業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倪娟(2016)以滬深兩市重污染企業為樣本,研究發現其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越高,可取得的銀行借款越多。故而霧霾發生后,企業有理由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以獲得銀行信任。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實施情況的報告披露的數據,2015年,各級環保部門罰款超過42.5億元,比2014年增長34%;2015年共破獲各類環境污染犯罪案件6 035起,比2014年增長16%。客觀來看,企業主體責任在規則層面日臻完善,唯需實踐中的嚴格執行和落實。
二、產權假設
對于控股權對社會責任披露的影響如何,歷來有過許多研究,但是結果不盡相同。企業通過履行社會責任進而獲得政府好感對于企業獲取競爭優勢是十分必要的,如企業通過捐贈、環境保護等活動可以幫助企業在投資建廠、項目審批、稅收優惠中獲得收益(梁建、陳爽英,2010)。在此背景下,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表現出明顯的尋租傾向,因為國有企業在政策導向方面具有先天優勢,相較而言,非國有企業的尋租傾向更加強烈(李四海等,2015)。據環保部消息,環保部印發《“十三五”環境監測質量管理工作方案》,旨在完善監測技術和質控體系,滿足環境監測管理需要,提升環境監測工作的科學性和規范化水平。由此可以推斷,在“PM2.5爆表”后面臨的嚴格環境規制下,非國有企業提升環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動機更強。也有學者認為,環境規制對重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具有“區間效應”,對國有重污染企業呈“U”型關系,而民營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呈倒“U”型關系(李強、馮波,2015)。尹開國等(2014)以 2010—2011年發布責任報告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相比于民營控股上市公司,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履行披露水平更高。
三、規模假設
對于環境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研究始于國外,Patten(1992)對美國上市公司年報進行研究,結果證實了大規模企業由于受到的關注更多,通過年報及其他渠道公開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的可能也更高。近年來,國內對環境信息披露影響因素的研究也日益豐富,李晚金等(2008)的實證研究表明環境信息披露水平隨著企業規模正向變動,鄭春美、向淳(2013)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由此可見,雖然研究的市場不同,但規模假設始終是成立的。
四、股權集中度與會計信息披露水平
在現有的文獻中,關于公司治理特征對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影響的研究很多,成果也很多。李晚金等(2008)將赫爾芬德指數,即把上市公司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作為股權集中度的衡量指標。結果證明,股權集中度對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沒有顯著影響。也有學者的研究表明,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越高,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就越低,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與控股股東的比例呈負相關關系。Haskins等(2000)將研究著眼于不同國際市場的對比,結果表明,由于歐美國家股權分散,數量眾多的股東會要求較高的信息披露水平;而亞洲的公司股權相對集中,對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要求較低。
參考文獻:
[1]倪娟.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與銀行信貸決策——來自我國滬深兩市A股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經驗證據[J].財經論叢,2016,(3):37-45.
[2]吳德軍.責任指數、公司性質與環境信息披露[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1,(5):49-54.
[3]王建明.環境信息披露、行業差異和外部制度壓力相關性研究——來自我國滬市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的經驗證據[J].會計研究,2008,(6):54-62.
[4]梁建,陳爽英,蓋慶恩.民營企業的政治參與,治理結構與慈善捐贈[J].管理世界,2010,(7):109-118.
[5]李強,馮波.環境規制、政治關聯與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經驗證據[J].經濟與管理,2015,(4):58-66.
[6]尹開國,汪瑩瑩,劉曉芹.產權性質、管理層持股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4,(9):114-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