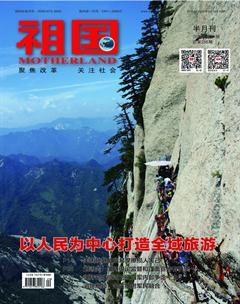文化研究視角下近代全盤西化思想的可行性分析
胡冶天
摘要: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觀以文化的整體性與工具性定義為基礎,而胡適的全盤西化觀則是基于實用主義的符號體系的再建構,兩者理論基礎的差異決定了方法以及愿景的差異。霍爾將文化定義為建立在事物、概念以及符號關系基礎上的意義,胡適希望再建構的是建立在基礎符號之上的二次建構的符號體系,也就是羅蘭巴特所說的神話,而羅蘭巴特借神話表達了意識形態的作用,根據阿爾都塞的理論,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統治階級維持現有社會結構、實現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工具,因此胡適對于文化成分的系統改造離不開政治的改造。陳序經的整體觀比胡適更具有長遠的眼光,但威廉斯、湯普森等學者提出文化受階級、語言的限制,陳序經將文化視為單純的工具,未考慮到這種限制,因此也不可行。雖然兩人“全盤西化”的愿景都未實現,但作為一股力量促進了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吸取。在中國文化已經納入世界化軌道的今天,霍克海默的預言仍然值得注意,中國依然要保持對“西化”問題的思考。
關鍵詞:文化研究 全盤西化 意識形態 符號
一、文化研究學派理論引入
文化研究學派最早興起于20世紀60、70年代的英國,該學派立足于大眾文化傳播,反對批判學派的精英主義傾向,而更關注微觀經驗的世俗生活,提出并描述了意識形態對于文化的控制作用。在文化研究學派發展的過程中,它吸收了許多方法與理論并逐漸成熟。
要研究文化,首先就需要對文化做一定定義。傳統的文化定義傾向于將文化描述為“被思考過的最好的東西”,而主要關注在文學、藝術中的文化表征。人類學、社會學領域則將文化定義為集團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共享價值。文化研究學派也曾經陷入傳統的文化定義,李維斯認為拯救社會需要依靠文學藝術的力量,要恢復古老的價值觀念,霍加特用自身經歷描述工人階級,將流行音樂等大眾文化現象當作一個個文本分析,為早期的文化研究提供了范例。直到霍爾、威廉斯等學者提出對于文化的定義,文化研究學派的研究取向逐漸清晰。
霍爾將文化定義為一種意義的強調,不是一種事物,而是一種實踐。人對磚和灰漿的使用使之成為房屋,對房屋的談論和做為使之成為家,因此意義通過實踐產生。霍爾著力于研究文化傳播的模式以及文化中的符號性,在他的理論下,文化在集團成員的意義生產和交換過程中得以體現,是人理解世界的方式,而意義是一種對話,永遠只能被部分的理解,因此文化的傳播過程中一定包含著某種主觀的傾向性。霍爾通過編碼與解碼的模型解釋這種傾向性,并用心理語言與表象這兩個表象系統來分解文化。霍爾也將文化的意義過程區分為事物與概念的關系和概念與符號的關系,聯系事物、概念、符號的過程就是表征過程。例如,紅綠燈的紅色和綠色便從單純的視覺刺激被人為化為一種顏色,這是事物與概念之間形成的關系,而紅色代表“停”而綠色代表“行”則是概念與符號之間形成的關系。這也意味著,表征通過語言產生意義,當人對事物擁有概念,就知道了意義,當有了語言,就可以傳達意義。因此,語言與文化有著緊密的關系。
威廉斯則進一步研究了文化與語言、政治之間的關系,建立起了一套更完整的文化研究體系。威廉斯認為共同的生活經驗是一種“感覺結構”,這種感覺結構就是一個時期的文化,而文化生成的過程是人們對周邊環境的改變做出整體的性質評估的過程,是一個慢慢獲得重新控制的過程。威廉斯認為共同文化只能建立在生命的平等之上,只有這樣,文化傳播才能擺脫政治當局通過手段操縱烏合之眾的角色。湯普森認為文化是個階級、集團斗爭的產物,因此應該根據階級進行區分。威廉斯不認可湯普森這種馬克思式的文化區分標準,他認為文化應該根據語言進行區分,因為文化先于階級存在。文化研究學派的后期發展也確實傾向于威廉斯的方向,德里達認為不存在絕對的“在場”,因此我們除文本外一無所有,“再現”就是我們擁有的一切,階級、性別、種族領域都是通過再現建構起來的。
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理論使這種對于文化與階級、政治的關系的研究方向更加清晰,導致晚期的文化研究與意識形態的研究交織在一起。任何社會形態都產生于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阿爾都塞將國家機器分為暴力的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負責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即剝削關系的再生產,這種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對于社會的文化至關重要。從中世紀至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從教會變為學校,這些主要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也就成為了一個時代文化的主導力量。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是“一般的意識形態”,阿爾都塞認為每個階級、每個領域都有獨特的意識形態,而這些意識形態之間沖突的結果就是一般的意識形態。最早的馬恩的“意識形態”游離在一個階級特有的信仰系統和偽意識兩種界定之間,葛蘭西認為意識形態是社會協調的產物,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是人們借以生活在物質環境中的思想構架,是一種對現實的意識。通過這種展開方式,建構的符號、意義與偽意識系統不謀而合,文化與意識形態交織在了一起。
在西方成熟的文化研究的視角下,中國“全盤西化”的思潮有了一些新的特質,借助文化研究理論,可以對全盤西化的可行性有一個更透徹的分析認識。
二、“全盤西化”理論的內涵與差異
“全盤西化”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思潮,西方列強的入侵以及清朝政府的無能逐漸摧毀了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知識分子開始反省中國文化的不足。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以胡適和陳序經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提出通過完全吸取、采納西方文化的方式使中國文化脫胎換骨,這一批學者被稱為全盤西化派,并與主張中西文化交融的折衷主義派與抵制西方文化入侵的抵抗主義派形成了對立之勢。
陳序經自幼接受西方教育,在新加坡、美國和德國的教育經歷讓他得以充分地領略西方文化的魅力,西方先進的科技所帶動的文化發展與當時中國落后的封建觀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樣的教育背景既是陳序經全盤西化思想的基礎,也構成了動機。在《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中,陳序經具體分析了中國文化的本質并比較了折衷主義、全盤西化以及抵抗主義三個派別,斷言:“我們的惟一辦法,是全盤接受西化。”陳序經對于文化的界定方式為他的全盤西化理論提供了合理性。在《東西文化觀》中,陳序經指出“文化是人類適應時境以滿足其生活的努力的結果和工具。”而在《文化學概觀》中又修改定義為“文化既不外是人類適應各種自然現象或自然環境而努力于利用這些自然現象或自然環境的結果,文化也可以說是人類適應時境以滿足其生活的努力的結果。”陳序經對于文化的定義圍繞著三個屬性展開,即人為性、整體性和工具性。文化的人為性意味著文化是人建構出來的,陳序經通過提出人為性明確了人與文化之間的從屬關系,文化的工具性則進一步強化了人應該控制文化而不應該為文化所控制的觀點。通過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歷史的分析,陳序經提出中國的文化的發展是一個不斷“復古”的靜止過程,認為是時候拋棄這個沒有發展活力的單調文化,換一個更順手的工具了。如果說人為性與工具性的提出旨在對抗抵抗主義的道德綁架,那么整體性的提出則是為了反駁折中主義的觀點。陳序經認為,一種文化隨時間推移形成多個層累,而文化中的層累與成分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系,即“文化叢雜”。如果按照折中主義的說法在中國文化中引入西方文化的成分,便會破壞中國文化各層累之間的關系,一個成分的變動會產生蝴蝶效應從而影響整個文化。基于這些文化的屬性,陳序經提出全盤西化是中國文化唯一的出路。
不同于陳序經建立在整體性與工具性之上的全盤西化觀,胡適的全盤西化則更親近折衷主義,胡適稱之為“充分世界化”,這種圓滑性也便是后來胡適與陳序經的理論矛盾的根源。和陳序經一樣,胡適也有出國留學的經歷,接受過西方的教育,深入感受過西方的文化。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期間師從實用主義學派集大成者杜威,實用主義學派的理論思想也成為了胡適的“充分世界化”理論的基礎。胡適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組織以及思想形式中殘存了太多封建的弊病,要根除的其實是這些弊病,又因為中國文化有太強的惰性,所以無需擔心在西化的過程中喪失了中國本位的問題,正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由此胡適支持“全盤西化”。而胡適的全盤西化,其實只是本著實用主義原則對不科學、不合理、無效果的封建習俗進行改造,而非直接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比起一個理論構建者,胡適更像是一個行動者,胡適所支持的與他所期望的結果并不完全相同,只因為他堅信這種支持會引起這種結果。胡適的“口是心非”引起了陳序經的不滿,他認為胡適的“全盤西化”的本質是折衷主義。陳序經的全盤西化基于文化的整體性與工具性的屬性,而胡適卻不認為文化成分與整體之間存在牽連關系,認為改造文化成分是可能的,兩人理論基礎的差異意味著矛盾不可避免。
三、文化研究視角下“全盤西化”的可能性分析
胡適的“充分世界化”理論構建了一個美好的可能性,即在保留中國文化本質的前提下通過引入西方文化的實用主義成分使得中國文化更為有效。胡適曾以“見女人脫帽”和“食番菜”為例,指出要學習的不是西方文化的具體內容,而是行為背后的意義與內涵,“脫帽”的意義在于禮節,“番菜”的意義在于衛生,因此在“見女人脫帽”與“食番菜”方面的西化的核心意義便是禮節與衛生,這體現了胡適對于全盤西化的一個期待,即解構符號。根據霍爾對于文化的符號意義的解讀,事物與概念之間的關系和概念與符號之間的關系形成之時,便是文化意義形成之時。“番菜”二字是中國人對于西方食物的定義,當番菜這個物件出現時,人們的腦海中便會出現“番菜”的概念,包括可食用性等特點,這是事物與概念之間的聯系。而由諸多屬性構成的“番菜”這一概念,又通過“番菜”二字得以表達和傳遞,當人們看到或者說出“番菜”和“脫帽行禮”這些話語時,人們便聯想到相應的概念以及它們的各種屬性,這是概念與符號之間的聯系。如此一來,兩個符號的建構完成了,但這還不是胡適希望解構的符號,胡適希望結構的符號是建立在這一符號基礎上的二次建構的符號體系。在這番菜的符號中“番菜”二字是能指而番菜這一事物是其所指,而在二次建構的符號體系中,“番菜”這一符號整體(包括其所指、能指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成了能指,其所指是“西方文化”,而胡適所做的便是對這種符號的再構建,將“番菜”整個符號的所指由“西方文化”變為“衛生”。這種再建構符號體系的傾向遍布胡適的所有理論,也體現在他整理國故的工作中,但當胡適埋頭于尋找論據、一點點地完成西化時,他卻沒有意識到這些工作背后的龐大機制,這種機制可能使得這些工作的艱難性遠遠超出他的想象,這種機制便是阿爾都塞所說的意識形態的限制。
胡適所希望再建構的符號也可以理解為羅蘭巴特意義上的神話,羅蘭巴特認為神話是一種稱為“釋言之言”的言說方式,是建立在現有符號之上的二次建構的符號體系,神話賦予了原有的符號新的意義。羅蘭巴特曾在《神話修辭術》中舉例:法國小資產階級用來描述鈴鐺、黃包車和大煙館的“中國性”一詞便屬于一種二次建構的符號。這一例子與象征西方文化的“番菜”與“脫帽行禮”不謀而合,胡適在不知不覺中走上了這條再建構神話的道路。而神話正是羅蘭巴特用來表示意識形態的方式,統治階級通過神話的概念與實踐來提升自身的價值與利益,以完成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穩固現存的社會結構,神話是具有階級特征的。因此胡適對于概念的一步一步的再建構其實便是在侵蝕統治階級的權力,這一行為必然會遭遇現有的社會結構和統治階級的阻礙。辜鴻銘曾對學生們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辜鴻銘的言行看似瀟灑,實則悲壯,在“辮子”的符號已經與“封建思想”的概念緊密相連的時代,辜鴻銘再建構符號的話語背后正是他憑一己之力抗衡統治階級的決心。
與胡適相比,陳序經徹底套用西方文化的全盤西化理論看似艱難,其實可能正體現了陳序經對于全盤西化可能遇到的巨大的阻礙的清晰認識。陳序經對于文化的整體性的定義也符合文化作為意識形態工具的定位,既然遲早要遭遇來自于“整體”的反抗,不如一開始就以整體改造之名行動,陳序經的文化層累論也符合阿爾都塞對于各階級意識形態的闡述。雖然陳序經在宏觀視野上優于胡適,有更明確的大方向,但他解決問題的方式卻有所欠缺,所構建的理想圖景的可行性也不如胡適。要將全盤西化落實到意識形態層面,就要將階級問題作為首要的考慮因素,但陳序經的理論中卻僅限于文化表象的討論,甚至認為文化只是單純的工具,所有文化都能為所有社會所用。即使將階級作為文化的區分標準,陳序經也沒有切中問題的核心,更不必說語言對于文化的決定性作用。文化是在意義、符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產物,因此特定的語言對于特定的文化具有適應性。陳序經將日本對于中國文化的學習作為他提倡的全盤西化的例子,但日本可以借鑒中國文化的條件是語言的接近,相似的歷史背景使得兩國的符號體系具有許多共通之處,但即使在這樣的基礎上,日本也只是借鑒中國文化的元素,后來又借鑒了西方文化的元素,相比之下更接近胡適的構想。
無論是胡適的還是陳序經的“全盤西化”理論,都沒有兼具方法以及愿景的可行性。雖然他們都沒有實現各自“全盤西化”的理想,但都作為一股思想力量沖擊了中國社會,促進了國民思想的“國際化”,推動了階級的革命。從這一維度上來看,胡適實現了他對自己的定位。
不能實現個人的愿景意味著理論不可行,但不意味著理論沒有意義,如今陳序經和胡適的思想已成為中國的知識財富,也給新的學者們留下了新的問題,例如,如果說今天的中國已經成功走上了“全盤西化”或是“充分世界化”的軌道,那么是否意味著中國的文化自此就可以埋頭前行了。胡適對于封建迷信的抵制以及對“賽先生”的提倡是通過引入啟蒙的方式改造中國文化,通過啟蒙對于神話的否定達到祛魅的效果,這種途徑正是霍克海默所說的“啟蒙在否定神話的過程中被卷入神話”。賽先生的到來同時也帶來了霍克海默對于“啟蒙終將毀滅自身”的預言,無論前途如何,中國如“全盤西化”派所部分希望地,趕上了世界的潮流。
參考文獻:
[1]阿爾都塞.哲學與政治[M].陳越,譯.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2]斯圖爾特.霍爾.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M].徐亮,陸興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羅鋼.文化研究讀本[M].羅鋼,劉象愚,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4]雷蒙·威廉斯.文化與社會[M].高曉玲,譯.吉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
[5]羅蘭·巴特.神話修辭術[M].屠友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6]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趙立彬.“論”與“派”:文化論戰中的全盤西化思潮[J].歷史研究,2006,(01).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