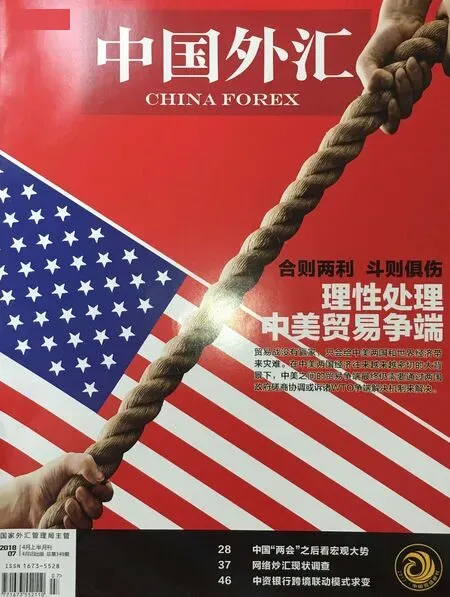防范美聯儲金融監管改革的沖擊
文/劉旭 李俊 編輯/靖立坤
2008年金融危機后,《多德-弗蘭克法案》出臺,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嚴格的金融監管改革。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美國總統,延續了共和黨自由主義的一貫主張,提議放松金融監管。2017年6月,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金融CHOICE法案》,財政部發布《創造經濟機會的金融體系——銀行和信用聯盟》報告。其核心是提高監管效率,減輕銀行監管負擔,體現了為金融監管“松綁”的傾向。未來,美國放松金融監管與漸進式加息縮表的貨幣政策,再加上減稅計劃的作用,以及近期貿易戰的影響,將使全球資本流動的不確定性有所增強。建議進一步完善外匯管理,提高對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的防范能力。
美聯儲加強金融監管的舉措
2008年金融危機后,《多德-弗蘭克法案》旨在加強金融監管,限制系統性風險。依據該法案,美聯儲對大型金融機構實施更為嚴格審慎的監管。
提高監管資本要求。一是強化對大型銀行的監管資本要求,提高銀行系統資本質量和數量,如提高普通一級資本(CET1)要求,增強抗損失能力。二是要求銀行的資本儲備要高于最低要求,用來保障銀行利潤可分配給股東和雇員。三是提高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的資本要求,減少銀行倒閉對金融穩定的威脅。
實施銀行壓力測試。美聯儲對大型銀行進行壓力測試(Comprehensive Capital Analysis and Review, CCAR),用于測試大型銀行是否有足夠的資本應對嚴重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逆行壓力下的沖擊。在CCAR的影響下,美國銀行系統一級資本增加了2倍,從2009年的5000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一季度的1.2萬億美元。同時,一級資本比例從5.5%上升到了12.4%。
強化流動性監管。一是流動性覆蓋率是一項關鍵改革,要求大型銀行保持足夠的高質量流動性資產,以滿足30日的現金凈流出。二是采用綜合流動性分析和檢查監管項目,衡量系統性金融企業的流動性。三是使用凈穩定基金比例監管,幫助大型銀行在一年內維持穩定的資金框架。
提高大型銀行的可救助性。要求美聯儲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合作,提高銀行的可救助性,降低此類銀行倒閉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以及政府救助風險。一是要求美國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及外國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在美的分支機構,滿足長期債務和“總損失吸收能力”的要求。二是促使最大型銀行優化其內部管理,如內部結構、公司治理、信息收集系統、資本的分配與流動性管理等。
美聯儲放松金融監管的措施
2017年以來美國所提出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旨在放松對銀行體系的監管,特別是對中小銀行的監管,以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同時,使金融監管既能發揮維護金融穩定的作用,也能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
金融監管改革七項核心原則。特朗普總統在2017年2月3日簽發的行政令中提出以下原則:一是美國公民有權獨立做出財務決策。二是禁止使用納稅人資金救助金融機構。三是通過更嚴謹的監管影響分析,解決系統性風險和市場失靈問題,促進經濟增長與金融市場繁榮。四是提高美國公司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五是維護美國在國際金融監管談判中的利益。六是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有效性和針對性。七是強調聯邦金融監管機構的公共問責制,使聯邦金融監管框架更為合理。
改進沃克爾規則,放松自營交易限制。一是《多德-弗蘭克法案》的沃克爾規則(該規則主要是限制存款性銀行的自營交易以及投資于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將主要適用于具有重要交易賬戶的金融機構,小型銀行可豁免遵守該規則。二是減輕銀行為遵循沃克爾規則需提交的文書報告負擔,降低銀行合規成本。
簡化中小型銀行管理,擴大豁免嚴格監管的銀行范圍。一是擬將小型銀行的門檻從5億美元提高到10億美元,讓更多的銀行能免于更為嚴格的監管。二是簡化社區銀行的資本框架,包括商業地產的風險敞口、抵押貸款服務資產、遞延稅款資產的資本處理規則等。三是小型銀行可豁免沃克爾規則和高管薪酬激勵要求。四是提高銀行參加壓力測試和風險委員會的100億美元的資產門檻,提高銀行審慎監管的500億美元的資產門檻。
簡化“提高銀行可救助性計劃”報送的要求。一是減少報送頻率。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擬將銀行提交“提高銀行可救助性計劃”的頻率由每年一次調整為每兩年一次。二是提高報送內容的針對性,將主要集中在關鍵問題和重大變化上。三是全面的報送要求將只針對大型的、復雜的或系統重要性銀行提出,同時簡化小型銀行和業務簡單的銀行的報送要求。
改善對銀行的壓力測試。一是提高壓力測試流程的透明度。將進一步披露美聯儲對各種貸款和證券投資組合模型的指標損失率,以及有助于預估損失范圍的風險特征信息等。二是擬取消CCAR中對具有高質量資本規劃能力的銀行的高質量目標要求,但將繼續評估此類銀行的資本規劃能力。三是調整CCAR指標中關于資產負債表和資本分配的假定情景,此類調整擬將與壓力測試納入銀行監管資本要求同時進行。
調整杠桿率。美聯儲正在重新審視補充杠桿率(SLR,旨在衡量銀行的總體杠桿水平),認為杠桿率是風險資本框架的一個重要支撐,但需對杠桿率和風險資本要求進行校準。此舉利于緩和任何反常的激勵措施,避免貨幣市場和其他安全資產市場的扭曲,并可解決托管銀行商業模式受杠桿率影響的問題。
中國應對沖擊之策
完善外匯管理內容,適應金融發展與改革的現實需要。一是將目前主要針對跨境收支和匯兌環節進行的管理,擴展至對跨境資產負債變動進行管理,特別是本國居民的境外資產負債情況,應納入管理范疇,以適應跨境資本運作增多的新情況。二是對跨境本幣與外幣遵循同一管理原則,以避免在本幣國際化條件下利用幣種選擇規避管理。三是在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中,對重點領域實施管理,如現鈔、房地產投資、證券投資、外債等(即使在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國家此類項目也仍可實施管理)。
豐富外匯管理方式,提高對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的防范能力。一是構建宏觀審慎與微觀監管并重的外匯管理框架。要利用逆周期管理工具、對系統重要性機構管理等手段,防控跨境資本流動的總體風險;同時繼續實施微觀審慎監管,關注逐筆跨境交易的真實性。此外,還要強化行為監管。二是保留必要管理手段,即未來開放條件下仍可采取的管理手段,如登記管理、賬戶管理、跨境交易逐筆真實性管理、事后檢查核查等。要做到跨境交易逐筆“留痕”,對跨境資金流動管理有跡可循。三是自律與他律相結合,加強對銀行的監管。從“三反”和展業原則角度,強化銀行跨境交易真實性審核責任;同時,支持完善外匯市場自律機制建設,培育銀行合規自律意識,形成合規自律文化,幫助銀行健康成長。四是深入研究外匯管理引入長臂統計、穿透監管等管理方式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