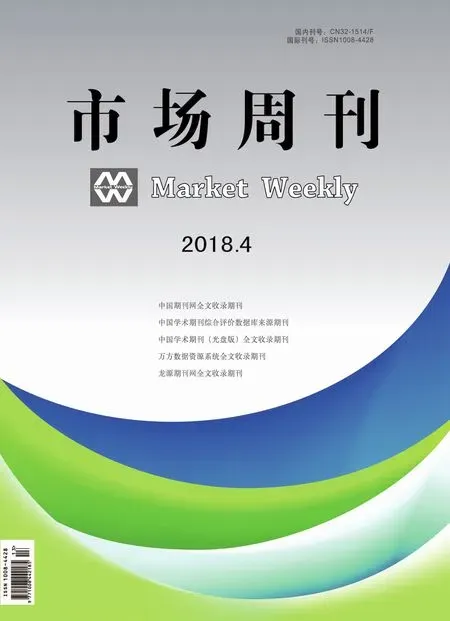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理論基礎及現實意義
張鑫
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變化表明,我國供給與需求結構的不協調,從需求方來看,人民群眾的需求從以往的基本物質文化需要轉變為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意味著一般性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已經得到滿足,轉向高品質的物質生活和高層次的精神文化享受;從供給方來看,我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經濟、科技等領域以及綜合國力都穩居世界前列,但取得成就的同時,也帶來了我國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
化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要求進一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來解決我國城鄉、區域和群體之間不平衡的現象,帶動基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各個領域的充分發展,全面提升人民生活質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受社會發展,經濟水平和政府財力的影響,在各個發展時期內容和標準都有不同的目標、重點和表現,從長遠來看,呈現領域不斷擴展、力度不斷增強、標準不斷提高的動態趨勢。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形勢下,如何有效推進不同階段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必須重點把握福利經濟學理論和公平與正義理論及其現實意義。
一、福利經濟學: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論依據
(一)主要內容
福利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經濟福利的一種經濟學理論體系,萌芽于18世紀末帕累托提出的“帕累托最優”標準,1920年英國經濟學家庇古的《福利經濟學》的出版標志著福利經濟學的誕生。庇古根據邊際效用基數論,提出兩個基本的福利命題:第一,國民收入總量越大,社會經濟福利就越大。庇古從第一個基本福利命題出發,提出實現社會生產資源最優配置的問題。因此增加社會經濟福利,就要提高國民的收入總量,就必須增加社會產量,而增加社會產量就必須實現社會生產資源的最優配置,庇古推斷出自由競爭可以使邊際社會純產品和邊際私人純產品的產值相等,從而達到社會經濟福利極大化;第二,國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會經濟福利就越大。從第二個基本福利命題出發,他提出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問題,根據邊際效用遞減學說,一個人的貨幣收入越少,其邊際效用越大;而貨幣收入越多,其邊際效用越小。所以,富人的貨幣收入的邊際效用小于窮人,把富人一部分錢轉移給窮人,實現富人與窮人在收入上均等化,可以使社會經濟福利達到極大值。總而言之,庇古認為經濟福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國民收入總量和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情況,故要增加經濟福利,就必須通過生產方面增加國民收入總量,通過優化配置來消除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這些都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基礎的理論支持。
(二)現實意義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以福利經濟學為其經濟學基礎的,根據庇古的兩個基本命題,我們可以得出:一是公共服務數量將隨著國民收入總量的增加而增加,而社會福利將隨著公共服務的增加而增加;二是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程度越高,帶來的社會經濟福利就越大。而要實現這兩點,需要政府采取適當的措施來調節社會生產資源的最優配置,以增加經濟福利;需要政府根據地方實際情況和公民客觀需求來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增加社會福利。
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當務之急是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同樣具有顯著的經濟意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利于改善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引導和拉動消費,擴大內需,提高國內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從而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農村義務教育和技能培訓,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綜合素質,促進農村就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在我國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中指出將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公共財政體系作為一大目標,表明我國財政用于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將一步突出均等化的導向。而根據邊際效用遞減這一規律,財政資金用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利于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向財政資金不足的地區或收入偏低的群體轉移財力,產生的邊際效用要大于資金用于財政充裕或高收入人群,優化社會生產資源配置,增加社會經濟福利。經濟協調發展,財政向貧困地區傾斜,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繼而有效緩解社會主要矛盾。
二、公平與正義理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保障
(一)主要內容
公平與正義是人類社會具有永恒意義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能否達到公平正義常作為衡量個人行為和判別社會制度優劣的重要標準。公平與正義理論由來已久,世界各國的理論家們始終堅持對公平與正義理論的探索和追求。
中國共產黨為馬克思主義公平思想的傳播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制度公平思想認為,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真正實現人人平等,才能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才是一個實現和超越公平正義的社會。馬克思主義第一次把公平正義的實現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中關于社會公平正義理論,是我們黨在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發展過程的理論結晶,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改變了舊制度下的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構建公平分配優先、均中求富的經濟發展目標模式,鄧小平的“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理論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大創新,社會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同時分配領域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因此,我國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和促進共同發展的必要手段。西方關于公平與正義的理論源遠流長。古希臘時期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都對正義問題展開了探討,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規劃了正義之邦的圖景,認為理性的實現或者完善表現為服從理性的統治而形成的和諧狀態就是“正義”,亞里士多德繼承和發展了柏拉圖的想法,提出了關于正義更加完備的正義理論,他認為正義存在于某種既定的平等的秩序關系中,分配公正是城邦穩定、和諧、幸福的政治基礎;近代的盧梭、洛克、休謨、康德等思想家進一步發展了正義理論,盧梭認為,應該通過訂立社會契約來建立國家,人生而平等與平等,富人與窮人在權利和義務面前沒有區別,社會達到正義與平等的狀態;二十世紀的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在當代產生的影響最為深刻,羅爾斯接受并修正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正義論,繼承并提升了盧梭、康德等人的社會契約論,構建了更高層次的正義理論體系,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提出了兩個正義原則:第一正義原則即自由平等原則,第二正義原則即機會平等和差別原則,其中第一原則優于第二原則,機會均等原則優于差別原則,這些原則保障所有社會成員在分配基本公共服務時是公平的。
(二)現實意義
基本公共服務是基于社會共識,根據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和整體水平,保障國家經濟社會的穩定,鞏固基本的社會正義和凝聚力,保護公民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所需要的基本社會條件。根據公平與正義理論,國家應賦予并維護每個人公平平等的權利。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是國家保障每一個公民都能公正而平等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對于社會底層群體和經濟基礎薄弱地區適當照顧,縮小地區和城鄉差距,促進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但均等化不是平均化,不是將基本公共服務上下拉平,完全一致,而是在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基礎上,強調“底線均等”,允許合理范圍內的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允許各地因地制宜,結合地方實際情況和公民客觀需求,采取不同的“地方標準”,而不是生搬硬套“全國標準”。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公共服務供給和社會資源大多聚集于發達地區,導致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與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之間,以及城市與農村之間長期在基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向農村和貧困地區傾斜,使村民、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能夠得到更多基本公共服務和優質資源,改變農村的發展面貌,實現在農村同樣“學有所教、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困有所幫、住有所居、文體有獲、殘有所助”,讓城市文明的現代化成果能夠更好地往農村和貧困地區輻射,帶動城鎮化發展的步伐,逐步實現城鄉之間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上協調發展,保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數量和質量在不同地區、不同群體和城鄉之間分配的合理均等,一定程度上縮小市場競爭導致的社會財富、收入和消費的巨大差距,緩解和抑制社會矛盾,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三、結語
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加劇社會階層多元分化,社會矛盾日益凸顯,經濟繁榮雖然重要,公平問題亦備受關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護個人最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確保每一個公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務,更好推動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十九大報告提出,目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穩定地解決了溫飽問題后,黨和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提升人民生活質量,增加社會幸福度,推動社會全面健康發展。所以,對福利經濟學和公平與正義理論的深入研究并理解其現實意義,一定程度上能夠指導推進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縮小城鄉、區域間的差距,緩解社會主要矛盾,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17,(001).
[2]庇古.福利經濟學(上,下)[M].商務印書館,2006.
[3]約翰·羅爾斯著,何懷宏等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4]劉云鳳.近代以來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D].江蘇:揚州大學,2017.
[5]趙和楠.財政支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城鄉收入差距調節[J].地方財政研究,2012,(02).
[6]國務院印發《“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J].城市規劃通訊,2017,(06).
[7]陳海威,田侃.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探討[J].中共福建省黨校學報,2007,(05).
[8]丁元竹.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過程中標準建設問題[J].甘肅理論學刊,2008,(05):24-26.
[9]樊麗明.區域內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及實現機制[J].財政研究,2009,(04).
[10]江明融.公共服務均等化論略[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