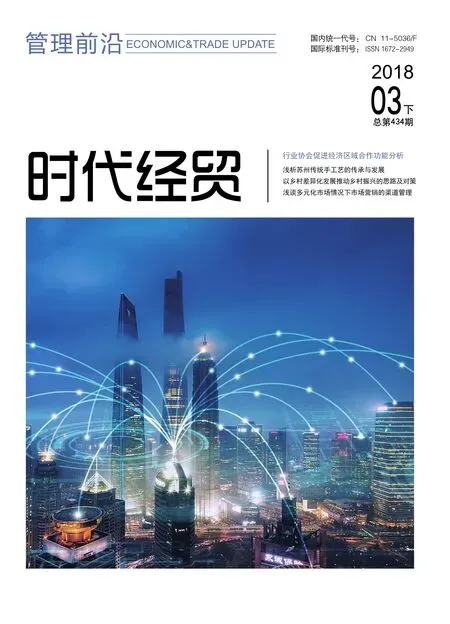知識產權無權處分問題初探
劉歡歡
(甘肅政法學院,甘肅 蘭州730070)
無權處分是民法領域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問題,因其涉及到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物權的變動等問題。從《合同法》第51條規定之初,對于無權處分效力的爭議就從未停止過,《物權法》出臺后,第15條規定了區分原則,再加上《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條所規定的內容,更導致這種紛爭甚囂塵上。反觀知識產權法領域,對無權處分在知識產權法領域中的具體應用規則進行研究的學者寥寥無幾,僅有的一些文章中對于無權處分及善意取得制度在知識產權法中的適用也出現了不一致的觀點。造成這一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國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分別規定了不同的變動標準,變動模式也不同,甚至相同類型的知識產權的不同變動也規定了不同的變動模式,無權處分的效力自然有所不同,具體規定如下:
我國著作權法對于著作權轉讓和許可的規定僅有一條,即《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5條,但其中采用了“可以”、“備案”字樣,與“應當”、“登記”的區別顯而易見。根據《專利法》第10條第3款和《專利法實施細則》第14條第2款的規定,登記是專利轉讓的判斷標準,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轉讓自登記之日起生效。但對于專利許可僅規定“應當備案”,其變動模式并未予以明確。根據《商標法》第42條第1款、第4款和第43條第3款的規定,公告是商標權轉讓的標志,這一點不同于專利權的轉讓。而對于商標許可則明確規定了備案的效力,即未經備案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在質權的設定方面,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的規定大致相同。
由上述我國現有規定可見,僅就轉讓和許可這兩種常見的知識產權處分行為而言,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變動的判斷標準及變動模式都有所不同,這種不同導致在分析無權處分行為時就更加復雜,不僅要考慮到合同的效力及知識產權的變動,甚至還要考慮到知識產權行為的構建。因此,筆者認為很有必要根據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將無權處分行為進行一個系統的分析。
一、知識產權無權處分的概念及構成要件
知識產權的無權處分行為,是指行為人沒有知識產權的處分權,卻以自己的名義對他人的知識財產進行法律上的處分,并與相對人訂立了處分知識財產合同的行為。這里的處分,主要是指知識產權的轉讓、許可、設定質權等。知識產權的無權處分會損害到真正知識產權人的合法權益,為我國法律所禁止。
知識產權無權處分的構成要件有二:首先,行為人實施了知識產權的無權處分行為。其次,行為人與相對人訂立了處分知識財產的合同。二者相比較而言,后者更為重要,因其涉及到該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以及知識產權是否會發生變動的問題,更有分析的價值和必要。
二、《合同法》第51條和《買賣合同解釋》第3條在知識產權領域的適用
《合同法》第51條規定:“無處分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后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有效。”該條規定了無權處分的合同屬于效力待定的合同,也是學界歷來最具爭議的一點。筆者認為,此處效力待定并非指無權處分的合同效力待定,而應當是知識產權的變動效力待定。主要原因在于,合同具有相對性,該合同發生在行為人和相對人之間,只要沒有出現合同無效情形,真正知識產權人并非合同當事人,沒有決定合同能否生效的能力。《買賣合同解釋》第3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以出賣人在締約時對標的物沒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賣人因未取得所有權或者處分權致使標的物所有權不能轉移,買受人要求出賣人承擔違約責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張損害賠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該條規定出賣他人之物的,合同原則上有效,筆者認為該規定也同樣應當適用于無權處分的知識產權合同,且并不局限于知識產權轉讓合同,也同樣適用于知識產權許可合同。由上述兩條可見,無權處分的知識產權合同原則上應當有效,只是知識產權能否發生變動,取決于真正知識產權人的追認,若知識產權人追認,則發生知識產權變動的結果;若知識產權人拒絕追認,則不發生知識產權的變動,相對人可向行為人主張違約責任或要求解除合同。
三、無權處分情形下知識產權的變動
物權的變動模式有意思主義和形式主義,形式主義包括債權形式主義和物權形式主義。知識產權的變動模式據此也包括債權意思主義、債權形式主義和知識產權形式主義。其中,采債權意思主義的國家包括法國、美國、英國、意大利等,采債權形式主義的國家有俄羅斯等,采知識產權形式主義的國家包括德國、瑞典、墨西哥等。我國物權法采債權形式主義,由此,有學者提出我國知識產權的變動也應當采債權形式主義說,即基于法律行為而發生的知識產權變動,除合法合同這一債權法律行為之外,尚需作出登記這一法定公示形式,方能發生知識產權變動的效力。債權形式主義不承認知識產權合意的存在,也不承認獨立的知識產權行為,其認為登記行為僅是履行債權合同的事實行為,而非包含有獨立意思表示的法律行為。
筆者認為,針對我國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作出如此統一的規定并不合適。首先,著作權不宜采用債權形式主義,因作品中包含有著作人身權的內容,也有可能反映作者的隱私,登記將會導致作品有公開的風險,因此,是否進行登記應由作者自行決定,強制登記并不可取。其次,技術秘密和商業秘密本就處于保密狀態下,強制登記將會導致秘密被公開或公開的風險增大,不利于對權利人的保護。而對于專利權、商標權、植物新品種權等,采債權形式主義比較妥當,能夠有效避免各種糾紛的發生。因此,在無權處分的情形下,應當區分不同的知識產權類型,采用不同的知識產權變動模式,從而決定無權處分的效力問題。
四、無權處分情形下知識產權合同的效力分析
知識產權合同主要包括:知識產權開發合同、知識產權轉讓合同和知識產權許可合同。對于那些通過公告方式公開的知識產權,如專利權、植物新品種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商標權,當出現無權處分行為時,合同相對人可以通過查閱公開信息知曉該知識產權的權利歸屬。如果行為人和相對人“惡意串通”,損害真正知識產權人的利益,該合同無效,如果當事人沒有串通的惡意,則屬于“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合同部分或全部無效。此種情形下可構成共同侵權,二者承擔連帶責任。
對于未公開的知識產權則較為復雜,且不同的知識產權應區別對待。著作權的無權處分中,若相對人知道或應當知道行為人無權處分,則屬于“惡意串通”,合同無效,相對人和行為人可構成共同侵權,承擔連帶責任;若相對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行為人無權處分,原則上合同有效,行為人履行不能,相對人可向行為人主張違約責任。技術秘密的無權處分中,若相對人有過錯,則合同無效,合同當事人構成共同侵權,相對人不得繼續使用該技術秘密;若相對人無過錯,合同原則上有效,相對人可以繼續使用該技術秘密。
五、善意取得制度在知識產權領域的適用
善意取得制度的當事人至少涉及三方:真正知識產權人、無權處分人和善意相對人。根據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論和實踐,其構成要件包括:(1)行為人無權處分;(2)相對人為善意;(3)有償交易行為;(4)已完成公示行為;(5)真正知識產權人的可歸責性。善意取得制度在知識產權領域中的適用應區分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區別對待:
首先,專利權、商標權、植物新品種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等,已進行公告,相對人可以通過公告內容了解真正的權利人,若此時仍與行為人訂立合同,不能認定相對人為“善意”,善意取得制度當然不能適用。其次,對于上述已經公告的知識產權,若出現登記錯誤,相對人基于對登記的信賴而訂立合同,構成善意取得,若為轉讓,則知識產權變動,若為許可,則被許可人可繼續使用該知識財產。再次,著作權采自愿登記,技術秘密和商業秘密無須登記,針對這幾種知識產權,應分兩種情況處理:若未進行登記,無公示當然不會產生公信力,善意取得不能適用;但若權利人進行了登記,則產生公信力,可以適用善意取得。
參考文獻:
[1]蘇平:《知識產權變動模式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2]石冠彬:《論無權處分與出賣他人之物——兼評〈合同法〉第51條與〈買賣合同解釋〉第3條》,載《當代法學》2016年第2期。
[3]王利明:《論無權處分》,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3期。
[4]吳國喆:《善意取得制度的缺陷及其補正——無權處分人與善意受讓人間法律關系之協調》,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