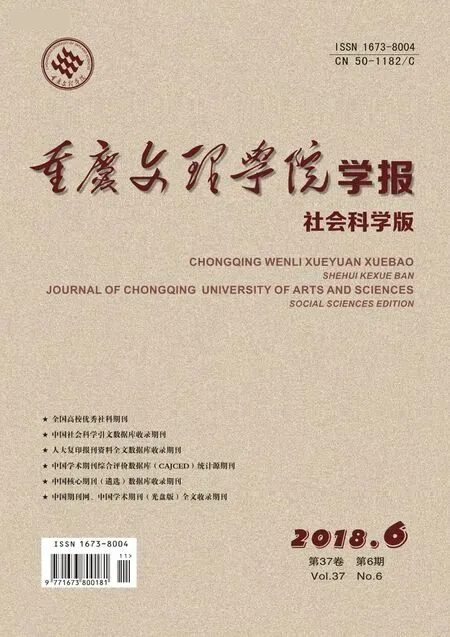論盛唐六言詩之“風趣”
張慧穎
(安徽師范大學 文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一、六言詩研究現狀綜述與盛唐六言詩發展概述
六言詩的研究相較于五、七言詩則相對較少,從宏觀角度研究的有:俞樟華、蓋翠杰的《論古代六言詩》[1],著力分析六言詩體在中國古代起源及發展的狀況,力求全面展現六言詩這種文學樣式的概貌;林亦的《論六言詩的格律》[2]與衛紹生的《六言詩體研究》[3],都是從格律、聲調和體式方面來研究六言詩;唐愛霞的《古代六言詩研究》[4]作為一篇博士論文,較為全面和詳細地闡述了六言詩的起源、格律、音節,以及與音樂、詞的關系,將魏晉南北朝至明清時期的六言詩全部納入其研究范圍,從微觀角度研究的則更注重六言詩的個案研究、朝代性和體式上的側重,張明華、王啟才的《黃庭堅與六言詩在兩宋之際的發展與變化》[5],李蓉的《范成大六言詩的新變》[6],趙飛文的《論唐代六言絕句》[7]以及劉繼才的《論唐代六言近體詩的形成及其影響》[8]等都屬此類。通過研讀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六言詩在起源發展、格律體式上的研究已經較為成熟和完備,然而其藝術風格方面則仍有可補充之處。盛唐時期的詩歌創作如同一座壯麗雄偉的高峰,那盛唐六言詩的創作又有著怎樣獨特的藝術風貌?雖然六言詩未能流行于世,但其藝術風格對后世創作卻未必沒有影響。
唐代是中國詩歌發展的巔峰時期,煌煌唐韻,俊采星馳。六言詩在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演變之后,也隨著中國古典詩歌進入空前的繁榮期,融入中國古典詩歌的大潮,呈現出一種全新的面貌。盛唐時期六言詩的創作群體與創作數量雖不及中晚唐,然而盛唐時期的創作群體主要為李白、杜甫、高適、岑參這樣的詩歌名家,作品質量較高,產生的影響也大大超過中晚唐,可謂是唐代六言詩的一個高潮期。

盛唐六言詩主要作家及作品情況表
從以上表格可以看出,盛唐時期基本是六言格律詩的時代,詩人們借鑒五、七言詩歌創作的成功經驗,在創作過程中自覺遵守格律詩的一些基本要求,從而使盛唐的六言詩基本以絕句為主。
自北周時期六言詩作為朝廷宴享祭祀之體登上歷史舞臺開始,其地位隨著時代的發展逐漸開始提高,不再單單作為宴享祭祀之用,亦成為詩歌正體登堂入室。到了盛唐時期,六言詩的題材內容已從朝廷歌辭轉變為描寫田園生活、山水風光,從而抒發閑情逸致,堪稱唐代六言詩中的精品。而正是這些田園山水之詩,共同輝映出盛唐六言詩“風趣”的藝術風貌。
二、盛唐六言詩“風趣”之所在
盛唐時期張說的八首六言詩皆為樂府,是歌功頌德的應制之作,贊揚李治與武則天的政治清明、福壽無疆,雖充滿著陽剛爽朗之氣,其內容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該詩的價值,是六言詩由初唐向盛唐過渡的作品。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張說的六言樂府《舞馬詞》《破陣樂》不僅有創體之功,對六言絕句與律詩,甚至詞曲的形成與發展都有著重要的影響,然這里暫擱置不論。
自王昌齡創作的六言詩《望月》《途詠》始,詩歌視野開始由朝廷轉向更為廣闊的自然世界。《唐詩匯評》在談及六言詩時收錄了王楷蘇《騷壇八略》之論:“六言詩,摩詰、文房輩偶一為之,其法大概以風趣為主,不措意可也。”[9]從王維的《田園樂七首》與劉長卿的六言詩出發,縱觀整個盛唐六言詩的概貌,“風趣”恰恰從形與意兩方面對這一時期六言詩的藝術風貌做了準確而精到的定位,使盛唐的六言詩出現了與五言詩、七言詩的雄壯渾厚相聯系又相區別的獨特藝術風貌。
“風趣”一詞最早出現于南北朝時期,南朝的謝赫《古畫品錄·戴逵》寫道:“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其內涵主要指風味情趣,與王楷蘇對王維、劉長卿六言詩的定位是相一致的,繼而從他們詩里放眼整個盛唐時期,解讀六言詩之“風”與“趣”的具體藝術特征。
(一)風神爽朗,飄逸靈動
盛唐六言詩最著名的當屬王維的《田園樂七首》:
厭見千門萬戶,經過北里南鄰。官府鳴珂有底,崆峒散發何人。
再見封侯萬戶,立談賜璧一雙。詎勝耦耕南畝,何如高臥東窗。
采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里人家。
萋萋春草秋綠,落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村巷,童稚不識衣冠。
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客猶眠。
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東谷黃粱夜舂。
(又名《輞川六言》)
這七首絕句表現了王維向往恬淡閑適的田園生活的心態,不論是采菱渡頭、杏樹壇邊、桃花源里,還是萋萋春草、落落長松、山下孤煙、天邊獨樹、南園露葵、東谷黃粱,抑或是桃紅柳綠、宿雨朝煙、遠村陋巷、泉水鳴琴,王維將這些充滿詩情畫意的自然物象聯系組合在一起,不僅色彩和諧,更是帶有山間田園獨有的明凈爽朗,風味雋永。除此之外,作者還善于用靜謐和諧的自然景物烘托鮮活靈動的人物形象,靜中有動,動靜結合,如壇邊漁夫、孤眠山客、歸村牛羊、枝頭黃鶯等,都是動態的形象,配合著田園的寧靜與優美,從而使整個詩歌呈現出一種靈動飄逸的藝術風貌,而那些富有張力的動詞,如“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中的“含”與“帶”,更是為整首詩歌在靜朗中平添了一份神韻,給讀者留下了無窮的想象空間。宋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中評價:“‘桃紅復含宿雨’云云,每吟此句,令人坐想輛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閑適于其間也。”[10]P271可見這七首六言詩,描繪出如此引人入勝的春日勝景圖,明朗靈動、風神熠熠。
王維之后,在六言詩創作方面取得較高成就的應推劉長卿。先看其三首六言絕句:
危石才通鳥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深處,澗水浮來落花。
(《尋張逸人山居》)
對水看山別離,孤舟日暮行遲。江南江北春草,獨向金陵去時。
(《發越州赴潤州使院留別鮑侍御》)
瓜步寒潮送客,楊柳暮雨沾衣。故山南望何處,秋草連天獨歸。
(《送陸澧還吳中》)
《尋張逸人山居》描寫詩人入山所見之景,通過描寫“危石”“鳥道”“空山”,烘托出一種空靈又靜謐的氛圍,將張逸人的居所與桃源相聯系,再用“澗水”與“落花”渲染,顯得別有情致。后兩首詩為送別之作,景中寫情,“孤舟”“日暮”“春草”“楊柳”等意象的組合,使送別充滿著詩情畫意,且詩中多用民歌語言,簡明清淺又富于情致。至于其兩首六言律詩,亦是展現出“風趣”的整體風貌,《苕溪酬梁耿別后見寄》與《蛇浦橋下重送嚴維》這兩首也是寫離情別意,同樣是通過景物渲染來表達感情,“白云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后溪”將時間、空間分別拉長拉大,于惆悵的離別中亦生出一份爽朗的豁達,“黃葉”“青山”與“寒江”“古木”等意象,分別從視覺觸覺等角度描寫景物,為之賦予了人的情感,從而使筆下萬物更添神韻,整篇詩作情致搖曳,品之不盡。
除了王維、劉長卿的六言詩作,李白的“門對窗溪流水,云連雁宕仙家”(《春景》)有著詩仙獨特的俊朗飄逸,呈現出來的詩歌風貌更顯靈動有致;王昌齡在其《望月》中也有“聽月樓高太清,南山對戶分明”這般風神清朗的景物;岑參的一句“洞口桃花帶雨,溪頭楊柳牽風”(《春山晚行》)更是寫盡風韻,靈動清爽。這些六言詩句或繪四季景物,或述村居之樂,形象描繪了大自然旖旎的風光,充分展現了盛唐時期六言詩作風神爽朗、靈動飄逸的藝術風貌。
(二)情理非凡,趣味無窮
爽朗飄逸的風神是盛唐六言詩的形象特征,而其內在的深層意蘊卻體現出一種非凡無窮的理趣。王維《輞川六言》中最著名的一首:“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客猶眠。”桃花帶雨,柳染煙濃,花落鶯啼人未醒,此時此地仍然寧靜如初。花落未掃乃是因家童與客俱未醒,這無人過問落花滿地的情景,不是別有一番清幽的意趣么?俗話說,心靜方能物靜,作者在詩中著意渲染靜謐的氣氛,正是為了表現詩人的追求物我皆靜,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融為一體的理趣。周珽在《唐詩選脈會通評林》中評此詩:“上聯景媚句亦媚,下聯居逸趣亦逸。”[10]P372指的便是此詩既有靈媚清朗的藝術形象,又兼含物我皆靜的理趣。而另外六首大抵也呈現出靜謐歸隱、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這一意趣。
劉長卿的《尋張逸人山居》則又是另外一番趣味。此詩采用欲揚先抑的手法,先說其險,再由落花來引人入勝。山路危石,盤旋直上,似乎只有鳥兒才能飛過,然而空山深處竟然還住有人家,順著澗水漂浮來的落花去追溯,上游定是桃花源一般美麗的地方。此詩不直說危石之后隱藏有什么地方,而是略露一斑,讓人從水面落花來判斷,美好的境地深藏其后,從而引人入勝。明代顧磷評點“桃源定在深處:有趣”[11]。這首詩的結構獨具匠心,用曲折婉轉代替平鋪直敘,讓景物慢慢出現在讀者眼前,從而別有一番幽賞細品之趣味,令人回味無窮。
富于情趣、理趣之作遠不止此二人之詩,盛唐六言詩著筆風韻流轉,細品妙趣橫生,太白“慣看山月山花”(《春景》)寫山居閑適之趣,“詩興正當幽寂,推敲韻語落砧”(《秋景》)寫詩興幽寂,需反復推敲方得佳作之樂趣。少陵的六言詩《村樂》:“心遠不知市近,家貧惟盼年豐。炙腎寧忘王子,顛毛已作山翁。”則更多體現了廣大農民淳樸生活中的樂趣,所謂“心遠地自偏”,長年的田間勞作已然隔絕了喧囂,唯有單純的愿望企盼著豐收,即使勞作再艱苦也不貪圖那空虛的快活,山中老翁也有自己生活的快樂和趣味。整首詩緊扣一“樂”字,末句“顛毛已作山翁”既有著自嘲的豁達,又有著安貧樂道的滿足,讓人讀來不禁對老翁簡單充實的生活心生向往。岑參通過《春山晚行》中“鳥度殘陽上下,人隨流水西東”一句也表達出一種人與萬靈在自然面前皆渺小力微的理趣,而高適在《元日》中通過將景物擬人化,從而將元日的盛大場面寫得妙趣橫生。盛唐的六言詩往往都有著或深刻的理趣或生動的情趣,使詩作余音繞梁、趣味無窮。
三、盛唐六言詩“風趣”之原因
(一)外部時代因素
唐代是我國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強大的國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與豐厚的文化積累,為唐詩的繁榮準備了充足的條件。而盛唐更是唐詩發展的高峰,林庚先生有言:“盛唐氣象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朝氣蓬勃,如旦晚才脫筆硯的新鮮這也就是盛唐時代的性格。”[12]在這一時期,詩歌在思想與藝術上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飛翔在廣闊的朝氣蓬勃的開朗空間,六言詩也從時代的昂揚進取中汲取了積極健康的時代成分,其表現山水田園內容的六言詩與現實社會是相聯系的,并非魏晉時期與世隔絕的消極避世,其“風趣”的藝術風貌源自盛唐時代的安定康樂。
王維《輞川六言》的“采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日斜”,渡頭風吹,林邊日斜,各景物和諧共處,構成了一幅優美清朗的田園圖。“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里人家”,一漁夫立于樹下,不遠便是處處人家,字里行間都充滿了濃濃的生活氣息,洋溢著不盡的田家樂趣。又其“南園露葵朝折,東谷黃粱夜舂”,正是這樣充實而忙碌的農作生活,使得整首詩流露出一種別樣的爽朗風韻。岑參的《村居》“夾岸人家臨境,孤村燈火懸星”便是最平常的生活場景,高適的《元日》“獻歲杯傾鸚鵡,鳴春韻雜笙簧”也絕非與世隔絕之景,正是這般安定而平淡的生活,才孕育出如此飽滿的詩意,造就這般“風趣”卓然。
另一方面,盛唐的時代特征造就了盛唐詩人尤其是山水田園派“藻思襟情”般的風神,他們以一種富于詩情的眼光來看待一切,對仕與隱也不再過分對立,與山水親近,與人世亦不疏,正如余恕誠先生說的:“詩人自身也是既怡情山水又親和人間”[13],因此,他們筆下的景物都是可以與之交流的,有著人的情思和情韻,出落而成的六言詩既有山水間飄逸靈動的情致,又有人世間深刻無窮的理趣。
盛唐的時代因素不僅影響著六言詩的風貌,同樣也影響著五言詩、七言詩,然而不同于五言詩、七言詩整體風貌上的雄壯渾厚,六言詩以“風趣”為主,大多也是因為題材上的田園山水化,從而使盛唐六言詩自有一股清新別樣的趣味,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時代影響這一共性原因,六言詩內部自身特點則是一個更具個性的原因。
(二)內部自身特點
陸時雍《詩鏡總論》說:“六言甘而媚”。指的是六言詩宜表現舒適恬淡、嫵媚多姿的生活。張風波進一步說:“以六言詩舒緩平穩的語調,表現其恬淡閑逸的生活情趣,可謂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14]那么就不得不關注六言詩這一特殊的體裁。
首先是句式。六言詩的基本句式是“二二二”,這是盛唐大多數六言詩都采用的句式,如王維的《田園樂七首》之: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客/猶眠。
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東谷/黃粱/夜舂。再如岑參的《村居》:
夾岸/人家/臨鏡,孤村/燈火/懸星。喬木/千枝/鷺下,深潭/百尺/龍吟。又如劉長卿的《發越州赴潤州使院留別鮑侍御》:
對水/看山/別離,孤舟/日暮/行遲。江南/江北/春草,獨向/金陵/去時。
諸如此類“二二二”句式的詩還有不少,而這種句式音節分配平均,字數相同,讀來十分舒緩平穩,且語義單位較松散,動詞極少,如王維詩中“桃紅”“復含”“宿雨”都是偏正詞組,“紅”“復”“宿”是修飾語,一句中語義疏淡,從而便有了舒緩的效果,而這種舒緩的語調與田園山水的古淡優美更是相得益彰,更生出一番韻味飽滿、風神蕩漾的姿態。然而盛唐六言詩也并非皆為“二二二”句式,王維的“采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里/人家”,便是一首“四二”句式的六言詩,還有“門對/窗溪流水,云連/雁宕仙家。 誰解/幽人幽意,慣看/山月山花”(李白《春景》),“心遠/不知市近,家貧/惟盼年豐。炙腎/寧忘王子,顛毛/已作山翁”(杜甫《村樂》)等句式,這是基于“二二二”句式的基礎上所做的一些改變,從而使音節在舒緩的基礎上更添一份靈動多變,不自覺便帶有一番趣味,讀罷唇齒留韻,自在“風趣”。
其次是疊字的運用。《文心雕龍·物色》說:“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意思是用重疊復沓才能寫盡景物的情狀,可以更好地形容事物。六言詩中的疊字使用頻率是遠遠高于五、七言詩的,因其基本的“二二二”句式更契合雙音步的疊字,從而在描繪景物上更加形象生動、逼真傳神,在節奏上也產生了明顯的音律效果,讀來朗朗上口,進一步促成了盛唐六言詩“風趣”的藝術風貌。
王昌齡的《途詠》:“僧舍蕭疏靜掩,漁舟隱隱煙光。”寫的是詩人途中夜息,萬籟俱靜,只看得見遠處忽明忽滅的漁光,疊字“隱隱”恰到好處地將煙光的模糊不定、若隱若現表現了出來,并且營造出一種靜謐安閑、別有情調的氛圍,借遠處的一點暖暖的燈火,暗喻詩人心頭的一份安慰、一點希望,不也是旅途中的一份樂趣么?
王維的《田園樂七首》之四:“萋萋芳草春綠,落落長松夏寒。”更是兩句用了兩個疊字,“萋萋”寫春天草木茂盛之景,從而展現出一派詩情畫意,“落落”寫夏天長松零落之貌,與春景形成對比,別有一番疏朗之美,二句便是兩種風神,田家四時之景亦是各有樂趣,疊字的運用使人讀來又添了一份安閑舒緩的情韻,“風趣”二字堪當也!
四、盛唐六言詩“風趣”之影響
(一)對宋代及以后六言詩的影響
從內容題材上看,宋代及元明清六言詩主要以寫景抒懷為主,這與盛唐六言詩山水田園題材的較高成就是分不開的,而對于盛唐“風趣”的特征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如蘇軾的《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之一:“秋早川原凈麗,雨余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展現了秋日平川之爽朗明麗,又伴著風雨的柔美,自有一股俊逸靈動的風神,末兩句抒發了歸隱之意,體現出詩人對田園樂趣的追求。再如楊萬里的《宴客夜歸》:“月在荔枝梢上,人行豆蔻花間。但覺胸吞碧海,不知身落南蠻。”在月光下的田園中,夜氣夾雜著荔枝與豆蔻的芬芳浮動著,前兩句讀來不覺景生眼前,有如身臨其境,穿行在花木間,一物一景都頗具情致,以至于忘記自己所處的艱難境地,反覺胸中暢快,真是趣從中來。明代楊慎的《長干三臺》其一:“雁齒紅橋仙坊,鴨頭綠水人家。邀郎深夜沽酒,約伴明朝浣紗。桃葉橫波風急,梅根渚遠煙斜。”也不難讀出其中風神俊爽的景物形象以及深夜沽酒、明朝浣紗的生活樂趣。
而取得六言詩創作較高成就的首推宋代王安石,他的《題西太一宮壁二首》幾乎可與王維的《輞川六言》相媲美。全詩如下: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
用“柳葉”“鳴綢”“荷花”“落日”等意象的排列,展現出一幅盎然清新的夏日圖:夕陽西斜中落霞輝映,岸邊楊柳枝垂葉綠,迎風低昂,偶爾一陣微風拂面,蟬鳴陣陣,池中荷葉相依如醉,前兩句寫景甚得盛唐之“風趣”,有著一種靈動優美的韻味,透露出一份安樂與陶醉;第三句“三十六陂春水”收攏前兩句,再以“白頭想見江南”結句,造成情感的飛躍,透露出詩人思念江南故鄉的情思,以眼前之景反襯故鄉之景,匠心獨運,文意搖曳,顯然是順承了盛唐“風趣”的藝術特色。而第二首寫詩人故地重游,面對物是人非之景所產生的感慨,嘆時間更替興亡多變,則更多地偏向于盛唐“風趣”中的理趣,宋代六言詩對理趣一脈的發展可謂是不遺余力,這與整個宋代詩文重理趣的是趨同的。
劉克莊的六言詩最重理趣,如《冬夜讀幾案間雜書得六言二十首》錄三:
叔夜真龍鳳矣,嗣宗猶螟贏然。一以《廣陵散》死,一以《勸進表》全。
有教圣愚無類,非人父子勿傳。此乃靖欲反矣,是亦羿有罪焉。
舉世盡兄孔方,無人敢卿五郎。客喜大夫糞苦,奴夸太尉足香。
第一首用前人的代表作品來顯示其人的處世哲學,從而寄予自己的褒貶態度,后兩首也皆是通過用典來示愛憎,委婉不直,令人深思后獲益匪淺,自然便從中悟出一番理趣。值得關注的是第一首句式結構,前兩句采用“二一三”句式,后兩句則采用“二三一”的節奏,由此可見,宋及以后六言詩對句式方面的改變更甚于唐。
因此,從形式上看,盛唐之“風趣”對宋至清六言詩句式上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上文已經詳述了宋及以后朝代對于“風趣”藝術風貌的繼承,而為了達到其詩的靈動飄逸,為了更好地體現理趣,突破傳統的“二二二”句式則是必然選擇。如黃庭堅的《題山谷石牛洞》中“白云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二句采用的是“三一二”的節奏;他的《次韻石七三》其一“骨硬非黃閣相,眼青見白蘋洲”二句用的是“二一三”的節奏;而在其二詩中“生涯一九節笻,老境五六十翁”二句則變成了“二三一”的節奏,這里將更加靈活的散文句式融入了六言詩,使得表現出來的景物也更加靈動俊朗,情韻更加搖曳多姿,而所表達的理趣也突破了原本句式的束縛,其范圍更廣、內涵更深,宋代六言詩正因為深受盛唐“風趣”之貌的影響,對盛唐六言詩一邊繼承,一邊發展,從而將“風趣”這一獨特的藝術風貌表現得更加具體,從而一直延續至元明清,余響未絕。
(二)對日本漢詩的影響
在日本漢詩中,有不少詩人從事六言詩創作,他們大多受到了盛唐六言詩“風趣”藝術風貌的影響,在題材上以山水田園為主,藝術特色上重景物的靈動風神,以表達清朗飄逸的情韻和閑適安逸的情趣。如日本詩人菊池溪琴深受王維六言詩影響,其模仿王維之詩如下:
鳥倦已歸江樹,帆遲憂逐晚晴。沙浦潮來雨歇,山城鐘盡云行。
青山皆繞古驛,野水半含人家。漁老歸時柳絮,耕牛行處桃花。
竹綠自有清韻,山青何關世情。門荒不見人影,窗靜只聞水聲。
——菊池溪琴《仿右丞》(選三)[15]307
此詩巧妙將意象組合,色彩豐富飽滿,一如王維筆下的輞川別墅,十分清麗閑適,那些靈動明朗的風景,無處不透露出一股安樂寧靜的氣息,有著一番俊逸多姿的情趣和淡然通透的理趣,盛唐六言詩之“風趣”于此處盡顯無疑,受這一影響的詩作還有很多,如:
千山萬山落日,紅葉黃葉深秋。風光此際如錦,思句人憑小樓。
——富田歐波 題畫
雨外孤帆出沒,煙中一水縈紆。殘日乍明乍滅,遠山如有如無。
——森春濤 題畫
紅塵紫陌無夢,黃葉青山有家。迎客撥書客坐,遣童汲水煮茶。
——賴山陽 畫山水
旁若無人筍長,相見一笑花開。偶吟長句短句,更近三杯四杯。
——久貝岱 《六言獨酌》[15]306-307
遠山落日,秋葉絢爛,雨中孤帆,紅塵紫陌,汲水煮茶,筍長花開,這一幅幅如畫般的美景中都蘊含著搖曳生姿的情致,那種靈動縹緲的風神和情理非凡的趣味正展現著盛唐六言詩“風趣”的煌煌余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