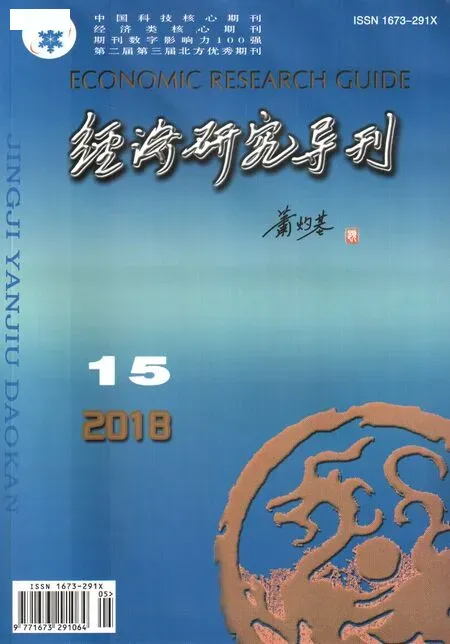從國際主要經濟體政策差異視角認識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意義
劉 暢,靖舒婷
(1.中共長春市委黨校,長春 130012;2.長春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長春 130022)
引言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發展明顯放緩,處于深度調整狀態,許多國家面臨嚴重的經濟失衡,國際市場貿易與投資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政治勢力抬頭。在傳統經濟動能增長乏力,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尚未實現關鍵性突破的經濟環境下,世界幾大主要經濟體在政策手段的選擇上存在明顯的差異性。歐盟、日本與美國等經濟體其政策方案主要圍繞通過寬松性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等手段以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而相較于貨幣、財政及貿易層面的短期經濟政策,中國更重視通過結構性改革以全面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三去一降一補”、增加有效供給、降低無效供給,以科技創新引領實體經濟發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致力于改善供給體系結構與經濟發展質量的戰略理念。
一、全球主要經濟體政策差異比較
1.歐盟。作為一個經濟體,歐盟始終無法調和其設立之初就先天不足的困境。具體而言,盡管擁有統一的貨幣歐元,然而歐盟內部一直受困于只有統一的貨幣聯盟而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聯盟的結構性不足,而更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更無從談起。政策手段的選擇不足直接導致歐盟更傾向于啟動貨幣政策以調節經濟發展,歐洲央行于2014年首次開啟負利率模式,隨后的2015年啟動量化寬松政策,并于此后進一步下調負利率及擴大量化寬松規模,流動性泛濫與債務結構扭曲嚴重干擾了市場的定價機制,并從公共債務領域傳導至公司債務領域,德國的Henkel公司與法國的Sanofi公司等先后發行了負利率的公司債券。然而,依賴量化寬松與利率下調等手段卻放慢了歐盟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步伐。
2.日本。不同于結構先天不足的歐盟,日本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日本政府可以充分主導其本國的結構性改革政策。然而,“安倍經濟學”在追求2%通貨膨脹目標優先的政策導向指引下,將長期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目標讓位于短期經濟繁榮的政策目標,結構性改革政策讓步于負利率與貨幣寬松等政策手段,其結構性改革并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3.美國。一直以來,美聯儲標榜自己獨立、超然的地位。然而,近年來,隨著美國財政及債務問題的惡化,美聯儲的獨立性地位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質疑。特別是特朗普政府上臺執政后,致力于提高政府預算赤字,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財政政策,以及兌現其競選承諾施行大規模減稅。減稅政策的實施將進一步加重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美國面臨財政赤字增長與經濟衰退的雙重隱患。
特朗普政府所提出的經濟政策主要關注于短期的就業機會與貿易赤字平衡,而忽視中長期的供給側及科技創新領域對生產率提高的影響,其政策導向更傾向于短期需求側而非中長期供給側改革,需求側改革雖然易于短期見效,然而中長期的結構性改革才是解決經濟發展問題的關鍵所在。國際社會對于這一現象并未視而不見,2017年以來,盡管美元開啟了退出量化寬松以及縮表等決策,然而國際市場并未如出現預料中的美元暴漲,反而出現美元指數連續下跌的景象,一度甚至出現拋售美元的高潮,弱勢美元的觀點成為國際市場的主流意見,國際資金正越來越多地配置歐元、人民幣與黃金等標的的金融資產以達到避險目的。
近年來,國際經濟學界普遍將2%通貨膨脹率這一政策目標奉為圭臬,這一觀點深刻地影響了各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表現為各國普遍采取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然而,隨著世界各國越來越接近惡性通貨膨脹極限的情況下,央行工具箱中的負利率、量化寬松等貨幣政策手段的發揮空間已經非常有限。在此情況下,各國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依賴正日漸明顯。然而,擴張性財政政策難以長期推行,許多國家的政府與企業部門杠桿率過高,并通過資產證券化等結構化的金融產品進一步放大其債務杠桿。而赤字與債務風險的堆積反過來抵消了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效果,長期債務的低利率及負利率對其市場定價的扭曲影響正日漸明顯。長期而言,各國真正應該關注的是如何借助結構性改革以推動生產曲線的擴展,進而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二、中國的供給測結構性改革新思維
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期間經濟工作的主線,十八大以來,中央對經濟形勢做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要判斷,將新常態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指導經濟工作的大前提,接受換擋期所面臨的經濟增速適當放緩。堅持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堅持以創新促轉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形成高質量、多層次、寬領域的新供給體系。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政策主線,致力于通過結構性改革以提升經濟增長質量,逐步由過于以地產、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及出口為主要驅動力的粗放性增長模式向以消費、服務業、科技創新等新要素驅動的經濟模式轉變。
2016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開局之年,由“三去一降一補”入手,逐步擴展為2017年的繼續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等四項任務。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中國經濟的判斷是著力解決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其中,供給側致力于適應新需求結構的變化,減少無效供給,積極培育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推動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降低金融等資源對無效供給的支持,清理“僵尸企業”,堅決淘汰落后、過剩產能,為培育新動能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切實減輕實體經濟的負擔;結構性致力于降低過剩產能、過剩庫存等冗余資源,加大對科技、農林、扶貧等重點領域的投資扶持力度;體制性矛盾重點在于通過完善市場機制,讓市場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2.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定力。在面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壓力下,中國非但不采取以貨幣、財政等手段強刺激的方式以維持經濟增速,更于2017年首次由官方界定了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灰犀牛”問題,積極防范金融風險,將影子銀行、房地產泡沫、國有企業高杠桿、地方債務、違法違規集資等問題納入高度警惕的視野下。直面當前經濟中存在的金融隱患,強調中國貨幣政策將采取“不緊不松”的穩健中性取向,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搞強刺激,致力于維持貨幣的流動性以及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強調穩定經濟增長但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致力于去杠桿而非加杠桿,清理、整頓地方政府債務,明確將去杠桿放在穩增長的任務之前,不會為保增長或刺激短期繁榮而任憑金融杠桿繼續回升。堅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達到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轉換增長動力、培育適應新消費需求結構的供給側生產結構,以達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的最終目標。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團學習時強調,改革開放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繁重的事業,必須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體現在經濟工作的思想方法上,就是要長期堅持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穩中求進,不為短期性經濟波動而犧牲結構性改革的長期性進程。
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創新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經濟新常態下,黨中央主動適應新的經濟發展環境,主動引領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戰略性創新舉措。旨在通過結構性改革,轉變以往要素依賴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使創新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胡鞍鋼等,2017)。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中國由上至下高度重視創新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支撐作用,“中國制造2025”計劃、大力發展人工智能等措施將有助于中國占據未來經濟制高點。難能可貴的是,全社會對創新發展理念的認識正日漸加深,創新發展對中國經濟的重大意義正日漸成為共識。從理論到實踐層面對創新的理解與運用正逐步走向成熟,如果說現代金融學的重鎮在美國,那么中國創新理論正逐步走在世界的前沿。
從近期的經濟數據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初見成效,2017年9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升至2012年以來的新高,制造業繼續保持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更值得注意的是,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同樣升至較高的景氣區間,新消費、新商業以及新生產模式的基礎正日益牢固,以深圳南山等地區為代表的區域創新生態系統充滿活力。中國經濟增長在平穩回落中開始顯示較強韌性,經濟結構逐步優化,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穩步推進,過去主要由地產和基建等投資拉動的粗放增長方式逐漸發生變化,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向縱深推進,產能過剩行業開始出清,集中度開始提高,消費升級逐漸成為總需求上升的主要貢獻力量(巴曙松,2017)。
結語
貨幣與財政政策作為短期經濟政策工具,可以在短期內起到調節經濟周期的作用。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有助于在短期內實現刺激經濟與調節景氣的政策目標,但是經濟發展的基礎畢竟應建立于堅實的產業與創新發展之上,而非憑借對貨幣流動性、基礎設施投資以及債務赤字等政策手段的依賴。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可以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工具,為推動中長期結構性改革爭取必要的時間。然而,經濟體過于依賴寬松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財政政策等短期刺激工具,可能會掩蓋其長期結構性改革的急迫性,推遲甚至阻礙結構性改革的推行。沒有結構性改革支持的大型經濟,難以維持長期可持續性增長。
近年來,歐盟、日本以及美國等經濟體迫于短期經濟目標的壓力,將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凌駕于長期結構性改革之上,以短期經濟增長目標為代價,通過寬松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財政政策等工具刺激經濟,犧牲經濟長期發展質量。長期來看,可能會陷入對貨幣與財政政策刺激的過度依賴,出現經濟放緩—貨幣投放—經濟與債務泡沫化—投資下降—經濟放緩的死循環。
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為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內運行,中國也會根據實際需要適當放寬貨幣供應與財政投資以實現穩增長的短期目標,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基礎,卻決不依賴短期的經濟刺激,而是堅定不移地推行中長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糾正要素配置過程中出現的扭曲問題,提升供給側質量,改善供給側結構,釋放生產力,以達到滿足、適應需求側結構變化的目的。
[1]楊偉民.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J].紫光閣,2017,(1).
[2]胡鞍鋼,周紹杰,任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和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2).
[3]巴曙松.客觀評價經濟調整階段銀行業的轉型進展[EB/OL].中國金融新聞網,2017-09-23.
[4]劉暢,于旭.地方政府對創新生態體系構建的引導方式研究[J].社會科學戰線,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