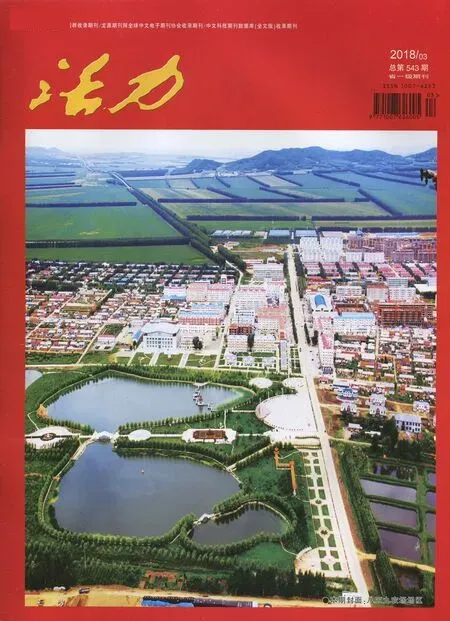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下的新聞表達(dá)的獨(dú)特性
(哈爾濱日報(bào),哈爾濱 150000)
在傳統(tǒng)的新聞媒體中,無論報(bào)紙雜志等紙質(zhì)媒介的新聞版面還是電視節(jié)目的新聞欄目,都是各自有各自的陣地,相互之間具有相對獨(dú)立性,幾乎可以用互不相干來形容彼此之間的關(guān)系。即使是在特定的情況下,因?yàn)槟骋粋€(gè)重大的新聞事件做出的連續(xù)報(bào)道,也一定是在不同的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上,以不同的視角,用不同的文本表述,不同的版面樣式,不同的視覺構(gòu)成,不同的圖片語言的運(yùn)用及欄目結(jié)構(gòu)來呈現(xiàn)給目標(biāo)受眾,這樣的表達(dá)形式,無論是從時(shí)間流演還是在空間布局的兩個(gè)維度上,都存在與生俱來的天然的割裂性。這就無可避免地造成了新聞本身的某些內(nèi)在的聯(lián)系被割斷,動(dòng)態(tài)的線性的新聞事件不得不以靜態(tài)表達(dá)的方式來講述和展現(xiàn),這是傳統(tǒng)媒體命定的無奈。
也正是由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媒體養(yǎng)成的這種線性的表達(dá),造成了習(xí)慣性的更重視新聞事件及新聞作品自身內(nèi)部的組織結(jié)構(gòu),強(qiáng)調(diào)新聞要素的完整。
在網(wǎng)絡(luò)新聞中,特別是在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成為網(wǎng)絡(luò)的主流,手機(jī)已經(jīng)“進(jìn)化”成了人體的外置器官,新媒體為代表的各種超級APP,成了伴隨式媒體,社交媒體的廣泛應(yīng)用和崛起,在時(shí)間和空間相互統(tǒng)一的節(jié)點(diǎn)上,各種新聞與評論的信息同時(shí)爆發(fā),不斷匯集,新聞事件的報(bào)道和表述,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在不斷變化中的動(dòng)態(tài)生成的過程。新聞表述已經(jīng)成為一種生態(tài)。
一、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背景下網(wǎng)絡(luò)話語的碎片化
這個(gè)生態(tài)的生成,伴隨著新聞事件的整個(gè)發(fā)展,新媒體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在網(wǎng)絡(luò)語境中呈現(xiàn)出“碎片化”的特征。
短小精煉是其主要特征,選取的是一個(gè)短暫的片段或側(cè)面,以情緒化、短語句等具有“網(wǎng)感”的語言,在新聞中追蹤報(bào)道當(dāng)前發(fā)生的事件,已經(jīng)成為新聞表述的不二法門。
所報(bào)道的某一個(gè)片段,與其他報(bào)道和片段,匯總聯(lián)系起來互相支撐,互相渲染,成為互為新聞的呼應(yīng),這其中的每一個(gè)報(bào)道、評論、事件片段等等節(jié)點(diǎn),都已經(jīng)成為新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彭蘭在《網(wǎng)絡(luò)新聞學(xué)原理與應(yīng)用》中曾經(jīng)提到過,網(wǎng)絡(luò)新聞在報(bào)道手法上表現(xiàn)為 “為追求時(shí)效性而進(jìn)行頻繁的動(dòng)態(tài)更新,容易形成新聞的‘瞬時(shí)化’或‘碎片化’:一些新聞在網(wǎng)站中轉(zhuǎn)瞬即逝,事后很難查證;一些新聞只能支離破碎地展示新聞事件的各個(gè)片斷,很難全面深入地體現(xiàn)新聞事件的本質(zhì)”。
正是這樣的“碎片化”表達(dá),使得記者對新聞的掌控大大地下降了,每一個(gè)受眾其實(shí)都成了制作新聞作品的參與者,成了新聞事件的傳播者。
在這樣的動(dòng)態(tài)的報(bào)道的過程里,受眾在建立對新聞事件的理解結(jié)構(gòu)上有了更大更多更廣泛的發(fā)言權(quán),從這一個(gè)層面上來理解,受眾的參與,既是對新聞作品的解構(gòu),又是對新聞作品的豐富。
二、網(wǎng)絡(luò)話語表述的自由化
在比較傳統(tǒng)媒體新聞報(bào)道的語言表達(dá)和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背景下的新媒體話語的表述特征時(shí)會(huì)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luò)賦予了人們更多的話語權(quán)、解構(gòu)權(quán)。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背景下的受眾成了新聞報(bào)道的參與者,眾多的人數(shù)使得其話語的表述也更加自由、豐富、多樣。
正如前文所述,網(wǎng)絡(luò)話語在新聞報(bào)道中生產(chǎn)突破了法律、政治、社會(huì)、文化等因素的制約,在事實(shí)層面上,無論從話題的選擇,新聞片段的展示還是具體報(bào)道話語的具體表述,都更充分地表現(xiàn)出了更自由、更大膽的特征。
在我們接觸到的各大網(wǎng)絡(luò)媒體中,無論是“傳統(tǒng)”PC端,還是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背景下的主流的新媒體矩陣們,形式上都可以繼續(xù)的開設(shè)專題,對熱點(diǎn)事件進(jìn)行追蹤報(bào)道。“海量信息”“海量的文字”,是成千上萬的受眾參與者,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文字習(xí)慣,語言順序和結(jié)構(gòu),把相同的新聞片段表述出來,體現(xiàn)出表述的自由。
我們經(jīng)常會(huì)看到這樣的報(bào)道現(xiàn)象,對相同的新聞片段或新聞事件的報(bào)道,以不同的標(biāo)題呈現(xiàn)出來,并且可以相安無事在一個(gè)專題里面共存,這樣的重復(fù)報(bào)道,在報(bào)紙等傳統(tǒng)媒體中是不允許存在的。但是,在網(wǎng)絡(luò)新聞報(bào)道中,顯得理所當(dāng)然,并且更能突出強(qiáng)化這一新聞的力度。
即使是在新聞話題和報(bào)道語言的選擇上,網(wǎng)絡(luò)形式也可以說無所不包,形式各異,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的是更為寬松的自由度。
往往可以看到這樣的現(xiàn)象,一個(gè)新聞事件有高雅、嚴(yán)謹(jǐn)?shù)年柎喊籽┑臅嬲Z言報(bào)道和評論,也充斥著是低俗、下里巴人的口語表達(dá)。這些形態(tài),在網(wǎng)絡(luò)報(bào)道中都可以被集中地、完整的、完全的呈現(xiàn)出來,這更是傳統(tǒng)媒體的報(bào)道中所不可能出現(xiàn)的。
面對這種網(wǎng)絡(luò)的“自由”,人們各抒己見,相互之間平等對話,百家爭鳴。
一言以蔽之,網(wǎng)絡(luò)新聞報(bào)道中呈現(xiàn)的報(bào)道話語的形態(tài),其種種特征形成了網(wǎng)絡(luò)的獨(dú)特文化、獨(dú)特生態(tài)。這種生態(tài),是網(wǎng)絡(luò)文化和現(xiàn)實(shí)中文化的種種碰撞產(chǎn)生的耀眼的火花,是事實(shí)上的傳媒話語的再生產(chǎn)、再實(shí)踐與再控制。這種再生產(chǎn)、再實(shí)踐與再控制與其他形式的話語如政治、經(jīng)濟(jì)、法律、道德、宗教、科學(xué)、文學(xué)、藝術(shù)等有著密切關(guān)系,同時(shí),具有自身的獨(dú)一無二的獨(dú)特性。
[1]彭蘭.網(wǎng)絡(luò)新聞學(xué)原理與應(yīng)用[M].北京:新華出版社,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