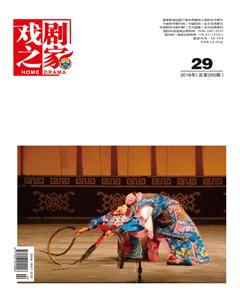侯孝賢鏡頭語言與歷史敘事
吳鳳鳴
【摘 要】侯孝賢作為臺灣電影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美學風格被影評家焦雄屏評為“混雜了東方式內省與凝練,以及西方式的客觀及疏離。”他試圖在影像中找尋歷史真實,努力嘗試成就真實面貌,并在此努力中產生出他特有的電影語言,如使用“長鏡頭”“深焦構圖”“空鏡頭”與“固定鏡頭”。這樣的表現手法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年輕導演甚巨,亦使新電影的陳述方式與傳統產生極大的改變。
【關鍵詞】侯孝賢;長鏡頭;空鏡頭;固定鏡頭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1007-0125(2018)29-0076-02
在臺灣,“歷史的影像化書寫”一直要到“臺灣新電影”出現后才浮現出來。敲響這一記鐘聲的代表,當侯孝賢莫屬。隨著臺灣電影發展至今,他依然是站在此線奮戰的勇士。侯孝賢獨特的電影成就除受到國際上極大的肯定外,也帶給臺灣影業創作者深切的鼓舞與提升。侯孝賢自稱他對電影“著迷于真實到偏執的地步”,也是他拍片最為痛苦的地方,這樣的堅持成為他創作電影的訴求。侯孝賢重視空間的營造、環境、演員的真實性,是為了讓這種影片更具質感、更有震撼力,而絕不是僅僅為了表層的與現實生活的相似、逼真。這也是侯孝賢越追求真實越主觀、越風格化的原因。的確,這正是一種東方式的含蓄美感,不強調詮釋個人的情感,凡是過激的表現都不符合文化現象。為了完成這種追求真實的過程與境界,侯孝賢的美學風格展現出“混雜了東方式內省與凝練,以及西方式的客觀及疏離。”他試圖在影像中找尋歷史真實,在內蘊的情感表現中看到真實,這都是他努力成就真實面貌的嘗試。總結他特有的電影語言,有“長鏡頭”“深焦構圖”“空鏡頭”與“固定鏡頭”,這些都是他追求真實下所激發出的特定體會與方式,并形成其特有的風格特色。
一、距離深遠的長鏡頭
讓鏡頭拉得遠,導演看似隱入了一個較為不具主導地位的立場,對一個喜歡戲劇情節為主導的觀眾來說,將因此看不到濃厚的戲份;這樣的運鏡方式對氛圍的掌控卻是可以籠罩全局的,導演在此反而可說是另一種不同形式的主導。換言之,演員在導演提供的既定素材空間里,活出角色的生活面貌,企圖更加貼近現實,并自由發揮演出,當然可以更貼近歷史感。
侯孝賢這樣的“長鏡頭”使用現象,原因有三點:第一,是其自稱因采用非演員,怕攝影機接近時驚動到他們。第二,歷史的縱深需要長鏡頭帶出距離感。第三,從導演的長期偏好中,看到了其獨特詮釋歷史的敬畏感。此三點是我們進一步分析其風格的重要因素。
就第一點而言,曾有人問侯孝賢拍片是否真受了小津的影響?他也曾解釋,“以前我的不動,是因為我喜歡用非演員。而非演員,最好不要驚動他們。不能太靠近,若架了軌道拍到他們面前,他們就不見了。所以用中景,拍得長,讓他們在我給的環境材料里活動,我盡量捕捉而已。為了捕捉真實,重組真實,以及對真實無以名之的偏執,就變成這樣不動了。”[1]
無怪乎侯孝賢在1983年至1987年間一直不采用明星,直到《悲情城市》后才逐步開始有明星演出。雖然起因多少包含了“臺灣新電影”成本不足的無奈與對舊有拍攝手法的一種反動,但這樣的處理方式的確是向傳統宣告了一種迥異的電影語言。
就第二點而言,歷史的縱深的確需要長鏡頭帶出距離感。李天鐸、陳蓓之在《八十年代臺灣新電影的社會學再探》一文中,特別說明新電影有一個共同的傾向,“舍棄動力式剪接的運用,而有意圖地‘場面調度,……新電影的‘場面調度是運用長拍鏡頭與深焦構圖來加大畫面時間與空間的容量,然后再用固定的中、遠景鏡頭來攝取畫面中的人事物,而讓信息經由三者的互動自然呈現……讓劇情緩緩地在觀眾的‘見證下展示開來。”[2]
今日回頭反省這樣的鏡頭運動方式,不論一開始是因成本的局限還是年輕導演對舊有方式刻意的反動,這樣的開創,對歷史的詮釋確實是有需要的,也就是說,當我們處理具有歷史縱深的時代時,長鏡頭可以呈現距離感,充分成全了觀眾一份想象回憶的含蓄空間。
至于第三點,則是我們由導演長期關注的重點看到了導演特殊的人文關懷,他將臺灣變遷社會中長期的失落融入其中,使觀眾在觀賞之余,不僅看到一些個人的生命歷史,還看到了鏡頭下的歷史注記,有人以文字紀錄歷史,侯孝賢則是以影像紀錄歷史。在有距離地窺看歷史過程中,觀眾已陷入時代氛圍中,產生時代的趣味感。
所以侯孝賢自稱“不能太靠近,若架了軌道拍到他們面前,他們就不見了。”其實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不見了”的恐怕不只是演員,而是觀眾需要回蕩的空間會不見,導演需要切進歷史的點也會不見,最怕“不見了”的,恐怕是觀眾本身吧。
二、情感充沛的空鏡頭
東方人的美感表現是一種含蓄的表現方式,戲劇營造不濃烈,情緒也不太過張揚,如此的表現手法才能有意猶未盡的感覺。正如喜悅與悲傷,為了使情感表現不過激,演員最好不要一次表演完畢,內容也不要以情節取勝,“耐人尋味”才是最佳。但是如此的表現手法,戲劇性自然較弱,加上不去刻意營造,表現面自然較少,這又應該如何補足才好?
侯孝賢電影中常用“空鏡頭”來補足。其實這種方式許多導演都會使用,侯孝賢顯然只是特別喜歡罷了。有時為了堅持固定鏡頭長拍的方式,縱使人物走出鏡頭,也依然以空鏡頭來沉淀觀眾的情緒,如《好男好女》片頭與片尾,拍片者唱歌通過空地,最后走出畫面;他更以空鏡頭視為一種詮釋主角或情境的隱喻,這種只有畫面而無人物的空鏡頭出現,是長鏡頭極佳的補充,使原本在長鏡頭中無法明顯表達的含蓄情感,都能透過空鏡頭表達出來。
既然如此,空鏡頭的時序安排就很重要了,時序比鄰的交互詮釋往往會是其重點,看它是被安排在哪里,便會得到不同的詮釋。
如《童年往事》,母親生病前有風雨欲來的烏云鏡頭,暗示生變;生病后送院,母親噩耗傳來,天空也雷聲隆隆。都是鏡頭含蓄詮釋情節心情的一種方式。又如《戀戀風塵》中男主角阿遠發生“兵變”,女主角阿云與天天為她送信的郵差結婚了,下一景空鏡頭的處理是拍黃昏金門海邊的木麻黃被風雨無情地刮著,以大自然的現象表露了主角的心境,笛聲悠揚,吉他勾弦出異樣的聲情。全片最后,阿遠回家,穿著當年阿云為他做的衣裳,蹲在大石頭上,靜靜聽著爺爺反復在田埂上說那番耕種困難的話:“不種蕃薯不下雨,一種蕃薯,臺風就來了……”“照顧蕃薯比照顧巴參還累。”兩人的視野望向天空,鏡頭以水墨的山城風光作結束。山上灰黑的云逐漸罩落下來,遠處平靜的大海流云,當光影浮動飄過山脈時,大有影過山無痕,隱喻人原就是融合在大自然中的脈動中,處理這一對情侶的愛戀,竟在連續包容的含蓄鏡頭里,對生命無常提供了深切的反省,讓生活的堅韌與化境凝注在大自然中。這種充滿情緒意義的帶動,一種“有感情的空鏡頭”,遂成為侯孝賢鏡頭的另一種特色。
三、客觀的固定鏡頭
一般而言,電影鏡頭若拉近拍攝,畫面不易持久;侯孝賢采用固定鏡頭,是延續了長鏡頭拍法上的搭配,但要補足這冗長的缺點,最適合的做法就是在不動的鏡頭中讓元素移動以增加長鏡頭的持續力,在侯孝賢所拍的片中,長鏡頭畫面最常出現的動態現象有兩種。
一種是鏡頭放空,聲音不放空。在侯孝賢電影中常出現的聲音有兩種,一種是收現場音;另一種是搭配音樂。采用現場收音的方式,是為了追求聲音的臨場感,這顯然符合侯孝賢堅持真實的原則。所以在一段漫長的長鏡頭中,觀眾可能需要屏息以待。至于搭配音樂,作用往往與空鏡頭使用類似,帶有象征或隱喻的作用,更甚而是導演內心世界的情感表露。如早期《風柜來的人》,當最后年輕人為同伴在市場上登高拍賣錄音帶時,市場中的種種鏡頭搭配了交響樂曲,那是侯孝賢心中的青春樂曲悠揚升起,距離與回顧味濃,但這種做法與后期作風是大相徑庭的,正如《南國再見,南國》中重金屬音樂的大分貝,不斷與車子的行進交疊;《咖啡時光》靜子每回尋訪作曲家故居時,作曲家的背景音樂就會響起,詮釋的都是銀幕中人物本身的點點滴滴。
但是配樂終究在侯孝賢片中占少數,就量而言,現場收音占多數。所以,這種以自然音為主的方式,當畫面一旦靜態不動,聲音劃過,便會產生一種心情上的變動,亦可算是另一種動態的搭配了。
第二種是背景物件移動畫面。利用物件移動使畫面產生活潑性,也是一種很好的搭配。交通工具是最常使用的物件,尤其是在侯孝賢的電影里,在所有物件移動的氛圍中,火車顯然是一個最為重要的物件。從《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戀戀風塵》《悲情城市》《咖啡時光》等都可見到火車,車站、列車廂內、行進中火車穿越山洞,顯然這都是侯孝賢常見的表現手法。
侯孝賢早年被訪問時說:“在臺灣,火車是一種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小時候我常搭火車,氣氛十分誘人,因此長大后對火車我仍然無法忘懷。像《戀》影片中,火車鐵軌出現比例比道路要多。”[3]
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是侯孝賢大部分作品中存在的問題,其背后蘊含的意義,充分道出其成長背景的人文精神。火車可說是表現鄉愁、時序變遷最容易產生共鳴的符號,正如小津安二郎影片中所出現的輪船、船鳴是一樣的,借由畫面中的交通工具,產生一種時序移動了的感覺,讓原本定格許久的畫面增加生動感。其實物件內容不僅限于火車或交通工具,侯孝賢的電影更靈活運用了光影移動、風吹云動等產生畫面的靈動,讓畫面縱使是靜止的空鏡頭,也能有大自然的動態演出。
四、結語
可以說,侯孝賢的電影帶有的東方美學色彩,正是指其含蓄的特色,而侯片的精湛在于其成功融合了看似矛盾的含蓄的東方美與追求寫實的精神,以時代寫真,以技巧寫意,這成就了侯孝賢獨特的電影語言,不論是長鏡頭、空鏡頭、深焦構圖與固定鏡頭,還是忽略敘事的因果關系,這不僅僅是一位導演的習慣問題,還會與其主題陳述具有密切的關聯性。他試圖在影像中找尋歷史的真實,在內蘊的情感表現中看到真實,在影像中展現東方美學,這都是侯孝賢努力成就真實面貌的嘗試。
侯孝賢之所以被認定為臺灣新電影的代表人物,除了其個人的電影成就外,更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是他的時代使命感。他將面對時代的責任融成了影像陳述,影響的不只是電影,陳述的也不只是歷史,而是將藝術觀念不斷突破與實踐。如此的人文關懷者在任何時代都是值得贊許的。
參考文獻:
[1]侯孝賢.尋找小津-一位映畫名匠的生活旅程[M].高雄:高雄電影圖書館,2003.
[2]李天鐸,陳蓓之.八十年代臺灣新電影的社會學再探[J].電影欣賞,1990:75.
[3]蓮實重彥.侯孝賢訪問錄[J].電影欣賞,1988,(11):62.
——以《山河故人》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