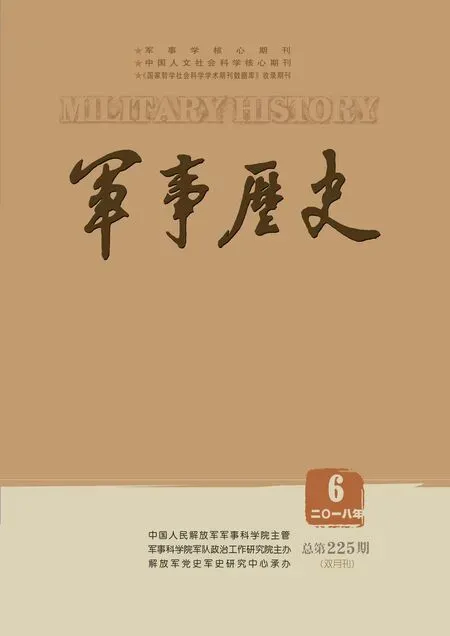外文數據庫應用與“一戰”史研究*
★
第一次世界大戰(簡稱“一戰”)結束已有百年,中外學者在不同時期做出了各有側重的研究。信息時代、數據平臺,為更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一戰”史提供了良機。文章在概述近二十年來“一戰”史研究狀況的基礎上,介紹幾種優秀的外文數據庫,并對如何利用機遇、迎接挑戰作以總結。
一、近二十年來“一戰”史研究概述
“一戰”開啟了人類戰爭史的新紀元。百余年來,人們從不同角度研究并書寫這段歷史:傳統史學關注帝王將相的軍事決策和關鍵性戰役;二戰后興起的新軍事史關注普通士兵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狀態;21世紀初,環境史學者逐漸關注前線士兵與戰爭環境的互動——人們書寫“一戰”史的視野逐漸下移。
近20年來,西方學者的“一戰”史研究成果豐碩。既有從傳統軍事史的角度對“一戰”起因的再思考,也有關于“一戰”戰略戰役戰術的煌煌巨著;①如Hew Strachan,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既有前線官兵的戰時經歷,也有少數族裔和戰俘的歷史影響;②如[法]雅克·梅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士兵的日常生活(1914—1918)》,項頤倩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Tim Grady, The German-Jewish Soldier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History and Memor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1;Heather Jones, Violence against Prisoners of War in the First World War: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1914-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既有塹壕體系中的人地關系,也有駐軍對阿爾卑斯山的遐想。③如Dorothee Brantz, “Environments of Death: Trench Warfare on the Western Front, 1914-1918”, in Charles E. Closmann ed.,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ry Destruction in the Modern Age,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Press, 2009; Tait Keller, “The Mountains Roar: The Alps during the Great War,”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4, No. 2, 2009, pp.253-274.
此外,還有統一的學術組織。國際“一戰”史研究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First World War Studies)2001年9月8日成立于法國里昂。研究會旨在開展跨越國家和學科界限的學術討論,鼓勵同資深研究者的對話,促進創新研究,并通過研究加強公眾對“一戰”的理解。[注]http://www.firstworldwarstudies.org/about.php,訪問時間:2018-10-11.會刊《“一戰”史研究》17年來共發表“一戰”史論文120篇,書評83篇,涉及戰爭進程、起因影響、前線后方、女性及少數族裔、帝國與殖民地、人口資源與環境等。
近20年來,《世界歷史》、《軍事歷史》和《軍事歷史研究》共發表國內學者相關論文23篇。《世界歷史》共11篇,含5篇國際關系史,2篇政治史,4篇新軍事史。《軍事歷史》共5篇,含2篇傳統軍事史,3篇新軍事史。《軍事歷史研究》共7篇,含5篇國際關系史,1篇國別史,1篇新軍事史。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國內學者對“一戰”的關注與研究,主要集中在國際關系史等傳統領域。
有學者明言:“最有挑戰性的并不在于‘一戰’的起因、經過和結果,這些研究都已很充分……始終困擾我們的問題在于,幾百萬人如何以及為何能在這場總體戰中堅持四年。”[注]Graham Seal, The Soldiers’ Press: Trench Journal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reface, p.xi.可見,“一戰”史僅有宏大敘事是不夠的,尚需微觀的個案研究。法國“一戰”后已出現的對一線士兵日常生活的審視,就有助于增進對“一戰”的認識和理解。但若想開展這樣的研究,需要對一手史料的獲取和解讀。外文數據庫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史料難題,中國學者得以與西方學者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就“一戰”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
二、各具特點的“一戰”外文數據庫
目前國內可見的“一戰”外文數據庫主要來自三個機構:美國信息服務商普若凱斯特(ProQuest)公司、英國亞當·馬修學術出版社(Adam Matthew Digital,AMD)和英國在線檔案館(British Online Archives,BOA)。這些機構在建立各自的“一戰”數據庫時注重專題、避免重復、窮盡信息。因此內容各有側重,風格各具特點,為“一戰”史研究提供了豐富、多元和用戶友好型的在線電子資源。
普若凱斯特公司與帝國戰爭博物館和大英圖書館等機構合作,創建了“‘一戰’塹壕期刊和部隊雜志數據庫”(Trench Journals and Unit Magazin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塹壕期刊和部隊雜志,是“一戰”西線基層部隊自辦的出版物,內容、立場和視角與官方出版物多有不同,英、法、美、加、德軍都有出版。塹壕期刊由步兵、炮兵、工兵等部隊自辦;部隊雜志則由醫院或醫療船、戰俘營以及救世軍、“士兵妻子與母親聯盟”等民間組織自辦。數據庫收錄戰地出版物有英法德三種語言、共1500多種,時間從1914年一直到1919年底。二者主要刊登詩歌、繪畫、短篇小說、笑話、戲劇和文章,多數作者使用匿名或者化名,此外還有些商品廣告。這些文獻直接來自前線官兵并服務于前線官兵,收藏了官方檔案忽略的戰地生活與戰斗信息,為系統研究雙方老兵的戰時經歷與思想狀況提供了直接史料。
亞當·馬修學術出版社的“一戰”專題數據庫有四個子庫,分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經歷》(The First World War: Personal Experiences)、《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傳與征兵》(The First World War: Propaganda and Recruitment)、《第一次世界大戰:可視化資料與情景紀實》(The First World War: Visual Perspectives and Narratives)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全球沖突》(The First World War: A Global Conflict)。數據庫收錄的文獻資源與珍貴資料,來自世界各地的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和戰爭紀念館。
《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經歷》收錄了大量日記、信件、明信片、隨筆、剪貼簿、個人物品照片和回憶錄等珍貴資源。這些資料不同于官方出版物或官方發行的報紙,而是從戰爭親歷者的視角,通過他們的描述或記錄來展現“一戰”的方方面面。主要的內容與主題包括:軍隊及內勤的日常生活與常規事務、塹壕戰與戰爭情景、前線食品供應與后勤補給、戰役與沖突、軍事訓練與軍隊紀律、作戰武器與戰斗裝備、戰友情誼、戰爭與死亡、健康與醫療、敵軍的情報偵察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傳與征兵》重點收錄戰爭期間政府、輿論和相關機構對戰爭宣傳的各類資料,文獻類型包括手稿、宣傳海報、明信片、傳單、手冊、報紙消息摘錄和圖片等。主要內容與主題有:征兵與訓練、前線士氣與后方士氣、不同宣傳形式的影響效果、革命與叛亂的潛在影響、通過審查制度控制群眾意見的效果、爭端與糾紛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可視化資料與情景紀實》收錄了大量攝影照片、手稿、畫作與海報、個人記述資料、視頻剪輯和實物照片等。其中的攝影照片反映了澳大利亞、法國、加拿大、美國和德國等國軍隊作戰以及戰場的場景,如陸海空戰、部隊行軍照片、塹壕戰、戰爭前線志愿者服務、戰俘、難民和軍事運輸等。手稿包括前線戰士與親朋的來往信件、戰爭志愿者服務記述等。畫作與海報收錄了400多幅油畫和300多幅水彩畫、鉛筆素描,以及大量宣傳海報、戰爭中描述女性的宣傳材料等。個人記述包括大量的戰時日記、前線的所見所感等。視頻剪輯共45段,展現了當時的戰爭場景,如軍隊行軍、作戰、醫療服務等。3D實物照片共200多張,包含作戰武器及裝備、交通工具、軍隊制服和徽章等,其獨到之處在于可以用鼠標拖動、旋轉、縮放和打印,方便讀者從不同視角審視實物的整體與局部。
《第一次世界大戰:全球沖突》大量收錄了相關官方文件和民間文件,包括日記、手稿、口述史資料等,有助于從全球的視角審視“一戰”,特別是西線之外的、以往被忽視的帝國和殖民軍隊。主題包括了巴爾干、俄國、非洲和中東遠東地區的戰事,華工的貢獻,德國、奧匈帝國和意大利方面的視角,美國的參戰,封鎖與海戰,空襲,愛爾蘭的動蕩,俄國革命,淪陷區生活,巴黎和會,戰后裁軍、救濟與重建等。數據來自加拿大葛倫堡博物館、美國胡佛研究所圖書館和檔案館、英國帝國戰爭博物館和國家檔案館。這一數據庫有著不同于前三個數據庫的亮點:一是提供了英國政府檔案,自上而下地了解當時英國殖民地軍隊的參戰情況,英國參與的海戰、空戰以及和談等;二是提供了有關俄國革命的日記、官方報道等;三是收錄了大量西方士兵以外的、世界其他國家軍人的戰時經歷;四是收錄了英美紅十字會以及戰爭受害者救助委員會的相關記錄,有助于開展醫療史、戰后救助與重建的研究。
除“一戰”專題數據庫外,亞當·馬修學術出版社還建有“醫療服務與戰爭:1850—1927”數據庫(Medical Services and Warfare: 1850-1927),著重收集了克里米亞戰爭、美國內戰和“一戰”期間的醫學報告與病例,以及回憶錄、日記、照片、明信片和實物等。數據庫全面收錄了南丁格爾的5000余封書信、筆記和報告,并通過智能識別技術,可對手寫文稿進行全文檢索。所錄內容為深入研究當時醫療服務與戰爭之關系的演變,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尤其是審視在“一戰”這樣的總體戰中,醫療兵的經歷、戰地搶救技術與規章、敵我關系與醫患關系時,數據庫內容彌足珍貴。
英國在線檔案館建有“戰爭研究專題數據庫”,其中與“一戰”相關的內容也較為豐富,主要收錄在以下四個子庫中。
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軍官日記,1914—1919”(British officers' diaries from World War I, 1914-1919),大量收錄了來自英國帝國戰爭博物館的“一戰”紀實資料,比官方記錄更豐富、更真實地反映了英國官兵的見聞,如何準備戰斗,如何在戰爭中生存,心理狀況等。其最大的價值在于,通過分析參戰官兵的書信和日記,可以了解不同銜級官兵的戰爭認知。
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反戰運動”(Conscientious Objection during the World War I),收錄了英國法庭和民主聯盟關于反戰運動的全部檔案資料,反戰者聯盟組織的完整報告,以及大量會議紀要和精英人物的言行記述。上述手稿、報告、會議紀要、新聞剪報、筆記和小冊子,記述了參加者的個人經歷,也反映了“一戰”期間英國反戰運動的整體情況,是研究反戰運動的珍貴資料。
三是“英國軍事家檔案:軍事戰術與軍事史,1881—1935”(Military tactics discussed in letters to and from military leaders, 1881-1935),收錄大量來自英國國家軍事博物館(National Army Museum)的珍貴手稿。如戰術與軍事史專家亨利·斯潘塞·威爾金森(Henry Spenser Wilkinson,1853-1937)與伊恩·漢密爾頓(Ian Hamilton)上將、威廉·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元帥等指揮官間的書信,以及“一戰”重大戰役的戰術問題等文章,反映了英軍高層對“一戰”相關行動的認知與反思。
四是“英國外交官報告:第一次世界大戰與西班牙內戰,1863—1939”(World War I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as reported by an Ambassador, 1863-1939)。埃斯梅·霍華德(Esme Howard)曾任英國駐西班牙大使(1919-1924)和英國駐美國大使(1924-1930),經歷過諸多重要歷史事件。數據庫收錄了霍華德從政期間的各類資料,包括個人手稿、來往公文、政治與外交檔案、重大戰爭與歷史事件期間的外交斡旋文獻記錄等。資料涉及的歷史事件包括“一戰”、巴黎和會和西班牙內戰等。
三、基于數據庫深化“一戰”史研究
上述數據庫收錄的大量一手文獻,對中國學者從事原創性的世界史研究助力不少。筆者以“‘一戰’塹壕期刊和部隊雜志數據庫”為例,談談數據庫為深化“一戰”史研究提供了哪些可能。
首先,通過生活史研究,了解“一戰”具象。筆者與學生依托“‘一戰’塹壕期刊和部隊雜志數據庫”,探討了西線塹壕中的人鼠關系,梳理了人鼠之間的互動關系變化軌跡,通過對具體問題的深入研究,對前線戰地環境與官兵經歷和戰爭記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初步探索。[注]詳情參閱賈珺、考舸:《“一戰”西線塹壕中的人鼠關系》,《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數據庫有關塹壕鼠的信息,有影像史料和文字史料兩種。影像史料包括照片和繪畫,筆者從所載老鼠的耳廓形狀、尾長與身長之比等特征,判斷塹壕鼠的種屬為褐家鼠,繼而結合文字史料判斷褐家鼠跟隨部隊輜重來到野地,雜食性使褐家鼠成功替代了原有的優勢種群——田鼠,也給駐軍帶來了鼠患。從戰地刊物上的官兵書信、擬人化小品、捕鼠方法大全、鼠皮收購廣告等文字史料,可以梳理出人鼠相遇—鼠騷擾人—人捕滅鼠—人鼠共生的變化軌跡。這一研究看似碎片化,實則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停滯的戰線對前線官兵的摧殘,以及人性在戰爭中的扭曲與調試。由此,一位法國老兵將自己的回憶錄命名為《一只老鼠的回憶》也就不再讓人詫異了。
其次,借力數據分析,做些比較研究。數據庫的便捷還體現在進行數據對比和分析的可能性上。眾所周知,“一戰”期間中國北洋政府以工代戰,近二十萬勞工前往歐洲戰場服務。他們的境遇如何?形象如何?筆者使用“Chinese”、“Chinese + labour”和“Chinaman”進行搜索,命中數分別是3079、302、485。“Chinese”較為寬泛,對勞工的指向性不強;“Chinese + labour”對勞工的指向性強,但命中數最少;“Chinaman”的命中數居中。帶有貶義色彩的“中國佬”命中數高于公允的“中國勞工”,足以說明當時中國勞工的境遇。用“Chinaman”指代的中國勞工,通常是怎樣的形象呢?筆者在“Chinaman”命中項里找到一篇來自塹壕期刊——《加拿大生活》——的短文,題為《可憐的剃頭匠》,[注]“Pity the Barber”, la vie Canadienne, Mar.1, 1917.講的是有個中國勞工去理發,剃頭匠稱“1.5法郎全套服務”,但這個“全套”在中國勞工看來是“圈套”——剃頭匠理過頭發、刮過胡子后就收工了!中國勞工非常氣憤,大聲說話并比劃著要求剪指甲、掏耳朵。剃頭匠勉強做了這些,要求漲價到5法郎,圍觀者紛紛嗤笑,認為中國勞工貪小便宜,掏耳朵的要求尤其過分。這實際上體現了文化的差異,因為這些服務在中國理發師傅那里確屬“全套”,且還應加上修眉和剪鼻毛兩項。“全套”還是“圈套”,評價標準都來源于人們自身的生活經驗,類似的矛盾或是笑話恐怕還有不少。
第三,整合政府檔案與民間資料,共同建構“一戰”全景。盡管歷史學者運用新軍事史和新社會史等理論與方法,改宏大敘事為微觀研究,使“小人物”因其在戰爭中的“個人史”“生活史”為人所知而不再沉默,體現了新史學不同于傳統史學的志趣與貢獻,但是傳統史學的價值同樣不應忽視。政府檔案的準確性往往要高于個人資料,且較少受個人情緒、知識結構以及眼界的制約,因此要充分利用數據庫,有效整合政府檔案與民間資料,共同建構“一戰”全景。惟有如此,才能全面和深入地審視“一戰”,反思世界和平之不易,批判帝國主義之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