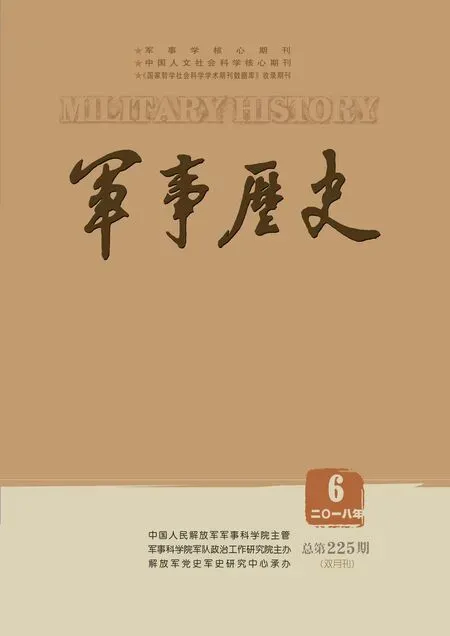恩格斯戰(zhàn)爭預(yù)測思想探析
——基于《戰(zhàn)爭短評》的研究與思考
★
1870—1871年普法戰(zhàn)爭,引起了當時遠在英國倫敦的恩格斯的高度關(guān)注。自1870年7月29日起,他不斷為英國倫敦一家著名報紙——《派爾—麥爾新聞》的專欄撰寫“戰(zhàn)爭短評”。這些評論文章顯示出恩格斯敏銳的戰(zhàn)略判斷能力,特別是分析戰(zhàn)爭進程的高超技藝。他的預(yù)言一再為戰(zhàn)場事態(tài)發(fā)展所證實,因此引起了當時歐洲軍政界和輿論界的普遍轟動。恩格斯之所以能夠透過戰(zhàn)爭迷霧直擊戰(zhàn)爭發(fā)展的實質(zhì)與要害,關(guān)鍵在于他能夠準確把握決定和制約戰(zhàn)爭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
一、預(yù)測戰(zhàn)爭首要是深刻把握戰(zhàn)爭與政治的緊密聯(lián)系
政治對戰(zhàn)爭進程乃至最終勝負的影響通常是最具有決定意義的。恩格斯之所以能夠深刻了解普法戰(zhàn)爭,預(yù)見其大體發(fā)展趨勢,首先就得益于他對戰(zhàn)爭與政治關(guān)系的深刻把握。正如恩格斯在戰(zhàn)爭爆發(fā)伊始指出的,“只要概略地觀察一下政治和軍事形勢就夠了”①《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北京:戰(zhàn)士出版社,1982年,第95頁。。這里所要觀察的“政治和軍事形勢”并非各自孤立存在,而是一種立足于緊密聯(lián)系的透徹分析。
(一)切實把握政治對戰(zhàn)爭的支配作用,成功預(yù)言戰(zhàn)爭的爆發(fā)與結(jié)局。恩格斯在看待戰(zhàn)爭與政治的關(guān)系問題時指出,政治不僅能夠?qū)е聭?zhàn)爭的爆發(fā),而且還能夠影響戰(zhàn)爭的一切方面,甚至是戰(zhàn)爭的結(jié)局。這是恩格斯考察一切戰(zhàn)爭必然遵循的首要原則。恩格斯并不是將普法戰(zhàn)爭視為某個孤立事件,而是看做交戰(zhàn)雙方平時和戰(zhàn)時政治的繼續(xù)。戰(zhàn)爭前夕,歐洲的許多人都寄希望于通過和平途徑解決兩國的外交爭端,恩格斯卻明確指出,不存在這種可能。他清楚地認識到,法皇拿破侖第三所奉行的對外擴張、對內(nèi)鎮(zhèn)壓政策,發(fā)展到19世紀70年代末,除了乞求于對外戰(zhàn)爭已無其他任何選擇,即“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國的階級斗爭篡奪了政權(quán),并且以不時進行的對外戰(zhàn)爭來延長自己的統(tǒng)治……1870年7月的軍事陰謀(指發(fā)動對普戰(zhàn)爭——引者注)不過是1851年12月的政變的修正版”②《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86—87頁。。而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為了增強本國在歐洲同法國爭霸的地位,掃清德國統(tǒng)一道路上的嚴重障礙,也認定惟有訴諸武力方能奏效。“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戰(zhàn)爭,還能期待什么呢?”[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89頁。在恩格斯看來,這種孕育著戰(zhàn)爭危險政治的延續(xù)必然導(dǎo)致一場你死我活的王朝戰(zhàn)爭。
正如恩格斯所預(yù)言,這場戰(zhàn)爭很快就不可避免地爆發(fā)了。1870年7月19日,法國對普魯士宣戰(zhàn)。一些資產(chǎn)階級軍事專家紛紛斷言,準備充分的法軍將在戰(zhàn)爭中獲勝,恩格斯則指出,戰(zhàn)爭對拿破侖第三“不可能有完美的結(jié)局”,普魯士一定能擊潰他的全部軍隊。這一后來得到完全證實的預(yù)言,正是恩格斯通過對法國戰(zhàn)前的政治的深入分析得出的。拿破侖第三統(tǒng)治下的法國在發(fā)動戰(zhàn)爭之前,國內(nèi)的階級矛盾已相當激化;第二帝國本身腐朽透頂:盜用公款、營私舞弊、假公濟私等惡劣現(xiàn)象遍布全國一切行政部門。因此,普法戰(zhàn)爭剛一開始,法軍就出現(xiàn)了人員不齊、裝具不足、給養(yǎng)極差等混亂狀況,從而使本來處于進攻地位的法軍在戰(zhàn)爭最緊要的關(guān)頭丟掉了幾乎一星期時間,喪失了戰(zhàn)場上的一切主動權(quán),以致造成爾后的一敗再敗,直至第二帝國最后崩潰。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二帝國的軍隊迄今為止敗就敗在第二帝國本身。”[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108頁。正是在認識和分析戰(zhàn)爭時,充分考慮到政治的決定性作用,恩格斯才能在軍事行動尚未開始以前,就一眼看穿戰(zhàn)爭的結(jié)局,作出法國對普宣戰(zhàn),意味著“第二帝國的喪鐘已經(jīng)敲響了”[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88頁。的大膽戰(zhàn)爭預(yù)測。
(二)全面考察政治和軍事形勢及其緊密聯(lián)系,準確預(yù)測戰(zhàn)爭的進程。根據(jù)對政治和軍事形勢的整體分析與把握,恩格斯將普法戰(zhàn)爭初期分為兩個階段,判明兩個階段已經(jīng)或即將表現(xiàn)出來的顯著特征。他指出,從法國對普魯士宣戰(zhàn)“到目前為止幾乎還一彈未發(fā),但是戰(zhàn)爭的第一階段已經(jīng)過去,并且是以法皇的希望的破滅而結(jié)束的。”[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3卷,北京:戰(zhàn)士出版社,1982年,第95頁。為什么兩軍尚未接戰(zhàn),恩格斯就如此定義戰(zhàn)爭的第一階段?因為在他看來,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表現(xiàn)在,法皇意欲以戰(zhàn)爭初期能夠掌握的優(yōu)勢兵力,向南德意志發(fā)動突襲,以期達成“使北德意志聯(lián)邦受到南德意志各邦的孤立,并利用不久前歸并普魯士的地區(qū)所存在的不滿情緒”[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3卷,第95頁。這一政治目的,使普魯士陷于軍事和政治上的被動。但是,恩格斯指出,這樣一個計劃很快被粉碎,戰(zhàn)爭進入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因為法國軍隊的躊躇不前,特別是“德意志人民族感情的突然的強烈的迸發(fā)”,使得法國不得不面對空前團結(jié)統(tǒng)一的德意志民族及其軍隊,這“就需要用現(xiàn)有的全部兵力來進行正規(guī)戰(zhàn)以代替突然襲擊了。……于是,開始了戰(zhàn)爭的第二階段,即醞釀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階段,從這一天起,法皇必然成功的希望開始消失了。”[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3卷,第96頁。恩格斯通過對政治和軍事形勢的全面考察,精辟概括出普法戰(zhàn)爭初期戰(zhàn)爭進程的階段性特點,極富預(yù)見性地指出不同階段戰(zhàn)爭進程和可能發(fā)展。
恩格斯還善于從政治可能對作戰(zhàn)行動施加的種種影響,大膽推測戰(zhàn)局的發(fā)展。在他看來,戰(zhàn)爭有其自身特殊的規(guī)律要遵循,如一系列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原則。但在普法戰(zhàn)爭中,法軍卻常常違背這些原則,導(dǎo)致作戰(zhàn)行動一敗再敗。恩格斯將這一現(xiàn)象歸因于無理的“政治上的必要”[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3卷,第115頁。。普法戰(zhàn)爭進行到1870年8月上旬,法軍由進攻轉(zhuǎn)入防御。此時直接配置在邊境上的法軍如同一字長蛇。恩格斯指出,依據(jù)防御部署的基本常識,法軍或可把軍隊主力后撤一日行程,使軍隊集中、同時處于能夠靈活機動支援的距離范圍內(nèi)。但是法軍的部署絲毫未有改變,直接導(dǎo)致首戰(zhàn)的慘敗。恩格斯洞見癥結(jié)地指出,這根本是由于“不允許在第一次的會戰(zhàn)以前就退卻”[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144頁。這一政治需要。恩格斯還大膽預(yù)言,正是出于“軍事行動一直服從政治上的考慮”[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259頁。,麥克馬洪軍團必將遭受覆滅的命運。戰(zhàn)局的發(fā)展再如恩格斯所料,因為擔心繼續(xù)退卻會引發(fā)國內(nèi)革命,巴黎政府拒絕麥克馬洪元帥的合理軍事請求,即退向巴黎固守防御、誘敵深入待機破敵。而巴黎政府卻一再強令該兵團去援救遠離法國中心的巴贊兵團,終致麥克馬洪兵團的被殲和法蘭西第二帝國的覆亡。
二、預(yù)測戰(zhàn)爭離不開對地理環(huán)境特征的透徹分析
戰(zhàn)爭指導(dǎo)者對于戰(zhàn)爭的駕馭能力,還突出表現(xiàn)在對地理環(huán)境特征的全面考量和整體把握上。恩格斯在思考和分析戰(zhàn)爭現(xiàn)象時,正是以此為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通過透徹分析交戰(zhàn)國家的地緣環(huán)境特點,以及可能爆發(fā)沖突的戰(zhàn)場地形條件,從更全維度、更深層次上揭示出戰(zhàn)爭的實質(zhì)和運動軌跡,從而科學預(yù)見其發(fā)展。
(一)地緣環(huán)境特點對國家主要戰(zhàn)略方向具有重要影響。恩格斯十分重視研究地緣環(huán)境特點對國家地緣安全戰(zhàn)略的影響,從這一角度深刻解讀了法國數(shù)百年征戰(zhàn)史中所奉行的地緣安全戰(zhàn)略——致力于構(gòu)建首都巴黎東北邊境方向的可靠的地緣安全屏障,根本是由法國天然的地緣環(huán)境特點所決定的。他指出,巴黎,這一“法國的中心距東北邊境太近”[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210—211頁。,且“這條國界又完全沒有河流或山脈可以作為防線”[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269頁。,這就促使法國:第一,去征服國界附近的地區(qū);第二,建立從萊茵河到北海的三層要塞帶;第三,總是力圖占有萊茵河的整個左岸地區(qū)。恩格斯還作出一個形象比喻,即以巴黎為中心畫弧,國界自然形成了一條以巴黎為圓心的、半徑為250英里的弧線。但是國界在法國東北邊境離開了這條弧線而形成了一根弦,這根弦上有一點距巴黎僅120英里。如果把上述弧線從此向北延伸就會發(fā)現(xiàn),它幾乎全部沿著萊茵河到達海邊。恩格斯指出,這就是法國要求取得整個萊茵河左岸地區(qū)的真正原因。因為只有在取得這個邊界以后,巴黎才能在它的最暴露的一面也得到與它的距離都是相等的邊境的掩護,而且有一條河流作為國界。恩格斯進而指出,這種對于“自然疆界”的訴求并非歐洲政治安全的一般指導(dǎo)原則,對普魯士,“同類性質(zhì)的軍事理由也不能使它有更多的權(quán)利要求取得法國的領(lǐng)土”[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211頁。。但事實上,法普兩國毫無疑問地都自認為有權(quán)要求這一點,這將必然導(dǎo)致二者在這一戰(zhàn)略方向發(fā)生軍事對撞。
整個普法戰(zhàn)爭中,交戰(zhàn)雙方正是緊緊圍繞于此展開軍事較量。普軍在法國東北邊境擊敗法軍主力后,巴黎成為其擊敗拿破侖三世法國的直接軍事目標。因為,法國的整個行政管理系統(tǒng)過于集中,這種集權(quán)化的趨勢在拿破侖三世統(tǒng)治時期又被加強了。與此相應(yīng),巴黎作為行政中心的地位進一步被強化。恩格斯進而指出:“如果巴黎陷于癱瘓狀態(tài),如果同巴黎的交通線被切斷,那末各地便沒有任何核心,并同樣地陷入癱瘓狀態(tài)。”[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210頁。戰(zhàn)事發(fā)展再一次被恩格斯所言中,普魯士后來的軍事行動皆以巴黎為基本指向,具體是消滅可以援救巴黎的一切野戰(zhàn)軍團,同時挫敗巴黎城內(nèi)的一切突圍行動,牢固圍困巴黎并逼迫其投降。這一點也為歷史所證明,普魯士參謀本部對法國的戰(zhàn)爭計劃首次擬定于1867年,此后又不斷加以改正,然而始終如一的是,“它的性質(zhì)是具有高度攻勢性,其觀念極為簡單。一般方向為巴黎;目標為擊碎在任何地處所遭遇到的敵人。”[注]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第3卷,鈕先鐘譯,北京:戰(zhàn)士出版社,1981年,第110頁。
(二)地形地貌條件決定軍隊主要作戰(zhàn)方向。地形地貌是戰(zhàn)爭賴以發(fā)生和進行的重要物質(zhì)條件之一,恩格斯非常善于把對地形地貌的分析融入對戰(zhàn)爭指導(dǎo)方針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原則的分析之中。特別是在普法戰(zhàn)爭中,對兩軍可能的主要作戰(zhàn)方向甚至是首次進行大規(guī)模會戰(zhàn)的地點,恩格斯據(jù)此早在雙方首次交鋒的前幾天,就作出了科學的預(yù)見。1870年7月29日,法軍向普法兩國邊境線開拔。恩格斯指出,法軍究竟要“向哪一個方向運動呢?一看地圖就可以得到答案”[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99頁。。在萊茵河左岸,有兩條縱貫?zāi)媳薄⒈舜伺B的山脈——佛日山脈和霍赫瓦爾特山脈。它們都有一些很好的大道貫穿其間,但是其中沒有一個地區(qū)是便于20萬—30萬大軍行動的。不過,在佛日山脈和霍赫瓦爾特山脈之間卻有一條寬達25英里—30英里的寬闊的通道,這里是極便于大軍運動的地區(qū)。此外,從麥茨到美因茲的道路也經(jīng)過這里,因此,“這里就有了一個自然界規(guī)定好的作戰(zhàn)方向”[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99頁。,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沖突一定發(fā)生這個通道內(nèi)的某地,或者在通道以外的美因茲城下。
恩格斯還指出,法軍集中的情況也很好地印證了他的判斷。通過分析法軍第一線、第二線以及預(yù)備隊的配置地域,以及近期的軍隊調(diào)動情況,他指出,法軍的全部兵力都已集中在那兩支山脈之間的通道前面。由此得出的結(jié)論是:法軍企圖進入這個通道,真正的會戰(zhàn)可能發(fā)生在剛才談到的那個地區(qū)。恩格斯的這一預(yù)見也像他對普法戰(zhàn)爭可能的進程的其他許多預(yù)測一樣,在后來的戰(zhàn)事發(fā)展中被完全證實了。他所指的這一地區(qū)在8月初連續(xù)發(fā)生了維爾特會戰(zhàn)、維桑堡會戰(zhàn)、福爾巴赫會戰(zhàn),成為普法戰(zhàn)爭爆發(fā)初期幾次大規(guī)模會戰(zhàn)的主戰(zhàn)場。
三、預(yù)測戰(zhàn)爭需要對國家軍事制度異同進行全面比較
一個國家的軍事能力同本國采用的軍事制度緊密相關(guān),這種與軍事制度息息相關(guān)的軍事能力也通常是國家制定戰(zhàn)爭策略的邏輯起點。恩格斯在認識和分析戰(zhàn)爭現(xiàn)象時,從戰(zhàn)爭自身所包含的內(nèi)部要素——軍事制度情況,全面考察戰(zhàn)爭的運動、發(fā)展和變化,進而基于這種變化準確預(yù)測了交戰(zhàn)雙方的軍事能力、戰(zhàn)爭策略的相應(yīng)嬗變。
(一)發(fā)展變化地看待兵役制度對國家軍事能力和戰(zhàn)爭策略的必然影響。“多兵之旅必勝”是一條不容忽視的戰(zhàn)爭法則。如何在平時和戰(zhàn)時保持一支數(shù)量和質(zhì)量上占據(jù)優(yōu)勢的軍隊,一直是19世紀歐洲主要軍事強國設(shè)計自身軍事制度的重要出發(fā)點。因為歷史傳統(tǒng)和戰(zhàn)略考量的差異,法國和普魯士采取著完全不同的兵役制度。法國采取的是基干兵制度,而普魯士則采取后備軍制度。恩格斯全面比較兩種制度的特點,指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決定著雙方迥異的軍事能力。法國的基干兵制度專注于培養(yǎng)和保持一支數(shù)量龐大的現(xiàn)役軍隊,它的平時編制與戰(zhàn)時編制差別不大。普魯士的后備軍制度則與之完全不同,普軍平時編制的人數(shù)還不到戰(zhàn)時編制人數(shù)的三分之一,但主要著眼為轉(zhuǎn)入戰(zhàn)時編制作好一切周密的準備。這種兵役制度以較高的征兵率、較短的服役期,保證培養(yǎng)出一大批受訓(xùn)良好的后備兵力。且普魯士有著一套極為完善的戰(zhàn)爭動員體制。因此,戰(zhàn)爭持續(xù)時間越長,戰(zhàn)爭動員越充分,兵力優(yōu)勢就愈發(fā)凸顯,戰(zhàn)場主動權(quán)就愈可能傾向于普軍。
在恩格斯看來,兩種迥異的兵役制度決定了兩國不同的戰(zhàn)爭策略及戰(zhàn)爭局勢的可能走向。普法戰(zhàn)爭爆發(fā)伊始,恩格斯就指出,“法國的基干兵制度使它能夠比普魯士的后備軍制度遠為迅速地集中一支譬如12~15萬人的軍隊。”[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95頁。因而,利用先期兵力優(yōu)勢發(fā)動突然襲擊,擊敗尚未充分完成戰(zhàn)爭動員的普軍,成為法國必然采取的戰(zhàn)爭策略。但同時也指出,“法國的受過訓(xùn)練的兵士不超過55萬人,而這樣的兵士單是北德意志就有95萬人。德國的優(yōu)勢正在于此,而決戰(zhàn)越向后推遲,這個優(yōu)勢就越明顯。”[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98頁。所以,隨著動員進行和兵力占優(yōu),“如果德軍在最近的將來不遭受攻擊,那么他們自己將轉(zhuǎn)入進攻。”[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98頁。法皇的戰(zhàn)爭策略在其被俘后的自白中得到證實,即“路易·拿破侖告訴我們,他深知德軍在兵力上的巨大優(yōu)勢,他曾經(jīng)希望用下面這個方法來抵消這個優(yōu)勢,那就是迅速攻入南德意志”[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253頁。。普魯士軍隊也正如恩格斯所料,通過迅即完成動員和集結(jié),很快扭轉(zhuǎn)了兵力對比并主動對法軍發(fā)起攻勢,完全奪回了戰(zhàn)場主動權(quán)。
(二)全面辯證地看待指揮體制對軍隊指揮能力和作戰(zhàn)行動的制約作用。軍隊的指揮體制是戰(zhàn)時軍隊行動的神經(jīng)中樞,直接決定軍隊的指揮效率甚至戰(zhàn)爭的勝負。恩格斯在分析法軍在普法戰(zhàn)爭中遭對手徹底打垮的原因時,指出其中一條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國的整個行政管理系統(tǒng),特別是軍事指揮管理系統(tǒng)過于集中。”[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209頁。當時,法國為了軍事目的把全國劃分為23個軍區(qū),每個軍區(qū)都駐有一個步兵師。然而,各師的師長和陸軍部之間沒有中間環(huán)節(jié)。師司令部更加突出行政管理職能,軍事指揮職能則被大大弱化。在拿破侖三世統(tǒng)治時期,這23個師曾合編為6個軍,每個軍由一個法國元帥指揮。但是這些軍和原來的師一樣,也沒有真正的司令部。在恩格斯看來,這些師、軍是單純的行政組織而不是作戰(zhàn)組織,“它們是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為了軍事目的編成的”[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210頁。。一句話,“法國軍隊的行政管理機關(guān)(如軍需部門等)不是接受指揮官(元帥或?qū)④?的命令,而是直接接受巴黎的命令。”[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210頁。恩格斯進而指出,如果巴黎被圍陷于癱瘓亦或投降,那么各地便沒有任何組織核心。事實確實如此,直至普法戰(zhàn)爭結(jié)束之際,普軍實際上僅控制著巴黎周邊和一條通往巴黎的狹長補給走廊,這些占領(lǐng)區(qū)尚且不足法國全部領(lǐng)土的八分之一,但是,分布在各地的法國駐軍群龍無首、各自為戰(zhàn)、相繼被殲。
恩格斯又分析到,與此完全相反,普魯士的每個軍都有固定的戰(zhàn)時編制,有定額的步兵、騎兵、炮兵和工兵,并且設(shè)有保持作戰(zhàn)準備的軍事指揮、衛(wèi)生、軍法和行政等部門。更為關(guān)鍵的是,盡管普魯士軍隊的總指揮是普魯士國王,但“在他周圍的首先將是以毛奇——一位優(yōu)秀的將軍——為首的總參謀部”[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58頁。。在恩格斯看來,毛奇為首的總參謀部之所以優(yōu)秀,根本在于其實行的一種全新指揮模式。毛奇提出了一種全新的“少下命令,多下達指示”的“任務(wù)式指揮法”。[注]參見戴耀先:《論德國軍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第151—152頁。立足于此,普軍總參謀部于1867年進行了徹底改組,努力將其“改造成一種獨特的工具,既保證下級單位層次上的靈活性和主動性,又保證對于共同的作戰(zhàn)信條和統(tǒng)帥部戰(zhàn)略意圖的遵循。”[注]帕雷特主編:《現(xiàn)代戰(zhàn)略的締造者:從馬基雅維利到核時代》,時殷弘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第287頁。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普法戰(zhàn)爭中,同樣在突然的遭遇戰(zhàn)中,普魯士軍隊能夠鎮(zhèn)定自若、靈活應(yīng)變,而法國軍隊卻常常陷入驚慌失措、被動挨打的不利境地。
四、預(yù)測戰(zhàn)爭要時刻緊盯攻防技術(shù)的最新發(fā)展
攻防武器之間的競賽,一直促進著軍事科技的發(fā)展,并導(dǎo)致作戰(zhàn)方法的變革。在恩格斯看來,每一次戰(zhàn)爭的內(nèi)容和進程,都可以看做是最新攻防技術(shù)的較量、與之相應(yīng)最新作戰(zhàn)方法的對抗。他非常善于從攻防技術(shù)的發(fā)展及其最新特點出發(fā),深刻分析由此引發(fā)的戰(zhàn)術(shù)演變,進而對戰(zhàn)爭可能采用的作戰(zhàn)方法和具體進程作出精準預(yù)測。
(一)基于攻防手段的最新變化準確推斷交戰(zhàn)雙方采用的作戰(zhàn)方法。在恩格斯所處的時代,要塞保衛(wèi)戰(zhàn)在戰(zhàn)爭中占有極其重要地位。一次戰(zhàn)爭的成敗可能就取決于交戰(zhàn)雙方對某幾個要塞甚至對某一個要塞的奪取和防守。在普法戰(zhàn)爭中,隨著法軍野戰(zhàn)主力兵團相繼覆滅,對于斯特拉斯堡、土爾、巴黎等法國要塞城市的圍攻日漸成為戰(zhàn)局的重心。恩格斯非常重視對這些要塞攻防戰(zhàn)、特別是對巴黎保衛(wèi)戰(zhàn)的研究,通過認真分析攻防技術(shù)手段的演進給予要塞攻防戰(zhàn)帶來的重大變化,準確預(yù)測出法軍可能采用的要塞防御戰(zhàn)法,以及與之相對應(yīng)的普軍采取的要塞攻擊戰(zhàn)法。
普法戰(zhàn)爭爆發(fā)前,獨立堡壘體系已經(jīng)取代舊式要塞,通過在大要塞周圍修建大量獨立堡壘,有效實現(xiàn)了相互之間的火力和兵力支援。這種要塞的最大優(yōu)勢在于,徹底改變了舊式要塞的一線構(gòu)筑方法和被動防御戰(zhàn)法,特別是保證了積極的野戰(zhàn)與正規(guī)的要塞戰(zhàn)相結(jié)合,從而大大地加強了要塞的防御。正因為熟知這一點,恩格斯指出法軍要想挫敗普軍對巴黎的圍攻,就必須以相當力量的野戰(zhàn)兵團,在獨立堡壘體系周圍展開機動作戰(zhàn),強力突破包圍線或阻止敵人完成包圍的嘗試。因為,“最后的勝負總是由野戰(zhàn)部隊來決定的,而要塞的作用并不是取決于它們天然的或人工的賦予的威力,即它們本身固有的價值,而是取決于它們所能給予野戰(zhàn)部隊以掩護和支援的程度。”[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602頁。但是,隨著法軍兩大野戰(zhàn)軍團相繼覆滅,巴黎保衛(wèi)戰(zhàn)恰恰失去了可以依托的核心力量。僅僅能夠依靠固有的堡壘體系、以新兵為主的巴黎守備部隊,以及“分散在城外的同樣一些新兵的微弱支援”[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237—238頁。。在巴黎被圍的幾個月中,城內(nèi)的法軍依托堡壘體系先后多次出擊,其中不乏一些大規(guī)模的出擊和某一方向的全面進攻,試圖以積極的軍事行動打破對巴黎的圍困,然而,卻始終因為缺乏一支強有力的野戰(zhàn)部隊做配合,實際取得的作戰(zhàn)效果乏善可陳,最終不得不陷于絕望、投降。
(二)熟悉技戰(zhàn)術(shù)變化的顯著特點成功預(yù)測戰(zhàn)爭可能的發(fā)展進程。恩格斯通過分析指出,隨著筑城技術(shù)特別是火炮技術(shù)的進步,對于要塞的攻擊方法也發(fā)生了重大改進。他指出,“自從使用線膛炮以來,甚至野炮的炮彈也幾乎完全是榴彈,所以現(xiàn)在可以比較容易地用任何一個軍的普通野炮去轟擊要塞和燒毀它的建筑物,而不必像從前那樣等待臼炮和重型攻城榴彈炮的到來。”[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181頁。他還特別關(guān)注到,作為線膛野炮的補充,普魯士軍隊還裝備有一種大口徑的新式線膛臼炮。這些臼炮能夠發(fā)射觸發(fā)引信炮彈,大大提高了對堡壘防彈掩蔽部的火炮和倉庫的毀傷率。因此,在分析普法戰(zhàn)爭中發(fā)生在斯特拉斯堡的第一次要塞圍攻戰(zhàn)時,恩格斯特別提醒到,“這是第一個使用現(xiàn)代線膛炮發(fā)射裝有著發(fā)信管的炮彈來對付石質(zhì)工事的圍攻戰(zhàn)例。……斯特拉斯堡將清楚地向我們說明,現(xiàn)代重型線膛炮在圍攻戰(zhàn)中應(yīng)當如何行動,因此這個圍攻在這方面值得我們特別重視。”[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182—183頁。
1870年8月中旬,普軍的軍事行動在斯塔拉斯堡、土爾等法國要塞城市遭到了頓挫。新聞輿論界普遍認為,這些地方之所以久功不克,是因為普軍不善于圍攻,或者只是為了進行軍事試驗。恩格斯對此嗤之以鼻,他詳盡解析了要塞攻防戰(zhàn)的方法步驟,提醒那些不懂軍事的人們“究竟什么是圍攻”[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190頁。。他指出,對斯特拉斯堡的第一次野炮轟擊并非正規(guī)圍攻的開始。圍攻要塞的準備階段可能持續(xù)很長時間,在這一階段,首先是包圍要塞,驅(qū)逐其警戒部隊和其他部隊,偵查要塞的工事,運來攻城炮、彈藥和其他儲備品,并建立倉庫,“在這次戰(zhàn)爭中,第一次野炮轟擊也是在這個準備階段”[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191頁。。在這之后,“挖掘第一道平行壕被認為是正規(guī)圍攻的開始。”[注]《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5卷,第191頁。因此,斯特拉斯堡從8月23日到28日受到了炮擊,但正規(guī)圍攻直到挖掘第一道平行壕,即29日才開始。恩格斯進一步指出,由挖掘第一道平行壕算起,“到第十七天,可能擊毀棱堡的側(cè)面以及配置在上面的火炮;那時才可能打開缺口”,因而從純軍事觀點來看,被圍者至少能夠堅守這樣一段時間,即17天。但這僅是“對于圍攻一種最薄弱、最簡單的要塞(沃邦式六角堡)的過程做一概述”,因為在斯特拉斯堡被攻擊的正面上又有外圍工事,因而它至少能比平均期限多支持5天,也就是22天。后來真如恩格斯所預(yù)測,斯特拉斯堡從受正規(guī)圍攻開始至9月19日被迫和談并最終陷落,與恩格斯的預(yù)測相差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