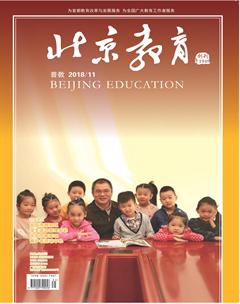教學學術:教師專業發展的核心命脈
楊躍
[摘要]“教與學的學術研究”已是當前我國教育發達地區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使命。正確認識教師職業的“學術性”與“師范性”,將有助于促進廣大中小學教師自覺地追求“教學學術”,并通過“臨床研究”提升反思水平,推動專業發展。
[關鍵詞] 教學學術;教師專業發展;教學專業;教師教育
2018年初春伊始,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教育部等五部委先后印發《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和《教師教育振興行動計劃(2018-2022年)》,教師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和重視。“教師職業應該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認識越來越成為全社會的普遍共識,可持續性專業發展亦成為廣大中小學教師的自覺追求。然而,“教學專業(teaching as a profession)”的特性和“學會教學(learn to teach)”的不易使得教師專業發展成為一件并不輕松的事情,“教與學的學術(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將成為我國教育發達地區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新使命。
“教學專業”的特性
“專業”是社會分工、職業分化的結果,在眾多職業中具有特殊性,主要指一群人經過特殊智力培養和訓練、具有較高深和獨特的專門知識與能力,并按照一定標準進行專門化的活動,從而為社會提供專門性的服務,促進社會進步,并獲得相應報酬、待遇和社會地位的專門職業。早在1948年,美國全國教育協會就指出,“專業”應符合八條評判標準:專業實踐屬于高度的心智活動、具有特殊的知識領域、受過專門的職業訓練、經常不斷地在職進修、視工作為終身從事的事業、行業內部自主制定規范標準、以服務社會為最高目的、設有健全的專業組織[1]。我國學者劉捷也提出,一個成熟的“專業”應該具備六個標準:運用專門的知識與技能、服務的理念和職業倫理、長期的培養與訓練、不斷地學習進修、享有有效的專業自治、形成堅強的專業團體[2]。可見,成為“專業(專業性職業)”至少需要具備兩大基本條件:一是具有包含深奧知識和復雜技能的科學知識體系,而要掌握這些科學知識,不僅需要經過專門的教育和訓練,更需要持續終身、不斷地學習和進修;二是為公眾和社會提供至關重要且卓有成效的高質量服務。
教師職業專業化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更是提高教育質量的基本保障;在“教師專業化”的背景下,教師專業發展的使命便是努力提升開展高質量教育、教學工作所要求的專業品質。教師的專業品質,即“教師專業性”(teachers professionality),是教師在具體教育、教學實踐工作中所表現出來的觀念、態度、知識、行為、情意等方面的典型特征,與“教學專業”的特性密不可分。不同于醫生、律師等專業性職業,教師所從事的教育教學專業具有鮮明的獨特性,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教學專業要求理性智識基礎和論辯能力。“專業總是一種高度復雜和技藝嫻熟的實踐形式”,但是,“決定專業的因素不僅僅是技能的復雜性”,更是由于該專業“在學術上具有廣泛的知識解釋基礎”[3]。專業人員和從事慣例性、操作性、因循性工作的技術人員雖然同樣需要具備并且靈活運用嫻熟的技術、技巧解決問題的能力,但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專業人員必須通過反省性思考對自己的專業行動后果作出判斷,因此,專業實踐是高度的心智活動。教師面對復雜教育情境時必須具有較強的教育敏感性,能夠作出審慎的決斷,并且對自己所作所為的價值、意義等作出原理性的解釋,這就要求教師接受理論性思考與反省性論辯的專門培育。
第二,教學專業超越工具理性主義普適性規范。“在課堂上試圖向一群困惑的學生解釋復雜的數學問題的教師”“必須基于當前的信息以及對將來不完美的預測做出判斷,然后行動”[4],而用以指導作出不同行為抉擇的策略性知識更多地是教師個人的實踐智慧(又稱實踐性知識),無法從工具理性出發尋找到普適性的技術規范并在教師教育中進行傳授和演練,“教師只能通過與特定的教育對象、教育情節和教育場景的互動來創生特定的教育效果”[5]。
第三,教學專業本質上是作為道德實踐的志業。“專業人員必須有價值觀、道德高尚和社會責任感”,專業實踐本質上是道德實踐(moral practice);教學專業因具有更嚴格的道德性而被視為“志業(vocation)”,要求“將認知、踐行和人生相整合”。“專業的教育者并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教某個人,其教學是為了讓學生明了認識是為了行動——改變他人的心智和生活,負責任地以及正直地為他人服務”,因此,專業的教師開展的是“人格的教育”[6]。
教師專業因工作對象特殊(具有主體性的、成長中的兒童青少年)、工作性質特殊(如工作標準的非同一性,工作效能的不確定性、內隱性、滯后性等)而殊異于醫師、律師等其他專業,“我們極大地低估了培養他人為教學做準備的復雜性”[7]。
“學會教學”的困難
教學專業的特殊性導致“學會教學相當不易,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學習內容上需要將多種類型知識相融合。美國著名教師教育學者李·舒爾曼開創的“教師知識”研究指出,教師必須掌握課目內容知識(subject matter/content knowledge)和關于學習者及其特征的知識(knowledge of learner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關于教育境脈的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contexts)、關于教育目的價值等的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ends, purposes and values, etc)、一般教學法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及課程知識(curriculum knowledge)等多種類型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教師應該具備的專業知識在根本上并不是這些知識的簡單相加,它們有機融合之后所生成的“課目教育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簡稱‘PCK)”才是教師專業知識的核心。“PCK”作為課目內容知識和教育(pedagogy)知識的特殊“結晶”,其中最關鍵的成分是教師如何認識特定學生對特定課目內容的學習困難或誤解,以及將采取怎樣的教學策略來幫助學生克服或轉化學習困難或誤解[8]。教師專業性集中體現在,能夠對如何向特定學生組織表達和調整所教具體課目的內容,適應學習者的不同興趣和能力形成自己的獨特理解,并實際開展有效教學活動。
第二,學習方式上要求具身化、個性化的深度學習。由于“學-教”無法從工具理性出發尋找到普適性的技術規范并依循這些技術規范進行演練,只有基于理解、注重反思的深度學習才是有效的學習方式。這需要學習者在有關教育、教學的概念、原理之間及其與自身已有的認知結構之間建立起豐富的聯系,能夠在新的特定情境下運用習得的教學原理去解決新的真實問題。
第三,學習過程中要求持續終身的德性與智性修煉。與從事例行性操作的工作人員不同,教師所從事的教育、教學工作要求教師能夠在復雜的、不確定的教育教學情境中作出道德的判斷,并實踐這種德行,以使學生獲得健康成長與可持續發展。教學專業被賦予更嚴格的道德要求,而這種道德實踐的能力和自我崇高品格的養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是通過修讀一兩門課程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品德學習的復雜和漫長也使得“學會教學”這項專業學習活動變得不易。
在“教與學的學術研究”中“學會教學”
教師在終身可持續專業發展過程中,始終致力于“學會教學”;而“教學專業”的特性,尤其是“教學”作為一項學術事業的獨特性,都表明教師正是在“教學學術”的研究中“學會教學”的。
1.正確認識教師職業的“學術性”與“師范性”
學界在談及教師職業及教師教育的特性時,總是將“學術性”與“師范性”視為兩個彼此對立的不同品性(如長期以來在教師教育中始終存在的“學術性與師范性之爭”);同時,又總是將“學術性”理解為“教師應該掌握‘教什么,即任教學科領域的科學知識”,將“師范性”理解為“教師應該掌握‘怎么教,即教育知識與教學技能”。從“教學專業”的特殊性質和“學會教學”的關鍵要求來看,這種對舉式的概念表述不準確。
首先,正確認識教師職業的學術性。
美國卡內基促進教學基金會前主席歐內斯特·L·博耶(Ernest L. Boyer)區分了“發現的學術(scholarship of discovery)”“整合的學術(scholarship of integration)”“應用的學術(scholarship of application)”和“教學的學術(scholarship of teaching)”四類學術活動,強調給予傳授知識的“教學的學術”以尊嚴和地位,將“教學”從一項個人化的經驗性工作提升為一種學者共同體內部需要共享、交流和探究的學術性活動,增進了人們對教學工作的學術價值的認識,也促使我們思考教師職業的學術性意涵。“教學作為一門學術性的事業,只有當教師沉浸在自己專業領域的知識之中,廣泛涉獵并在智力上不斷深化,教學才能得到好評。”[9]教學像其他形式的學術一樣,既是一個探索的過程,也是一種成果。教學學術具有所有學術共有的特點,即李·舒爾曼所認為的:“當教師將工作公開、接受同行評價和批評,并與所在社團的其他成員進行交流時,教學就變成了教學學術”。教學學術是教師指向對教和學的研究并生產研究性和創造性的可見成果。在教學學術領域,中小學教師與大學教授一樣,同樣可以有所建樹。
參照美國學者李·舒爾曼等人建構的“教師知識結構”,中小學教師要勝任專業化、高水平的教學工作所必須具備的核心專業品質就是教師應該能夠將所擁有的學科知識轉換成具有教學意義的形式,從而適應不同學生的不同能力和背景。這種獨特的能力即為“PCK”所指稱的教師實踐性知識,具體包括教授具體課目主題的能力與方法,以及讓學生掌握相關概念與過程的能力與方法。“從教學促進他人學習的意義上說,教學意味著以一種最有利于學生學習的方式掌握學科知識。教師既要掌握學科知識,還要理解所教知識的目的,但僅此還不夠,教師必須能夠將自己所理解的學科知識轉換成與學生的多種能力、興趣、背景等相關聯的知識形態。教師必須根據自己對學科知識的理解探求一種走進學習者心靈、激發學習者動機的方式。”[10]教師從事教學工作的學術品性的集中體現,以及教師必須開展的“教學學術”的重大任務,就是自覺地探索和分享這些實踐智慧。
其次,準確理解教師職業的“師范性”。
教師不僅需要掌握所任教課目的內容(所謂“具有學科專業領域的學術性知識”),而且需要懂得怎么教(即掌握教育專業領域的知識、技能),這已經近乎常識。但是,正由于對“學術”的理解錯誤和對“教學學術”的嚴重忽視,前者被稱為“學術性”,后者被視為“師范性”,二者之間的關系被曲解為“非此即彼”的相互對立關系,似乎“師范性”并不具有“學術性”。事實上,傳統所說的“師范性”本身蘊含著極豐富的學術意涵,至少“教學學術”的提出彰顯出“教學”是一項學術性事業的價值與地位。教學學術具有更強的自我反身性,即教師更多地是對自己的教學實踐活動本身進行反思與研究,以生成教學成果;更強調教學實踐改進過程中的理論生成,即理論與實踐之間高度的彼此互動;是一種跨學科研究,要求教師具備多學科知識、能力,并在此基礎上產生對真實教學的深刻洞見。
教學專業的特性要求教師職業的“師范性”必須蘊含教師職業所特有的“學術性”(即“教和學的學術研究”),教師在“學會教學”的專業發展進程中,絕不能停留在知識習得和技能訓練的表層學習上,而應該為“學會教學”開展深度學習。有研究者形象地將廣大中小學教師在學習了專業知識、訓練了專業技能、形成了專業態度之后卻不能有效提高專業發展水平的情形,比喻為“如同開了中藥鋪子,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專業態度都被分散放在藥柜上不同的小匣子里,由于缺少教學研究論文的訓練而不能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許多教師靠加倍的努力來改善這一狀況,結果卻是在藥柜上開了更多的匣子”[11]。
“教”是為了“成就學生的學習”,教師為“教會學生學習”而自我努力“學習如何教”;教師自主建構自己的教學知識,有意識地開展“教與學的學術研究”(即教科研活動),反思、凝煉“PCK”,便是教師“學會教學”和獲得專業發展的最有效的學習策略。
2.激勵教師自覺地追求“教學學術”
廣大中小學教師針對長期被遮蔽的“教學學術”,深入、持久地開展“教和學的學術研究”,探尋獨特而有效的、向特定學生教授特定內容的有效教學方法,自主建構自己的教學知識(特別是提升“PCK”水平),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專業發展成就。研究表明,諸如“PCK”一類的教師知識是緘默的、零散的,很多優秀教師都難以用明確的語言來梳理和表述自己的“PCK”知識,也沒有機會、時間、意愿、動力等將這些緘默的專業經歷轉變為清晰、系統的知識,進而在教學專業界傳播、共享。因此,為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教師教育界應積極營造尊重“教學學術”、崇尚教學創新、倡揚“以教研為志業”的良好氛圍,激勵從事教師教育的大學教師或教研機構工作者與廣大中小學、幼兒園教師開展長期的實質性合作研究,分享、體驗和挖掘教師緘默而內隱的“PCK”知識,并使其顯性化、系統化,激勵廣大教師熱愛并自覺獻身于“教學學術”。
3.通過“臨床研究”提升反思水平
教師專業發展中應倡導中小學教師與大學教師、師范生(職前教師)等相互合作,共同開展“實踐者研究(practitioner research)”。比如,大學教師教育者可以邀請師范生和新任教師一起,系統地參與相關課程與課堂教學改革的探究活動,新任教師既以“學習者”的身份,又以“師范生的教師”(即教師教育者)的身份,從共同探究中學習如何確定研究問題、設計研究路徑、收集與分析數據、對研究結論進行反思等。師生在合作開展課程學習的行動研究、自我研究等各種“實踐者研究”的過程中,既能夠“收集和組織成百上千的臨床案例”,又能夠體會“反身學習”對于“學教”的不可或缺性、加深對“教學”是一種“反思性實踐”的認識,從而尋找到“PCK”與“教和學的學術研究”的結合點[12]。
總之,通過與專業伙伴分享加深對“教與學”的理解,提煉和提升教學專業最核心的“PCK”,是教師專業發展最獨特的表現;自覺地追求“教學學術”則是教師專業發展的核心命脈。當然,要提高教師學習的專業性、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既需要廣大教師學會采取有效的學習策略,又需要教科研部門積極開展活動,提供有力的支持保障,幫助廣大教師“學會教學”、獲得可持續性專業發展。
參考文獻:
[1]Division of Field Servic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48). The Yardstick of a Profession. Washington DC: NEA. p.8.
[2]劉捷.專業化:挑戰21世紀的教師[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62-64.
[3][8][美]舒爾曼.實踐智慧:論教學、學習與學會教學[M].王艷玲,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380-382,242-244.
[4][6][7][12][美]李·舒爾曼.標志性的專業教學法:給教師教育的建議[J].黃小瑞,崔允漷譯.全球教育展望,2014(1):3-13.
[5]耿文俠,等.教師職業的專業特性分析[J].教育研究,2007(2):83-88.
[9]歐內斯特·L·博耶.關于美國教育改革的演講:1979-1995[M].涂艷國,等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75.
[10]Stenve Herne,等.學會教學:教師專業發展導引[M].豐繼平,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61.
[11]邢紅軍.教學研究論文:中學教師專業發展水平的科學標度[J].教育視界,2015(7/8):7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