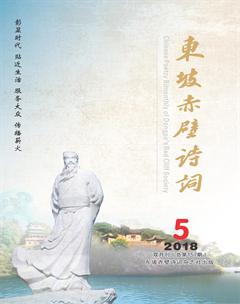詩路是條朝圣的路
劉慶霖
有人說,藏族的男人大多數都是用前半生勞動掙錢以養家糊口,而用后半生去朝圣——朝拜圣山、圣水、圣佛。而且,他們一旦走上朝圣的路,不管路途多遠,都會堅持到底。他們采取磕長頭的形式,三步一叩,無所畏懼,有的把家人都帶上一起朝圣,有的甚至就死在朝圣的路上。他們有信念、存善心、肯吃苦、能堅持,實在讓人欽佩。我曾經寫過《朝圣者》:“一念生時雜念沉,低頭磕向日黃昏。以身作尺量塵路,撞得心鐘唯自聞。”
詩非宗教,但有一點與宗教相似,就是詩路也像宗教的朝圣之路。詩人要在“朝圣”的路上,完成從靈魂深處到詩歌境界、表現藝術的不斷超越,方能使自己的詩進入“詩歌圣殿”。古今優秀的詩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經歷了以下三個方面的朝圣和超越。一是靈魂凈化之路。“詩歌圣殿”是詩人的終極目標。它是距太陽最近的地方,是人類精神的理想家園。正如美國詩人惠特曼所說:“看來好像奇怪,每一個民族的最高憑證,是它自己產生的詩歌。”要到達“詩歌圣殿”,詩人不但要用意志穿越時空,走一條艱難而漫長的路。而且還要以朝圣之心完成對自己靈魂的洗禮。真正經過朝圣洗禮的人,他們的手雖然依舊沾滿風塵,可他們的心靈卻是最干凈的。詩人要寫出真正的好詩,一定要有靈魂的參與,而我相信,靈魂的純度與高度,同詩人所能達到的高度是至關重要的。真正的好詩,是詩人靈魂的一部分。二是詩境臻妙之路。要進入“詩歌圣殿”,一定要有精神的高格和靈魂的高尚,并最終以詩歌的形式為人民群眾服務。但只做到這一點還遠遠不夠,詩歌必須首先在藝術上感染人,才能夠被他人所接受。“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為什么能夠感動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和熱愛詩歌的廣大讀者?就是因為詩境之臻妙。詩境臻妙之路,依然要詩人們以朝圣之心態去努力追求,去行走乃至自己去修筑、去開辟。三是語言錘煉之路。詩歌“朝圣”要攀登的還有一段至關重要的路,那就是語言錘煉之路。這段路,同樣充滿困難,須我們長行不殆、堅持不懈。要特別指出的是,錘煉語言,不是強迫語言符合我們的意愿,而是讓我們的意愿,適應詩歌的語言條件。這就像一位元帥調兵遣將,必須知道官兵本身的特長,做到知人善任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也正如海德格爾說的:“探索語言意味著:恰恰不是把語言,而是把我們帶到語言之本質的位置那里,也即,匯入大道之中。”此“大道”便是詩歌語言表達意境的自身規律。
(作者系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著名詩人、詩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