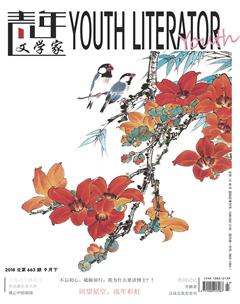《文心雕龍》當代闡釋
摘 要:《文心雕龍》在當今文學理論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并且對提升當下中國文學理論在全球文學理論中的話語權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文學應注重現實生活的反映,反對“淫侈”的文風;對《文心雕龍》體現的文理與文體進行概述。
關鍵詞:劉勰;《文心雕龍》;文體;文理;視域融合
作者簡介:蔣思墀(1985-),女,陜西南鄭人,陜西理工大學2016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7-0-02
一、《文心雕龍》文理與文體
在劉勰的生平考據中,大多學者參考范文瀾《文心雕龍》的考證推論。王元化先生在《劉勰身世與士庶區別問題》中引“劉勰一生跨宋、齊、梁三代,約當宋泰始初年(公元465年)生,至梁普通元年間(公元520或521年)卒,得年五十六七歲。”[1]30-31王運熙也援引范文瀾先生的考證在《文心雕龍譯注》中將其作為前沿;然而楊明照先生考證劉勰“一生歷宋、齊、梁三世,計得七十二三歲。”[3]前言李慶甲先生在其《劉勰卒年考》中提出劉勰“的生年當是公元465年左右,他的卒年是公元532年,總共活了六十七八歲。”[1]62
《文心雕龍》結構分說。《文心雕龍》全書一共五十篇三萬七千多字,當代學者結構劃分則有所差異。楊明照先生云“是書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論文之體,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言文之術,序志統攝全書”。[1]19與劉永濟先生在《文心雕龍校釋》中所理“下編統論文理,上編分論文體,學者先明其理論與上編所舉各體文印證,則全部了然矣”[2]序相通。劉綬松先生也認為“《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分為上下篇。上篇自《原道》起,訖《書記》止,共二十五。下篇自《神思》起,訖《序志》止,也是二十五。”[1]168而王運熙先生在《文心雕龍譯注》中將其細分為五部分“自《原道》至《辨騷》五編為第一部分;自《明詩》至《書記》二十篇為第二部分;自《神思》至《總術》十九篇為第三部分,泛論寫作方法;自《時序》至《程器》五編為第四部分,在全書中屬于雜論性質;末篇《序志》為自序”[3]前言謂之第五部分。并且在《<文心雕龍>的宗旨、結構和基本思想》中詳細闡釋了這一問題。
《文心雕龍》內容的闡釋。劉綬松先生在《<文心雕龍>初探》中論述“《梁書·劉勰傳》就說沈約讀了《文心雕龍》后,稱它‘深的文理,而且‘常陳諸幾案。”[1]167其一,穆可宏先生在《論<文心雕龍>與儒家思想的關系》中指出“《文心雕龍》闡明文學與自然景物的關系,也繼承《禮記·樂記》的思想,《明詩》中‘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物色》中‘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情以物遷,辭以情發。”[1]115都表現這種關系。劉綬松先生也論述“宋初山水詩的盛行,《文心雕龍·明詩》篇說:‘宋初文詠,體因有革。莊老告退,而水方滋。儷采百字之隅,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詞必窮而追新。《物色》篇說:‘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鉆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1]175周振甫先生在《<文心雕龍·原道>試論》中認為劉勰在《序志》里說“‘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就是要說明創作本與自然,以反對矯揉造作。”[1]304其二,《文心雕龍》表現文學創作與自然景物的關系,認識到文學創作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在《時序》篇中“時運交移,質文代變。”通過分析齊梁以前中國文學史上大量的事實,得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結論。其三,《養氣》與《風骨》篇論及曹丕、劉楨受孟子影響而以“氣”論建安諸作家,但有所不同,劉勰強調“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可見同樣也受孟子“知言”“養氣”說的影響。其四,劉勰繼承鄭玄、鄭眾對賦的看法,并且在《詮賦》中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比興》篇也詳論比、興,但是更多的是側重在比,進而對比、興解釋為“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其五,倡導清的文學導向,抨擊“離本彌甚,乃始論文”的惡劣文學傾向。《序志》篇講“而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秀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
劉勰《文心雕龍》的整體思想。王元化先生在論及劉勰的創作背景及其思想談到,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吐露了內心的不平和憤懣,反對了代表門閥標榜的浮華尚玄的文風,提出了文質并重的進步文學主張,但是從思想體系上來說,他始終沒有越出儒家那一套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思想原則和倫理觀念。他不滿于等級森嚴的門閥制度,卻不得不向最高統治集團進行妥協。他恪守儒家古文學派立場反對浮華文風,卻不得不與玄佛合流的統治思想沆瀣一氣。這些矛盾現象只有通過他的時代和身世才能得到最終的說明。劉勰關于文學藝術的整體思想,劉綬松先生提出“依照劉勰的看法,文學藝術的主要任務,就是藝術地再現現實(自然環境與社會生活);凡是能夠真實地具現人們在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活中的思想感情的,就是美好的文學作品。”[1]183王運熙先生在《<文心雕龍>的宗旨、結構和基本思想》一文中論述“《文心雕龍》是一部詳細研討寫作方法的書,它的宗旨是通過闡明寫作方法,端正文體,糾正當時的不良文風。《原道》至《變騷》五篇是總論,提出寫作方法的總原則和總要求,也是全書的基本思想。”[1]253馬宏山先生在《論<文獻雕龍>的綱》一文中認為“劉勰之所以要‘辨騷,就是他要闡明他所看到的文學上一個重要的文題,即文學的藝術性問題,他認為文學的藝術性在屈原作品中濃郁地表現著,但這種藝術性并不是由于屈原作品‘異乎經典者地‘夸誕所形成,而是由艷麗的辭藻所組成的。”[1]286馬宏山先生在《論<文心雕龍>的綱》一文中也論述“‘道與文之前的辯證關系。即‘道和文之間,一個是‘本體,一個是‘末用:‘道是文之‘本,文是‘道之‘末;‘道是文之‘體,文是‘道之‘用”。[1]258從這里可以更進一步清晰劉勰《文心雕龍》的整體思想。
劉綬松先生認為《文心雕龍》存在著一些缺點。“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指出了人類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活所給予文學的重大影響,即是人們之所以需要進行創作活動,乃是因為在自然界和社會生活里有了某種理解和感受的緣故。但是他還不能進一步地指出,人們之所以在自然界和社會里獲得某種理解和感受,乃是人們在自然界和社會里進行斗爭地實踐的結果。”[1]206另有研究者認為:“《文心雕龍》是這樣一部書:它充滿著矛盾。當作者按照原道、征圣、宗經構造自己的文藝思想體系時,他是唯心的;當他總結大量文藝創作的歷史經驗,提出創作理論命題并回答這些命題時,他在許多地方又是唯物主義的。常常在看來是唯心主義糟粕的地方,并存著唯物主義思想,并存著豐富、深刻的現實主義理論,就像恩格斯在評論黑格爾哲學時說的那樣:“由于‘體系的需要,他在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強制性的結構。”[1]329
綜上,劉勰的《文心雕龍》在中國文學藝術乃至整個世界文學史上都是非常顯耀式的里程碑。馬宏山先生在《論<文心雕龍>的綱》中論述“乾隆時期《四庫全書》的總編纂官紀昀,就曾在《文心雕龍·原道》篇眉批說:‘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眾流。”[1]260在先于當代學者之前就有對《文心雕龍》進行深入地評述,而且認識其中的文學藝術觀點,并進行闡釋,進而在當下,就更有義務對我國古代文學藝術進行進一步的認識與發掘,實現更有效的、有意義的闡釋。
二、視域融合
《文心雕龍》當代闡釋,正如一千個讀者一千個哈姆雷特一般,存在著闡釋者與作者與文本之間的循環。那么,如何理解,并且如何正視這樣一個問題,就需要闡釋者進行必要地視域融合。正如前文所講,有研究論述劉勰受儒家的思想,或受道家的思想,抑或受佛家的影響。闡釋者都是從主體角度出發,進行論述其自身對于劉勰《文心雕龍》的認識,對于某一問題進行闡釋論述。視域融合強調的是作者的視域與闡釋者的視域進行融合,在現在的研究中,這個融合是有較大的延伸與擴展的,不是作者與闡釋者的視域融合之后,反之其視角變小了,而是不斷拓寬與發掘的進程。舉個例子,作者烹飪了一道美味的佳肴,闡釋者進行闡釋的過程中,在原作者烹飪的基礎上,加入了新的調料,形成闡釋者的視角,這就是一個有效的拓寬與發掘的過程。當然,在這里也存在著施萊爾馬赫的闡釋觀與伽達默爾闡釋觀的不同,施萊爾馬赫強調闡釋者的闡釋是無限接近作者愿意的過程,而伽達默爾強調的是闡釋者的主體性闡釋。筆者更傾向于伽達默爾的闡釋者的主體性闡釋的闡釋觀,因為正如羅蘭·巴爾特強調的“作者之死”,文本的意義超越了作者而趨向于獨立存在,這就更凸顯了闡釋者主體間性的重要性。不論是任何闡釋者在論及《文心雕龍》的任何方面,都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都豐富了《文心雕龍》的當代意義。當代《文心雕龍》的闡釋,有對劉勰生平的考證,有對其文本內容的分析,有對其結構的剖析等等,但是這些所有的闡釋都不能離開闡釋的循環,把握文本的原意的基礎上進行闡釋分析論述,才能夯實闡釋者的闡釋文本的信度與效度。那么,如何進行闡釋的循環,施萊爾馬赫所講,闡釋者必須從細節中去理解文本,同時也必須從整體上把握文本,簡而言之就是細節與整體的統一。這樣才能夠不使闡釋的主體性失去其立足的土壤,反之,不進行有效的元文本理解,就去盲目闡釋,則失去了對于該文本闡釋的初始意義,更談不上闡釋者的主體性。任何文本都需要結合時代的特征,進行符合時代的闡釋,這是主流的,當然,筆者所述的主流是為符合歷史潮流的,經得起歷史考驗的主流。
最后,視域融合是闡釋者、文本、作者的不斷拓寬的融合。闡釋者需要持續有效地進行基于文本細讀的闡釋循環,推進闡釋的時代轉化,實現闡釋的視域融合。前文所述,僅僅是當代學者對于《文心雕龍》的當代闡釋,其闡釋視角也很明確。但是隨著當下中國綜合國力的日漸強盛,亟待轉化20世紀由西方文論主導文學理論的歷史現狀,不僅僅是以中釋西,抑或是以西釋中,筆者認為這都是不全面的,《文心雕龍》作為一部具有重大文學理論價值的文學著作,其視域融合也應著眼于全球文學理論這一視角,強調其整體進而實現整體的話語權轉向。
參考文獻:
[1]甫之 涂光社主編.《文心雕龍》研究文選[M].濟南:齊魯書社,1988:1-1080.
[2]劉永濟校釋.文心雕龍校釋[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
[3]王運熙 周鋒譯注.文心雕龍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4]吳林伯注.《文心雕龍》義疏[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
[5]胡海 楊青芝著.《文心雕龍》與文藝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張習文.伽達默爾視域融合理論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2.
[7]王濤.論視域融合的內涵及其對中西比較史學的重要意義[D].陜西師范大學,2013.
[8]黃文前.試論“視域融合”[D].陜西師范大學,2000.
[9]柴橚 袁洪庚.隱身于譯者主體性背后的“視域融合”[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