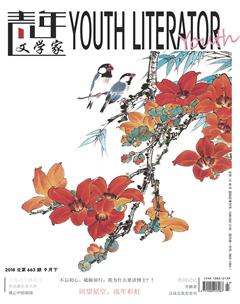淺析《麗吉婭》意志隱喻整體效果的生成
摘 要:在愛倫坡的創作觀中,整體效果始終是其堅守奉行的原則。在《麗吉婭》中,開篇的題記、美人意象的隱喻、場景作為內心世界的外化以及最關鍵的借尸還魂的情節設置,都可視為愛倫坡為了實現其整體效果而做出的精心安排。并且通過對關鍵線索的串聯和聯系,可以發現意志是小說在極力表現的關鍵詞,通過意志的力量與失去意志會出現的可怕情境,讓讀者同樣在恐怖感中生發出對意志力量的關注。
關鍵詞:《麗吉婭》;意志;整體效果
作者簡介:陳培玉,四川大學文新學院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專業。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7--02
在愛倫坡的創作理論中,整體效果論是貫穿其創作的核心觀念。他認為:“聰明的藝術家不是將自己的思想納入他的情節,而是事先精心策劃,想出某種獨特的、與眾不同的效果,然后再杜撰出這樣一些章節——他把這些情節聯結起來,而他所做出的一切都將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實現在預先構思的效果”[1]在愛倫坡的作品他始終都在追求最終效果的實現。那么在《麗吉婭》這篇小說中,他意欲實現的效果是什么?這種效果又是通過怎樣的方式達成的?
在對這篇小說的整體效果探討之前,需要認識愛倫坡的讀者觀。在愛倫坡對自己讀者觀的論述中,“他突出地介紹了古代斯巴達人的‘圓筒配對法:發信人與收信人分別擁有兩個尺寸外形完全相同的木質圓筒,前者將細長條狀的羊皮紙均勻纏繞于圓筒外壁,而后以橫向書寫的方式將信息表于其上。如此一來,取下的羊皮紙上便只顯現出看似毫無意義的縱向字母排列;收信人接到訊息后,將其均勻纏繞于自己手邊的同尺寸圓筒上,而后以橫向閱讀的方式加以解碼。”[2]坡創作小說企圖實現一種效果,而這個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于讀者的接受情況的追求。這種看法也體現在愛倫坡批評霍桑小說曲高和寡中。小說創作是面向更為廣泛的讀者的,而不僅僅是像霍桑的小說只是寫給自己和身邊的幾個朋友看。那么愛倫坡創作《麗吉婭》想要實現什么樣的效果,也就等于作者希望讀者可以在小說中獲得什么樣的體驗。為了使讀者和作者之間可以達成,制謎與解密的關系,作者在細節之處暗暗留下線索或者僅是一種感覺,將一種完整的情緒與氛圍指向一個統一的效果之中。
作為整體效果的組成部分,驚悚的情節、陰暗的場景、凝練的意象、是構成《麗吉婭》的重要部分。當然作者所安排的細節遠不止這些,所有的細節可以說都是作者為了實現效果的安排所為。下文將通過對三個方面的分析,去探尋愛倫坡在《麗吉婭》中最終追尋的效果是什么。
一、美人意象隱喻意志
麗吉婭作為小說中引起“我”生命軌跡起伏變動的動力,古典優雅的樣貌、廣博深邃的學識、蓬勃昂揚的生命力,以及麗吉婭對于“我”的啟發,給“我”的愛和引導,使得這一角色似乎“只是為了代表一種思想,這種思想幾乎可以理解成故事的寓意。”[3]
愛倫坡歷來都將霍桑的寓言性創作視為一個反面案例,但這并不意味著愛倫坡本人對作品中的寓言性的全盤拒絕。只要通過恰當的方式,寓言性仍是虛構小說的一個內涵要素。“對于虛構性敘事而言,寓言畢竟還是能夠在恰當利用的情形下獲得一席之地的:關鍵只是在于要確保隱性意義,以一種極為深邃的暗流貫穿于顯形意義之間,從而避免表層意義在未經讀者意志操控的情形下受到干擾。”[4]結合這種說法可以認為,在愛倫坡的小說中也可能會具有寓言性,只是這種寓言性是隱性的。因此也不妨認為麗吉婭是具有寓言性的小說,而她的隱喻埋藏在愛倫坡所創作的故事與情節中。但這種暗流也并不是讓讀者完全捉摸不透,愛倫坡在講寓言性化成暗流的時候,同時也給讀者留下了解讀文章的一把鑰匙。
這把鑰匙便是作者放在小說開篇,它既抓住讀者的注意力也是愛倫坡個人表達內容的指向,這就是小說中的題記。“意志就在其中,意志永不消亡。誰能知曉意志的神秘和活力?上帝不過是憑自己的意圖而彌漫于萬物的偉大意志。人并不屈從于天使,也不徹底屈服于死神,除非意志薄弱。”[5]這句話著重在強調的是意志。作家為了強調這一點,在文章中也將其顯著標志出來。在小說中也強烈地渲染了麗吉婭身上強大的意志力以及她對于生命的渴望,在她與死亡抗爭無可避免地失敗時,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話也正是:“人并不屈從于天使,也不徹底屈服于死神,除非意志薄弱。”[6]因為麗吉婭的這種特質,從她那里也傳遞給“我”對于意志同樣的感受。因此麗吉婭可以視為對意志的一種隱喻,作者在小說中給我們留下了線索將二者勾連起來。也的確,將這一層寓意帶入來解讀小說時,是完全合乎于小說的整體構造的。
麗吉婭的美貌、學識、對“我”的意義,如果還原是對意志的寓意表達的話,也就是指意志尤其是勃勃的生命力,麗吉婭的形象也就是在說意志本身的美好,而且它能夠喚醒人身上的積極因子,對于個人的激勵鼓舞,就算經歷了與死神的殘酷對抗之后,意志同樣也不會屈服。擁有意志就意味著存在,正如麗吉婭自己因為擁有不曾屈服的意志,她的存在是從始至終的。在“我”搬到荒僻的修道院之后,“我”依然會感受到麗吉婭的影子在游蕩。以致到最后“我”親眼目睹了麗吉婭借尸還魂。意志的永生是不可輕視的,而“我”曾經擁有過強大的意志,一如麗吉婭讓我感受到的力量。然而當“我”遭遇了一次意志的重大挫折之后,便日漸消沉一去不復,麗吉婭死了,“我”的意志磨煉并未從她那里獲得完滿的充實,麗吉婭未曾與死亡妥協,但“我”卻因為麗吉婭的死,帶給“我”意志力的源泉的枯萎,而被死亡打敗。
二、場景作為意志力喪失的外化
在小說的后半部分出現的陰森恐怖的氛圍,可以說是一個人在意志受挫,頹廢于現實所留下的痕跡。沉溺于毒品和幻滅的生活中,也讓“我”哪怕活著,卻形如游走在生死邊緣的幽靈,虛弱縹緲喪失了堅定的生命力。麗吉婭的死對“我”而言是生命的轉折,自此以后“我”便過上了另一種全然不同的生活。隨之發生改變的還有“我”生活的環境。在小說的前半部分沒有出現過對場景的相關環境,“我”的全部的精神和注意力都灌注在麗吉婭的身上。而當麗吉婭死后,“我”便沉迷于藥物之中,常常神志不清,再婚之后與妻子一起住在荒僻幽暗的廢棄修道院中。由麗吉婭曾經充實填補的那部分生活變得空洞了,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無法彌補。“我”后來選擇的住址和家居裝飾可以視為是“我”的精神狀態的外化,作者也花了很大篇幅在極力地將這種混亂陰森的精神通過場景布置展現出來,也為“我”后來漸漸暴露出的心理恐怖做了充足的鋪墊。
首先是居住的這所修道院“位于美麗的英格蘭那人煙罕至的荒野地帶。房子陰郁、沉悶、莊嚴,周圍幾乎呈現出原始的景象,許多傷感和悠久的回憶籠罩它們,使一切融合在一種徹底廢棄的情緒中……”。[7]從“我”對居住地的選擇來看,“我”始終沉溺在失去麗吉婭的痛苦中,無法解脫,并且由此衍生出越來越濃郁的頹廢情緒。這頹廢的情緒隨著“我”,在一天一天地加重,于是出現了濃墨重彩描寫下的婚房。“房間的每個角落里都豎放著一口巨大的黑色花崗巖石棺,那是從正對著盧克索古城的法老墓里運來的,古老的棺蓋上不滿了遠古的雕刻。”[8]從“鉛色玻璃”“縱橫交錯的枝蔓”到貌似棺木的床以及房間各個角落的花崗石棺槨,這些陳設武夷不會是讀者聯想到黑暗陰森、神秘壓抑的墳墓,即使是婚房,卻處處凝聚著死亡的氣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新婚的妻子一天一天身體變得虛弱,而“我”也同樣在這個環境中迷亂混沌。這一切都是源于當意志與生命力喪失之后,造成的難以平復的痛苦。干枯的意志與生命帶來的便是如小說中的場景這般,無序亂碼和空洞失衡的體驗感。
三、關鍵情節爆發意志
然而由場景所制造出來的低沉陰暗的氛圍,作為意志消沉的外化表現,還不能夠完全表現作家所欲實現的整體效果。作家需要借助最關鍵的一個情節設置來完整其整體效果。“在坡的眼中,事件表現出了些許‘工具理性的特征。它們主要是通過建構迂回蜿蜒的敘述路徑以引導讀者在渾然不覺之中走向某個神秘的終點。”[9]在小說里,最高潮的情節便是“我”在神智迷亂之際看到了麗吉婭從亡妻尸體上復活。《麗吉婭》的復活在愛倫坡的創作史中并不是孤立的出現,《莫蕾娜》《額舍厄舍屋》《與一具木乃伊的對話》等篇目中都對這一主體有詳細描述。在最終的恐怖到來之前,已經有了很長篇幅的鋪墊,讓故事的走向變得神秘黑暗、驚悚彌漫。
讀者所獲得的恐怖感不同于在愛倫坡的某些小說中的修辭上的暴力帶來的生理不適而出現的恐懼。《麗吉婭》里借尸還魂的恐怖感,首先是一種心理恐怖。這種來自心靈受到的恐怖,源自小說的敘述者在遭遇了極大的悲慟之后,意志渙散而產生了對外界反應的扭曲。扭曲現實在主人公的世界里意味著無可逃避的窒息與壓抑,于是心理在重壓之下出現了恐怖的精神幻象,但這幻象卻能扎根在精神世界中,無處不在。這又會進一步地加重心理的恐怖,而使得這種恐怖感獲得了蔓延至無窮的可能。借尸還魂便是這種心理恐怖的最終爆發,現實與幻象已然模糊了界限,在虛實的邊緣,麗吉婭復活了,而“我”的精神卻面臨著崩潰與死亡。從始至終,生與死的沖突都無比激烈地貫穿在小說里,并且始終都保持尖銳的對立。
借尸還魂這一情節成為小說恐怖感爆發的高潮,這種恐怖感的傳遞給讀者的通道是“我”。通過“我”的眼睛、意識去感受了麗吉婭復活的恐怖景象。以第一人稱的帶入感和詳盡細致的感觸為讀者建構起了強烈的情緒體驗,這故事是虛構的,而這情節中獲得的恐怖感確是真實的,用真實的體驗刺激心靈以喚醒受到鈍化的感受力。在這種強烈的感受激蕩之下,會讓人感受到本篇小說處處強調的意志的巨大力量。愛倫坡在最后,用借尸還魂這樣極度恐怖的情節,既讓“我”重新看到麗吉婭,給了“我”再一次觸摸的意志的溫度的機會,也讓讀者走入了一個因為極端恐懼下引起的內心強烈的震撼,以此來喚醒讀者對于意志的感受力。可以說,在這里,愛倫坡所欲在這篇小說中實現的整體效果得到了完滿的表現。
注釋:
[1]于雷,《愛倫坡小說美學芻議》[J].外國文學,2015(01).
[2]于雷,《愛倫坡小說美學芻議》[J].外國文學,2015(01).
[3]哈利·李·坡《永恒:埃德加·愛倫·坡與其世界之謎》[M].袁錫江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4]于雷,《愛倫坡小說美學芻議》[J].外國文學,2015(01).
[5]埃德加·愛倫·坡,《摩格街謀殺案》[M].張瓊 張沖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6]埃德加·愛倫·坡,《摩格街謀殺案》[M].張瓊 張沖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7]埃德加·愛倫·坡,《摩格街謀殺案》[M].張瓊 張沖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8]埃德加·愛倫·坡,《摩格街謀殺案》[M].張瓊 張沖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9]于雷,《愛倫坡小說美學芻議》[J].外國文學,2015(01).
參考文獻:
[1]埃德加·愛倫·坡,《摩格街謀殺案》[M].張瓊 張沖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于雷,愛倫坡小說美學芻議[J].外國文學,2015(01).
[3]曹曼,從效果說看愛倫坡作品主題的藝術表現構架[J].外國文學研究,2005(03).
[4]任翔,美·死亡·恐怖——論艾倫·坡的詩歌與心理小說[J].文藝研究,2011(09).
[5]哈利·李·坡,永恒:埃德加·愛倫·坡與其世界之謎[M].袁錫江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