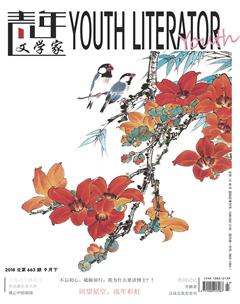“出自/于”的詞匯化與語法化
摘 要:“出自/于”在《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中被歸為動詞類,然而其從上古到中古乃至近古時期都一直存在臨時搭配的現象,期間也包含一個逐漸固化為詞的過程。因詞匯化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語法化,我們發現“出自/于”發展成為一個動詞這一現象并不是它的終點,它也正朝著由實到虛的這一方向發展。
關鍵詞:結構的演變;詞匯化;由實到虛
作者簡介:郝瑞澤(1993-),男,漢族,河北定州市人,文學碩士,延邊大學語用學專業碩士2017級研究生,研究方向:對外漢語教學。
[中圖分類號]:H1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7--02
引言:
大概在先秦時期,“出自/于”絕大多數都是以松散的結構形式出現,即“出”與“自”、“出”與“于”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不緊密,而是“自”或“于”與后面的賓語的關系更緊密,如:
(1)日居月諸,出自東方。(《詩經》) (2)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詩經》)(3)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左傳》(4)出自湯谷,次于蒙氾。(《楚辭》)(5)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尚書》)(6)伐虢之役,師出于虞。(《國語》)
上述各例中我們更傾向分別把它們理解為“自東方出”、“自幽谷出”、“自東門出”、“自湯谷出”、“于陶丘北出”、“于虞出”這樣的介賓結構作狀語的情況。因此我們認為,大致在這個時期“出自/于”兩者的結構關系相對松散,屬于臨時搭配的情況,并且我們注意到其后面所接賓語大多都是具體的且表示地點、方位的名詞,這也更好的解釋為什么“自/于”與后面賓語關系更加緊密而不是與“出”的關系緊密。
一、“出自/于”的詞匯化過程
“出自/于”的詞匯化過程是按照歷時的發展脈絡演變的,我們整理出大量的語料后發現它們的發展演變具有很強的規律性。下面將從兩個方面來進行具體的說明:
1.1“出自/于”的語法特點
前面提到大致在先秦時期,“出自/于”屬于臨時搭配的情況,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出自/于”逐漸開始固化為一個動詞。既然它當時正朝著動詞類的方向發展,那么它就應該具備一個動詞本應該所具有的語法特點,如下面的例子:
(7)其先出自炎帝。(《北史》)(8)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因話錄》)(9)寧既厚結元載已久,楊炎又出自載門,寧初附炎,炎因此大怒。(《舊唐書》)(10)而吳歌雜曲,始亦徒歌,復有但歌四曲,亦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樂府詩集》)(11)員外道:“我愛那縫補處,這行針線,必出自妙手。”(《警世通言》)(12)蓋皆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周易》)(13)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淮南子》)(14)通《毛詩》者,多出于魏朝劉獻之。(《北史》)
上述大致是沿著歷史發展的脈絡列舉的,我們不難發現,“出自”具有很強的規律性,與之前不同的是,從漢代到元明“出自”的前面出現了副詞如“先、多、又、亦、多、必”等,而我們從大量的語料中發現從漢代到魏晉六朝“出自”前所用的副詞偶有所見,而到了隋唐五代開始有大量的副詞出現在“出自”的前面,既然它開始受副詞修飾,那么我們認為,大致從漢代開始出現詞匯化,到了隋唐五代開始逐漸趨于固化,但即便是出現了大量副詞修飾的現象,之前臨時搭配的用法仍舊很多,因此還是處于一種用法較為復雜的狀態。而反觀“出于”,它的規律性相對較弱。上述例子中在《周易》中就已經存在副詞修飾的情況,而到了漢代開始大量出現副詞修飾的現象,如:“也、不、皆、先、多、又、忽”等,與“出自”前面所用副詞大致相同。總之,它們既然能受到副詞修飾,則可以說明它們更傾向于是一個動詞了。
1.2結構及后接名詞的變化
前面說過,“出自/于”起初是一個“V+P(O)”結構,那么結合前面的例子與下面的例子進行對比:
(15)帝嘆息,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宥怒,出自人君。(《三國志》)(16)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北史》)(17)召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由宰相,況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舊唐書》)(18)楊八老出自意外,倒吃了一驚。(《喻世明言》)(19)烏大爺道∶“老師這幾個門生,現在的立身植品,以至仰事俯蓄,穿衣吃飯,那不是出自師門?(《兒女英雄》)(20)止是這時正拿著媚外手段,礙著日本公使夫人情面,所以假意奉承,并非出自本心。(《女媧石》)(21)帝曰:“此當出自朕意。(《續資治通鑒》)
拿“出自”來說,看前面的四例中都沒有副詞來修飾,但是根據結構或者是根據句義,我們都可以推斷出此時“出自”是作為動詞的,也就是說此時“出自+NP”是動賓結構,兩者之間邏輯關系很緊密,絕不能看作或者是翻譯成“自xx出”的意思。再看“出自”后面的名詞性成分,有的是指人名詞如“人君”,有的是與人有關的抽象名詞“本心、朕意”等,由此對比前面的例句我們可以發現,“出自”后面的名詞性成分由之前具體的、表地點或方位的成分擴大到表指人的或與人相關的抽象性成分,正是因為這種改變才為它的詞匯化或語法化提供了可能。同樣“出于”情況與“出自”相似,舉出兩例而不做贅述。
(22)這“弦歌”高樓的佳人,也還是出于詩人的虛擬。(《古詩十九首》)
(23)今七廟之義,出于王氏。(《晉書》)
二、“出自/于”的語法化
本文在摘要中就提到“出自/于”在《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中被歸為動詞類,上文中我們闡述了“出自/于”的詞匯化過程,而且我們也知道詞匯化現象不可避免地會伴隨著語法化,因此我們通過對語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后發現:“出自”似乎沒有出現虛化現象,而“出于”出現了由實到虛的情況,如:
(24)尤惡下為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于天性。(《舊唐書》)(25)俗重氣俠,好結朋黨,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義。(《隋書》)(26)此似鄙吝,且出于不得已。(《東坡文集》)(27)而甲午之大亂,出于民怨。(《東坡文集》)(28)逮此干聞,出于窘迫。(《欒城集卷四十九》)(29)出于狂戇,不足加罪。(《后漢書》)(30)出于無計,遂欲休糧以清凈勝之,則又未能遽爾。(東坡文集)
先看前五個例子,似乎很像前面列舉的“動賓結構”,其實并不一樣,前面的“出自”不管是臨時搭配還是“動賓結構”,它本身所表達的意義幾乎沒有改變,它都側重于“出”字上。可是上面幾個例子中的“出于”則不同,雖然也不能看作是“于xx出”這樣的形式,但是這里更傾向于表達的是“由于、因為”的意思,即“由于/因為他的天性,他好結朋黨”、“由于民怨,才導致甲午之大亂”,那么這樣的話“出于”就更傾向于介詞詞性,雖然介賓結構作狀語出現在謂語之后很難以讓人接受,但是從句子的意義上講似乎這樣才說得通,即便是這樣的例子不足以說明問題,那么(29)(30)兩例中“出于”分別放在句首,這樣就更具有說服力。而且在現代漢語中雖然把它歸為動詞類,但是介賓結構作狀語的用法也逐漸多了起來,如:
(31)出于禮貌,我說了聲謝謝,問他:“你怎么會知道我的生日?”(《幸虧她的指點》)
(32)出于職業的習慣,也出于對一個有成就的科學家的愛護、對親友的關心,他強迫張戈躺在床上,要為他詳細檢查。(《起死回生》)
(33)出于這一考慮,他們將升任南澳鎮總兵的惠昌耀暫留香山協之任,撥發水陸兵數百名在澳門附近的各個要隘布防,還決定派遣官職較大的干員進駐澳門,以控制那里的局勢。(《澳門四百年》)
(34)出于生活所迫,她不得不起早站排買些電影票,然后轉手賣給后來買不到票的觀眾,其代價僅僅是買她兩包瓜籽,票價分文不多取。(《電視文學概論》)
三、結語
上述可以看出,“出自”具有很強的規律性,即隨著歷時的演變受副詞修飾的現象逐漸增多,并且后面所接賓語也是由具體的、表示地點或方位的名詞逐漸擴大到表示指人或與人相關的抽象性成分;與之對比,“出于”的規律性則不那么明顯,通過語料可以看出“出于”一詞,不論是從它受副詞修飾這個角度還是從它后接賓語這個角度來看,它都處于一種錯綜復雜的狀況。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自”和“于”同樣作為介詞,并且共現在“出X”結構中,那么為什么“出自”似乎沒有虛化為介詞的可能,而“出于”虛化為介詞的可能如此之大,其中的原因也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的探究。
參考文獻:
[1]劉紅妮.詞匯化與語法化[J].當代語言學.2010,12(01).
[2]陳昌來.漢語介詞的發展歷程和虛化機制[J].柳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2,(03).
[3]劉堅,曹廣順,吳福祥.論誘發漢語詞匯語法化的若干因素[J].中國語文.199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