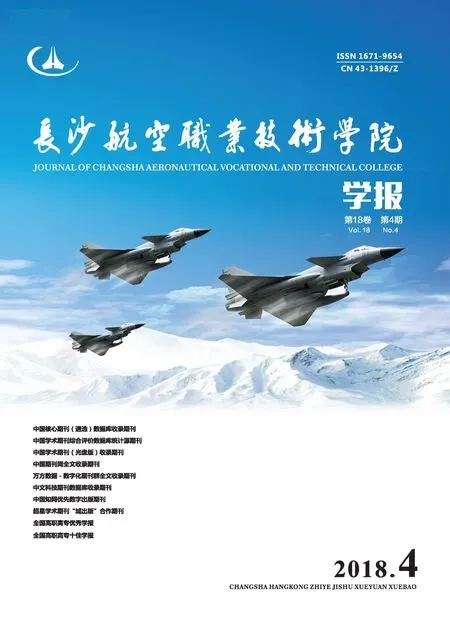智慧監管:民用無人機企業監管的路徑選擇
問延安,蔣 倩
(安徽工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院,安徽 馬鞍山 342032)
國內民用無人機應用始于20世紀80年代,主要用于航空測繪和物理探礦[1]。從20世紀90年代至2006年,民營企業陸續進入到民用無人機的研發隊伍中,產品主要用于科研,未能量產及普及。2007年到2012年前后,民用無人機制造商開始涌現,軍工集團亦開始涉足民用領域。2012年前后至今,以大疆創新為代表的無人機向消費級市場展開強烈攻勢,無人機真正走進大眾視野,短短幾年內,零度智控、奇蛙、云頂智能等民用無人機企業相繼成立并引導了國內民用無人機行業的巨大變革。
然而,無人機的民用化除了便利之外,其衍生出來的公共安全等問題亦逐一浮現。2016年8月,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和埃迪斯科文大學聯合公布了一項研究成果,他們分析了2006年~2016年間澳大利亞發生的150起無人機事故,發現其中64%的事故主因是無人機技術故障[2]。我國民用無人機行業近年來取得長足發展,但由于監管規制主體多元,涉及的主管單位包括民航總局、工信部、工商總局、海關總署、公安部、體育總局、軍方等諸多機關部門,各環節管理工作難以有序銜接,協調難度大,很難對民用無人機的研制、銷售、使用、維修、報廢的運行周期展開有序管理;加之民用無人機種類繁多,構型、重量、航程、續航時間、使用動力、任務載荷、操控模式各異,準確對其分類管理的維度有待細化設置;遑論對呈井噴式發展態勢的民用無人機企業類別繁復產品質量展開有效監管。技術盲區和創新驅動,使得政府相關監管部門面對頻發的“炸機”投訴往往或束手無策或偏信企業,在市場與安全間難求平衡:放任式監管,無人機產品的安全漏洞及開源飛控可能會呈病毒式蔓延態勢,在拉低無人機市場技術門檻的同時,有可能加劇技術故障引發“炸機”安全問題;封殺式監管,在互聯網時代已無可能,其結果可能是無人機的便利被扼殺,而無人機“炸機”隱患依舊存續。那么,政府相關部門如何能通過適度監管規制無人機企業,導引其走出一條將無人機“炸機”減少至可控范圍內,并實現市場與安全平衡之路呢?
1 監管無人機企業的困境分析
在監管政策相對滯后技術發展的互聯網時代,產業涌現、技術缺陷、管理失措交織在一起的無人機“炸機”風險陰云,依舊密布在我們的頭頂之上,單純依賴政府相關部門游離在技術盲區中的無序監管,可能只會不斷陷入“一放就亂,一管更亂”的陷阱(圖1)。

圖1 監督無人機企業的困境
困境一,監管機構易陷入規制俘獲[3]。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出現了新的變化,無人機企業成為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驅動的加速器;以新科技為導向,20世紀90年代美國企業所發起的“重理管理”運動[4]影響到公共部門,“重理政府”改革浪潮亦波及我國。基于兩股力量的驅動,我國無人機企業對政府產生了潛在的規制俘獲,或者更準確地稱之為規制俘獲中的類型之一:“企業影響”。只要未出現大規模公共安全威脅,監管規制就處于失語狀態。
困境二,監管機構難擺脫技術失靈迷霧。技術失靈是無人機企業“俘獲”或“影響”政府相關部門的內在原因之一。歷經新舊兩大發展階段的規制俘獲理論,從市場失靈到引入信息失靈,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驅動著規制俘獲理論引入技術失靈概念,無人機企業對技術的開發和利用是以效率和利潤為標準的,技術自身不會自動關注產品質量及公共安全問題;再者,技術開發存在著不對稱性,技術活動的專業化會制造出無人機企業技術復雜性的“迷霧”,政府相關部門難以提供適配的監管規則。顯然,以大疆創新為代表的無人機企業正是借助技術發展優勢及高新企業的“光環”,跳脫出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管,并利用技術復雜性“影響”監管部門。
2 智慧監管的意涵
智慧監管衍生自回應性監管理論[5],先以政策框架面貌呈現,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倡導以智慧監管替代命令控制型監管[6],歐盟以“管的更少,管得更好”來概括智慧監管的內涵,受國際合作組織推崇的智慧監管框架日益引發學術界的熱議。
智慧監管可以在放任和封殺式監管之間達致一種平衡,在應對技術及利益復雜的環境政策問題上取得了較大的成功,為消解贊成國家強力監管和主張放松管制者之間的意見分歧提供了有效途徑[7]。智慧監管具備一種后“命令控制”式的監管面相:政府干預是必要的,但需輔以一系列市場和非市場的解決方案;政府等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公眾及社會組織相結合,共同制定監管制度和政策,以實現預期的政策結果。不少學者陸續提出了智慧監管的原則,可以綜合概括為八個方面,具體如下:1)避免相鄰政策的不當影響;2)在復合政策工具的范圍內,選擇最具成本效應的監管組合;3)公共和私人機構組成混合監管主體;4)發展新環境下的政策工具(如網絡監管技術)來解決傳統政策工具失靈問題;5)借助激勵和信息工具提升監管政策的效果;6)采用適度干預的監管措施;7)確保強力干預式監管手段的威懾效應,以應對不可逆風險的威脅;8)實現雙贏結果的最大化[8]。有學者亦聚焦于智慧監管策略研究,提出公共部門、私人部門與社會組織混合監管的四大策略:全面互補、全面互斥、按序互補、按需互補[9]。依據這些原則和策略建構出智慧監管框架(圖2),有助于破解監管無人機企業的困局。
3 智慧監管對監管無人機企業的啟示
當前,“大眾創新,萬眾創業”浪潮和“放管服”改革驅動了國內無人機企業的飛速發展。一方面,相關公共部門對監管的“公正、理性、適度”特性思考不足;另一方面,無人機生產企業技術發展速率和增長指數遠遠超過監管部門的知識儲備,針對魚龍混雜的無人機產品,政府相關部門難以建立有效的質量監管框架。而智慧監管關注透明度,注重消解公眾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推崇簡潔性原則,祛除遮蔽公共利益的復雜性(或假象),為相關公共部門對無人機產品質量監管提供了有益補充,促進了人工智能時代公共管理監管理論的發展。
基于互聯網的公眾自發監管無人機企業的非政府力量,有諸多優勢:從網絡信息的可共享性來看,有助于建立無人機產品信息共享機制。從公共協商機制來看,有助于實現監管規制的適度性。監管政策唯有建立在各利益相關主體廣泛認同和支持的基礎上,才能凸顯其可執行性和適度性。無人機網絡論壇可以為無人機監管過程的多元主體提供了表達、交流、協商的平臺。政府借助公眾自發建立的無人機監管平臺,要求無人機企業公開技術信息,讓無人機愛好者、消費者、公眾、行業協會、媒體等分析并使用這些信息,給無人機企業施加壓力,充分發揮“智慧監管”力量對無人機企業的約束力。互聯網技術與無人機監管政策的高度融合,或許會大幅度減少因產品質量缺陷導致的“炸機”,促進無人機融入國家空域系統的進程。
智慧監管機制的核心是回應、塑造、協同和關系,塑造是智慧監管機制中最重要的一環。政府相關部門對公眾參與監管支持不足,會阻隔甚至扼殺公眾、企業以及政府間合作的可能。政府相關部門應明確與無人機企業、公眾之間的關系,完善配套制度,著眼于提供服務,才有建立智慧監管機制的可能。政府提供政策支持服務、市場供給優質產品、社會公眾理性監督、行業獨立自律、企業優化技術,各方共同發力,才能消解技術失靈,培育壯大公眾監督網絡平臺,實現多元治理,消解無人機“炸機”,為民用無人機安全融入空域系統保駕護航。
4 監管無人機企業走向智慧監管的路徑
從智慧監管的原則及對無人機企業監管的啟示出發,結合我國無人機企業監管現狀,提出對無人機企業智慧監管的路徑和方法。

圖2 監督無人機企業的智慧監管框架
4.1 整合監管政策
我國現有的民用無人機規范性文件包括《民用無人駕駛航空器系統空中交通管理辦法》(2009年)、《民用無人機駕駛員管理規定》(2013年)、《輕小無人機運行規定(試行)》(2015年)、《民用無人機駕駛航空器實名制登記管理規定》(2017年)等,各地區亦出臺了諸多地方性的管理規章。現有的監管民用無人機的法律法規多以部門規章的形式出現,這些碎片化的臨時性規定,很難對無人機企業的制造、運營、銷售及使用環境展開全面監管。從國際經驗來看,制定統一無人機系統監管條例是必要的,在工業界和學術界的合作下,各國航空部門和國際組織正在制定統一的民用無人機路線圖、適航性和設計標準及監管政策,如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在2007年成立了一個致力于協調15個成員國及8個國際性組織之間監管條例一致性的無人機系統研究小組(UASSG)[10];日本國會在2016年通過了《無人機管制法》;德國聯邦交通部于2017年出臺了所有無人機必須上牌的規定。借鑒域外經驗,我國宜加快對無人機企業研發、制造、銷售、培訓和使用的統一立法。
4.2 建立多元監管機制
適度有效的監督離不開已經開發的和可能實施的足夠成熟的技術。鑒于無人機技術的復雜性,監管部門需要同無人機企業合作,以獲得制定監管技術和標準所必須的相關信息。如美國針對無人機企業的監管標準先由業界承擔,聯邦航空管理局積極參與標準的制定,監管機構和企業在達成自愿共識的基礎上,建構監管框架。在不斷更新迭代的無人機技術背景下,監管部門被動緩慢地通過調整現有無人機規則的監管效度是有限的[11]。政府、行業協會、企業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監管,在無人機工業設計標準制定、避障的標準化通信技術研發等方面,企業和行業協會能發揮重要作用;無人機愛好者群體參與監管,既有助于倒逼無人機企業不斷改進其產品品質。民用無人機能否順利融入國家空域系統,公眾接受是重要基石之一。糅合行業和組織自律的多元監管模式,可以為智慧監管無人機企業提供更為適度的支撐框架。
5 結論
21世紀以來,隨著無人機民用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各國逐步建立了適用民用無人機的國家法律框架,旨在減少民用無人機帶來的風險,統一的監管標準正在逐步形成。
進一步研究的方向是智慧監管無人機政策框架的制定及實施,以無人機融入空域系統為目標,借助硬性法律規定和柔性條例的約束,整合市場和社會的力量,圍繞國家監管的主軸,監管部門與無人機生產企業、無人機愛好者真誠溝通。總體來看,政府相關部門應對智慧監管無人機企業進行引導和規范,當然,有效引導和規范的前提是七大公共部門間能形成統一的政策和行動,而這又離不開有效的跨部門協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