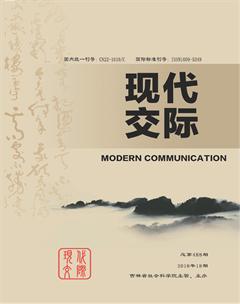盜竊罪與侵占罪的界定因素分析
王藝霖
摘要:認定物的占有狀態是區分盜竊罪與侵占罪的關鍵,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不同情況下財物占有狀態的界定缺少實質標準,單純通過對占有狀態的判斷界定盜竊罪與侵占罪難以應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多類新案例、新情況。本文通過借鑒因果關系原理中的介入因素理論,在難以認定占有狀態時引入對行為人取得財物手段的考量,通過比較占有狀態與行為人手段這兩個因素的作用地位,判斷案件性質,并在量刑階段對占有狀態和行為人手段進行程度上的考察,進而提高案件處理結果的合理性。
關鍵詞:侵占 占有 遺忘物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8)18-0041-02
一、本質區分因素:物的占有狀態
成立盜竊罪須滿足“竊取他人占有的數額較大的財物”,他人占有是盜竊罪成立的前提。而在侵占罪中,侵占代為保管的他人之物、遺忘物、埋藏物的行為,都未破壞他人占有。可見盜竊罪與侵占罪的本質區別在于行為發生時物的占有狀態,對有人占有的財物與遺忘物、埋藏物的界定更是區分盜竊罪與侵占罪的關鍵。
理論上來講,盜竊罪與侵占罪的占有狀態是一般化、理想化的。認定行為人構成盜竊或侵占時,要求可以清晰地判別物的占有狀態,也即在理想情況下,他人占有與無人占有是獨立且相反的。但在司法實踐中,二者并非獨立于彼此,而是對占有程度判斷中的兩個極端狀態。對侵占罪與盜竊罪的界定難點,是在于對兩極端中間不同程度占有狀態的評價。司法實踐中涌現的新案例、新情況正是這一點的有力證明。例如許霆案中對故障ATM機中的錢是否脫離銀行占有的判斷,以及梁麗案中在機場取得的財物是否應認定為無人占有的爭論都給司法實踐與理論帶來了新的難題。
許霆案與梁麗案之所以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是因為對這兩個案件的裁判結果并非僅代表個案中的公平正義,更與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無數新案件緊密相連。在這兩個案件中,ATM機系統故障的程度以及機場管理人員或物主人對財物的控制可能性,是判斷財物占有狀態需要考慮的因素,本文姑且稱其為物與占有人分離程度因素。當可以清晰推定物與占有人完全分離時,分離程度達到100%的理想值,反之,當占有人對物具有絕對的占有時,分離程度為零。在這兩種情況下,區分侵占與盜竊并無難度。難點在于,對介于兩個理想狀態之間不同情況的認定,并沒有確定的模型或標尺,使得盜竊罪與侵占罪的界定只能借助個案中司法人員的經驗法則和價值判斷。董玉庭教授對此提出,當物在公共空間脫離原占有人的占有時,若該區域管理者有足夠的能力管理遺落的財物,其主人毫無疑問是管理義務人。反之,若空間管理者對遺落的財物不具有管理可能性,則應認為該空間沒有管理義務人,財物脫離原占有人的占有則應為無人占有的財物,馬路的管理者因為根本無能力管理遺落的財物,毫無疑問不能成為管理義務人。這種觀點的提出對財物所在空間的類型化具有指導作用,有效區分了不同空間中,與原占有人脫離時物的占有狀態,但對不同空間管理可能性的判定仍然因人而異。因此,本文認為,應在此基礎上引入對另一因素的考察,即行為人取得財物的手段。在非理想狀態下對行為人手段進行考量,對個案中行為人手段與結果之間的關聯程度進行判斷,同時比較物與占有人分離程度與行為人取得財物手段兩因素對結果發生的作用,能夠有效彌補單純考量占有狀態的不足,利于在司法實踐中對盜竊罪與侵占罪進行更加合理的界分。
二、考察行為人取得財物手段的補充作用
物與占有人分離程度與行為人取得財物手段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正如前文所述,一般盜竊罪模型下,物與占有人分離程度為零,行為人取得財物手段是行為人獲得財物占有的決定因素;反之,在侵占罪一般模型下,行為人取得財物未破壞任何人的占有,此時物與占有人的分離則是行為人取得財物的決定因素。在難以定義物的占有狀態時,將占有分離程度與行為人的取得財物手段進行比較,若物與占有人的分離程度較高,對結果的發生有決定性作用,則應認定為侵占行為,反之,若行為人的手段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則應認定為盜竊罪。
本文的觀點是在借鑒因果關系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在因果關系原理中,根據介入因素對因果進程的客觀影響加以認定,若介入因素對結果的發生具有決定性作用,則中斷行為與結果的因果關系。同理,在定罪過程中對行為人的手段與行為人取得財物的因果關系進行判斷時,考慮物與原占有人的分離程度,若財物與原占有人已經分離至對結果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程度,則應排除盜竊罪的成立,在侵占罪的犯罪構成內進行衡量。
在對占有狀態進行判斷和歸類的基礎上,對兩個因素的決定作用進行比較,優勢在于能夠使盜竊與侵占罪的界定不僅僅依賴于對占有狀態的判斷,而是借助對占有狀態進行判定與對兩種因素的決定性作用進行比較的雙重衡量規則下,對兩罪進行界定,從而使盜竊罪與侵占罪的區分更加有據可循。隨著科技的發展,行為手段體現出多元化趨勢,認定行為手段是否為導致結果發生的(下轉第40頁)(上接第41頁)決定因素,應符合社會公眾的一般價值判斷。
三、盜竊罪與侵占罪的界定與量刑規則構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在定罪階段對盜竊罪與侵占罪的區分,應首先對財物的占有狀態進行分析,根據空間環境等客觀因素確定財物有人占有與否,若能得出較為清晰的、符合社會公眾認知的結論,則根據判斷結果對行為人的行為進行性質認定。若僅通過對物的占有狀態的客觀衡量無法認定是否應為有人占有之物,則應將占有分離程度與行為人取得財物手段對結果的作用進行比較分析,最終確定二者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進而對案件性質進行認定。
在此基礎上重新對梁麗案與許霆案進行分析,不難得出以下結論:在梁麗案中,對珠寶的占有狀態進行分析可知,機場人員流動性大,在該區域中遺失的財物立即脫離原占有人的占有,同時,該區域的管理人員不具有對遺失物的管理可能性,因而不具有管理義務,該財物應判定財物為無人占有之物,在此種情況下,則應在侵占行為范疇內進行認定,沒有對行為人取得占有手段進行考察的必要;與此不同的是,在許霆案中,對行為人取得占有時ATM機中現金的占有狀態存在較大爭議,此時單純依靠對占有狀態的判斷難以得到較為清晰的結論,則應考察行為人的手段對取得財物結果的作用。在筆者看來,雖然銀行ATM機出現故障,但在ATM機故障與許霆對ATM機進行操作的手段之間,許霆的手段應是更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甚至可以認為,本案行為人是通過假意實現債權而非法取得財產的占有,ATM機的故障只是起到輔助作用。因此,對本案中行為人的行為應在盜竊罪范疇中進行認定。
占有分離程度與行為人取得財物手段在個案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對二者程度的判斷一方面決定著行為的性質,而在另一方面,對同一罪名范疇中兩個元素的量變應在量刑階段加以考量,逐步實現刑罰的輕重與物的歸屬狀態之間的同向遞進關系,進而實現個案中的實體正義。
參考文獻:
[1] 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944.
[2] 董玉庭.撿與偷的界分——以梁麗案為背景的分析[J].人民檢察,2009(17):46-49.
[3]陳興良.刑法總論精釋(第三版)[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215.
[4]郜金泰,姜瑞云,祁海霞.“許霆案”“梁麗案”的啟示:物的歸屬狀態論[J].河北學刊,2009,9(29):192-195.
責任編輯:孫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