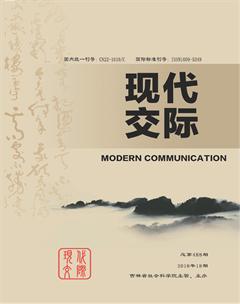行唐方言入聲字聲調實驗分析
蓋欣 郭沈青
摘要:《中國語言地圖集》依據行唐方言沒有入聲這一特點,將其劃歸為冀魯官話石濟片趙深小片。近年來一些學者卻在調查中發現,行唐方言存在入聲。本文在傳統田野調查基礎上,采用實驗語音學的方法對行唐方言聲調格局進行測定,用朱曉農的z-score歸一化方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描繪出行唐方言入聲字聲調的曲線圖,確定入聲聲調情況,為方言研究提供一種新的方法。
關鍵詞:行唐方言 入聲調 實驗語音學 調值
中圖分類號:H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8)18-0055-02
行唐縣隸屬于河北省石家莊市,位于河北省西南部,太行山東麓淺山丘陵區與華北平原的交接地帶。南距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50公里,北距北京240公里。呈西北東南向不規則的長方形狀,長53公里,寬26公里,面積1025平方公里。
行唐縣歷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有人類居住。夏商周時期分屬并州、冀州。公元前221年,秦皇一統,分天下三十六郡,南行唐縣建制,屬鋸鹿郡,治所在今故郡村。兩漢時期,稍有變動。北魏去“南”字改為行唐縣,屬恒山郡。南北朝五代十國時期,行政區域變動較大,直至后漢乾佑元年(公元948年)行唐復名。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歸河北石家莊管轄至今。目前,行唐縣下轄15個鄉鎮,總人口約44萬。
在方言劃分上,《中國語言地圖集》依據行唐方言無入聲這一特點,將其劃歸冀魯官話。但我們在調查中發現,行唐方言較為特殊,清入字未完全發生歸派,自成調類。這就與其劃片依據相違背,于是我們查閱前輩學者的調查情況,發現各家觀點也是多有不一。
最早記載行唐方言入聲問題的可追溯到1986年賀魏、錢曾怡、陳淑靜的《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方言的分區(稿)》,此文將行唐劃歸北方官話石濟片趙深小片,并且指出行唐只有平、上、去三個調類,無入聲;1993年的李藏住、劉建洲主編的《石家莊地區方言志》,記述了河北省石家莊地區其下屬十三縣市方言的綜合專門志書,是填補石家莊地區方言調查空白之作,該書明確指出:“行唐屬官話區與晉語區的過渡地帶,沒有入聲,所以劃分官話區”;劉淑學2000年在《冀魯官話的分區(稿)》也明確指出“除石家莊西郊北郊、行唐、井陘、灤縣、灤南等縣市的方言是三個聲調外,冀魯官話絕大多數縣市方言有四個聲調”,認為行唐方言不存在入聲,調類只有平上去三調;張世方在《漢語方言三調現象初探》也認為行唐入聲已全部歸派,屬于三調方言類型中的“灤縣型”。以上四種文獻調查時間較早,均認為行唐方言無入聲。
但是后期的調查都普遍認為行唐方言中入聲獨立成調。例如,王永德主編的新版《行唐縣志》記載行唐方言分為平上去入,入聲獨立成調,調值213;2001年蓋林海《行唐方言概說》中認為行唐方言存在入聲,調值為213;2005年3月蓋林海、朱懋韞、張吉格在《石家莊晉語區方言綜述》中指出:“石家莊方言的晉語區包括贊皇、元氏、井陘、平山、靈壽、行唐六個縣和鹿泉一個縣級市”,這些方言點存在入聲;2014年鄭莉《河北中南部方言聲調問題研究》指出行唐是四聲調方言,分為平上去入四調。筆者在2015年利用傳統的田野調查法,也發現行唐入聲尚未完全歸派,清入字有53.4%獨立成調,調值讀為213,與平上去三調明顯區別。
以上是我們可以搜集到的記載有關行唐方言的全部資料,我們可以看到2000年以前的記載普遍認為無入聲,但是在2000年以后學者們的調查中,均發現行唐入聲是獨立存在的。
一、實驗語音學分析
鑒于以上情況,本文采用實驗語音學方法對行唐方言的單字調進行了分析。實驗語音學方法首先用praat軟件進行基頻提取,采用朱曉農先生的z-score歸一化方法①對原始基頻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消除個體差異情況,能保證實驗結果的精確性和科學性。
本文所選例字為《漢語方言音系調查簡表》中的64個例字,錄音人共6人,其中男性4人,女性2人,年齡50歲以上的2人,40歲以上的1人,30歲以上的2人,24歲以上的1人。他們一直都是生活在行唐的本地人,對當地方言很熟悉。要求每個人把實驗的例字先讀幾遍,確保讀音穩定,錄音時每個人每字讀3遍,每個字中間間隔2~3秒鐘左右,每讀一個字為一個樣本,本次采集總的樣本為64字×6人×3遍=1152個。然后我們對這些樣本進行z-score歸一化處理。具體步驟如下:
(1)為了使所得聲調基頻曲線具有可比性, 取每個錄音有效調長的相對百分時刻點的基頻值,即音長0%,5%,10%,20%,30%,40%,50%,60%,70%,80%,90%,100%時刻點的基頻值,再把各個錄音百分時長處取基頻值求均值,所得數據如下。(見表1,限于格式,只體現一位小數)
(2)然后把上表中的基頻值轉化成對數值,得到表2。
(3)對表2中的對數值求均值?和標準差σ,注意各聲調在0%處的值舍去,降調在100%處的值也舍去,即表2中陰影部分的不用于計算,求的?=2.401132769,σ=0.069293001。
(4)把表2中的數值進行LZ歸一化處理,得到表3:
(5)根據上表數據,做聲調的絕對時長圖。(見圖1)
圖1中 T1為平聲,T2為上聲,T3為去聲,T4為入聲,縱軸為標準差,橫軸為絕對時長單位為ms。從圖1我們可以看到,入聲T4的曲線明顯是不同于平聲、上聲和去聲的,它有特定的調型和調值,是獨立存在的調類。我們用五度標調法對其進行轉化②,平聲T1調值為44,上聲T2調值為44,去聲T3調定為53,入聲T4調值為213。
以上實驗基于《漢語方言音系調查簡表》,那么行唐方言中是只有這幾個個別的入聲字保留了入聲調,還是有大規模入聲字均讀作入聲調呢?這些尚未發生歸派的入聲字在字數上是否足以讓入聲獨立呢?我們基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寫的《方言調查字表》,刪減了一些生僻字,共計選用入聲字510個,根據入聲今讀情況進行了統計和整理,發現283個清入字中151字尚讀入聲,保留率為53.4%,已發生歸派的有132字,其中24字歸入平聲,16歸入上聲,92字歸入去聲;全濁入共計111字,102字發生了歸派且基本歸派到平聲,只有9個讀為入聲字,保留率為8.1%;次濁入共計116字,有5個仍讀為入聲調,占比4.3%,其余有110字歸入去聲,占比94.8%。整體來看,次濁入歸派最快,全濁入次之,清入字歸派最慢,在調查的510個常用入聲字中,共計有165個保留入聲,入聲整體保留率為32.4%。由此,我們看到,行唐方言中讀作入聲的單字并不是個別現象,165個未發生歸派的入聲字,足以使得行唐入聲獨立成為一個調類。
二、結語
行唐方言早有人研究,但是以前都是通過傳統的人耳聽辨法得來,主觀性比較大,導致諸學者觀點不一,本文利用praat軟件對行唐方言進行精密的實驗室語音軟件分析,在調值的確定上更為客觀,為傳統語音學方法提供了一種更加準確的方言調查方法。
上述我們證明了行唐方言確實存在入聲,并且入聲獨立成調,與其他三調平行共存,聲調格局為平聲24,上聲44,去聲53,入聲213。
至此,我們不管是用傳統的田野調查法還是現代實驗語音法,都證明了行唐方言尚存在入聲,是四聲調的格局。至于早期的調查中為什么沒有發現入聲,我們猜測可能是發音人的選取上稍有偏差,前期方言調查比較粗略,可能存在疏忽,再加上早期文獻之間都相互參考,初始的調查結果被多次引用,而沒有人再對行唐方言進行過核對等等。不管怎樣,后期學者的一些調查都證明了入聲的存在,本文中,在實驗語音學方法的大量數據分析之上,所得結論也和后期學者們的觀點保持一致,所以我們認為,行唐入聲確是存在的。
注釋:
①朱曉農.語音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276.
②石鋒.北京話單字音聲調的統計分析[J].中國語文,20066(1):33-40.
參考文獻:
[1]郭沈青.陜南客伙話語音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2]蓋林海,王素貞.河北行唐方言語音概說[J].石家莊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1:9.
[3]朱曉農.語音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4]林燾,王理嘉.語音學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責任編輯:楊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