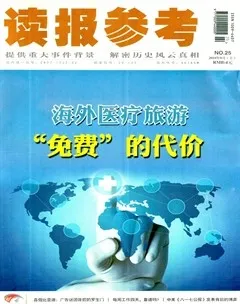“百校之父”田家炳,大愛無名
田家炳,這個來自廣東梅州、長居香港、普通話帶著客家口音的老人,比大多數人更關心內地的教育。他初中輟學,卻擁有眾多“博士”“教授”的名譽稱號。這些彰顯身份、學術和成就的稱號,放在他的身上似乎恰如其分——幾百座“田家炳大樓”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02018年7月10日,田家炳逝世,享年99歲。
在梅州大埔縣,坐上的士或電動摩托,一定不能說去“田家炳大橋”——這里共有126座田家炳大橋,它們在韓江流域依次排開,讓這塊一度只能依靠水路的“瓷土之鄉”徹底告別了擺渡過河的歷史,也結束了行人常因粗木作橋而落水淹死的慘劇。
在1978年田家炳捐資100萬港幣興建湖寮大橋(后改名田家炳大橋)前,田氏宗族已經在大埔綿延了800余年,到田家炳,已經是第18代孫。
香港皮革大王
1958年,田家炳一家來到香港。在陌生的城市里,田家炳夫婦帶著九個孩子,擠在80平方米的房子中。長子田慶先回憶:“當時只有兩三個房間,我們幾個兄弟姐妹都是上下床堆在一起住,生活看起來也比較緊張。”
田家炳開始創業,他計劃發展塑膠薄膜及人造革。田家炳找到了一塊30萬平方英尺(約2.8萬平方米)的土地,但這塊地在屯門海濱,想要利用必須先填海。香港從未有過私人填海的先例。很多人都認為這一行投資大、技術高、獲利微薄,他的行動被看成是往海里扔錢。
1960年秋,田氏塑膠廠在填海建成的土地上正式開業。投產第一年就榮獲“香港新產品獎”。田氏塑膠廠在香港站穩了腳跟,下游加工業也如田家炳預料那樣跟著發展,產品遠銷東南亞及歐美,塑膠業成為香港很大的出口行業。“香港人造革大王”的稱號自然落在了田家炳的頭上。
1982年,擁有數億家產的田家炳,從商海中隱退,把化工廠交給幾個兒子共同管理,自己專心慈善事業,捐出十多億元資產,成立“田家炳基金會”,成為了少有的“職業慈善家”。
嘗試“造血”
改革開放后,田家炳做的第一件事是建設家鄉。從田家炳大橋開始,他接連捐資興辦各類有益民生的工程,創辦醫院、電視臺、電視廣播中心、少年宮、婦幼中心、輪渡碼頭、水電站等民生項目,捐助幼兒所、小學、初中、高中、職業學校、衛生學校、電視大學等學校。
田家炳對家鄉的要求盡量滿足,為了配合家鄉建設,甚至同意遷移祖墳。1992年,田家炳的侄孫田玲發時任村委書記,負責每年大年初一給田家炳拜年以及轉達村內需求。這年他代村民提出希望田家炳將鄉道修繕完成。按照田家炳的計劃,鄉道將按兩次分批修建。接到電話后,田家炳要了一份計劃書,完成了鄉道建設。田玲發說:“銀灘村兩公里的鄉道,除了一位印尼華僑建設的200米,都是田家炳出資建成的。他說話算數,你要多少他就給多少,但超出的部分由我們承擔。”比起捐助實體的項目,田家炳更希望村民能夠自強不息,讓他可以從“輸血”變成“造血”。
田家炳幾乎貢獻了大埔縣大部分的基礎建設,其中包括6條公路、23所醫院、33所學校和126座橋,這些工程星羅棋布,遍及大埔城鄉內外。大埔縣政府決定,從1991年開始,每年舉行一次田家炳系列工程落成和奠基典禮。現任大埔縣政府新聞秘書劉招迎曾是列隊中的一員。據他回憶,在田家炳參與的幾次慶典中,都有數萬群眾夾道歡迎。
“校長在哪里”
戴希立去仁愛堂田家炳中學面試校長時不過三十多歲,他提出“學生為本,教師治校”,得到當時校監田慶先的支持,將他選為仁愛堂第一任校長。這也成為他與田家交往的開始。
在通信中,田家炳與戴希立達成了“己立立人”的共識,并將此作為仁愛堂的校訓。第一次見面,田家炳帶全家人訪問學校。在校門拍照時,由家炳讓家人把位置空出來,“第一張留給我跟校長。”戴希立嚇了一跳。
很快他發現,對于校長和老師,田家炳十分尊重且重視。在內地,學校剪彩都是領導參與,校長很少安排位置,能夠擔任司儀已經非常難得。而田家炳每次都會問:“校長在哪里?”不但安排座位,還一定要校長上臺參加剪彩。但看到學校施工圖校長辦公室過大時,田家炳又會提出,“留出更多的空間給老師和學生。”“他會覺得你是領導,你應該做個榜樣。其實他非常簡單,三句話:中國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關鍵在校長和老師;德育為先。他很清晰,一直堅持。”戴希立說。
師范院校也是田家炳重點捐助的部分。他認為“要辦好教育,必須要有好的老師。師范大學是培育教師的重要基地。”1995年,他向四川、東北、華中、山東、南京的五所師范大學與杭州大學各捐資800萬創建田家炳教育學院/書院,又向山西、西南、云南、貴州、廣西、江西的六所師范大學,以及廣東省的惠州大學與嘉應大學(后都改稱學院)等八校共捐4800萬元。
1999年,各省市師范大學熱情推薦、重點中學慕名申請資助,還有學校自愿減少資助金額,接受撥款時間向后延伸,但務求加入田家炳中學的行列,以提高學校的知名度。當時,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香港房地產市價較高峰期下跌過半,但田家炳居住的大宅外觀不俗,保養適宜。這套豪宅位于香港九龍塘高尚住宅區,面積超過700平方米,帶有游泳池、私家花園和運動場等,田家炳在此已度過了37個生日。據地產公司估算,可賣過5000萬港幣。按照田家炳的計劃,能夠資助二十余所中學。為了恪守捐資承諾,他和家人商量后,決定賣掉房子。在洽談過程中,對方得知了田家炳賣房是為了助學,還多付了300萬港幣的房款,最終以5600萬成交。
2005年,為增加資金擴大捐資,田家炳將13萬平方米、24層的田氏廣場售出,得款近3億元,為數十所大學、中學提前付清捐款。如今,國內39所師范大學里面,都有一個“田家炳書院/學院”。類似的教學樓,在全國各地的大學里面,共有九十多棟,加上他捐建的中學166所、小學44所,它們都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田家炳。田家炳也因此被稱為“中國百校之父”。
“捐我的生活費”
田榮先懷疑過父親到底是節儉還是吝嗇,“以他的身家財富,根本不應該活得這么寒酸,為什么他老是怕過分享受,怕寵壞自己,自約得近乎自虐?及后才體會,吝嗇的小人是省自己的錢而慷他人之慨,絕不會像父親那樣,連賓館里的肥皂、抹手紙、蒸餾水或電源都替人家珍惜。長大以后,看見父親傾囊為善的義舉,更深深敬佩他薄己厚人、坦蕩無私的情操。”
田家炳將基金會交由社會人士參與、自任名譽主席后,仍會參與捐助項目的討論。他沒有決定權,但每次總堅持“都要捐一點”。如果基金會不批準,他就會說:“捐我的生活費,我不需要這么多。”“在一些人眼中,我不會用錢。但我想我是很會用錢的人,我在家鄉、祖國大陸、香港,無論是捐校舍、蓋醫院、造橋,都是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田家炳不喜出門遠行,又起臥有序、作息定時,最怕出門打亂生活規律。但為了多去鼓勵關懷受捐助的單位,他幾乎每年都會到各地院校拜訪。又因為怕打擾對方,行程總安排緊湊。以2006年9月的行程為例,他只有7天在香港,余下時間奔赴了13個城市。幾個陪同的兒子都吃不消,接班輪流陪他,他卻莫名興奮。
在田家炳看來,以“田家炳”命名學校,是因為田家炳有些事可以影響到一部分人,或者大家共同研究怎么發揚這種精神。“我要達到這種目標,首先要真正把學校辦好,辦不好不但沒有給我光榮,反而丑化了田家炳。家長就會說,我們兒女千萬不要送到田家炳學校去念書。這樣我就會覺得不知道怎么報答大家對我的愛護與熱情。我很希望確確實實把學校辦好,不要辜負大家厚愛。”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