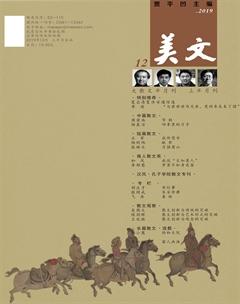四季里的日子
楊晨潔
周榮池在《節刻》中以溫情的方式重新定義著不同節氣的意義,他是一位站在生活根子上的本色作家,他的散文描繪著生活于土地上的人,解讀著農人對生活的智慧,詮釋著人何以承擔熬過漫長的日子,訴說著四季輪回以及那些平淡卻又踏實的存在。周榮池以在場的言說,個體的疼痛與感知摯誠地書寫著故土與生活。“南角墩”是周榮池散文世界的解碼口,“四季”是他在《節刻》中堅守的秩序,他始終不曾離開過佇立的南角墩,南角墩的四季輪回繪制著周榮池最初的精神圖景。
逝水無聲,流年暗中轉換。南角墩的節刻是樸實的,每一個日子都兼具獨特與俗常的雙重特性,除夕叫三十晚上,元宵叫正月十五,中元節叫七月半,中秋節就叫做八月半,都只是按照所處的時間位置給予節日最簡單的定義。節日的意義在南角墩并不顯著,村莊按照自然的秩序隨著地球的自傳安然地進行著,古老樸素的南角墩憑著時間的刻度在周榮池的筆下復蘇,并逐漸鮮活。周榮池以溫情的筆觸,寫南角墩的草木植物,寫那里的興衰與死亡。草木蟲魚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共同遵守著日子的節奏,互相扶持著前進。周榮池一直細膩地處理著呈現在文本中的生活,他極力營造一種在場感,輔以各類大小事件給文字以恰當的溫度和濕度。母親每日倔強地擔水,打春后耐心準備酥土,清明前后種瓜點豆,端午時節親手制作白粽,這些細碎的生活情境被周榮池一一納入自己對時節的書寫,并在其中添加豐富的情感因子,秋收時節的疲憊與忙碌,插秧日子里專屬女人手中的溫情,在火紅的日頭落下后吐露一句對生活煽情的感謝,或者還有將撿拾的棉花做成新被胎的欣喜,這些豐富的感情使每一個時刻都不再是寡淡的時間點,都在不同的情感層面上與活生生的日子產生了溫暖的共鳴。周榮池尋覓的正是此種方式,他的散文因此獲得了一種呼吸感。周榮池發現了勞作人們在平淡日子里的精神弧光,他們堅韌、沉默、踏實并執著,他們遵守著四季的規矩,也在不經意地越軌中遭到放逐,也由此,周榮池確認了他所關注到“放逐”與“秩序”。
在周榮池的文學世界中存在著“放逐”的潛臺詞,而“放逐”的背后暗含“秩序”。另一篇——《河流》將這種放逐演繹至極致,勞作的人們在河流、村莊的秩序之外被放逐,遂成為一名離開者。這種放逐不僅細微到周榮池代表的每一個個體,亦可放大至一座村莊,一段歷史。可以說,在放逐與秩序之間,周榮池為自己的寫作標好了方向。甚至在這兩種悖反的力量之間,周榮池建立起了屬于他自己的,關于世界與語言的敏感通道。散文賦予周榮池書寫“我”的自由,而在自由之外,周榮池崇敬“秩序”。“秩序”作為一種四季輪回的力量,在周榮池的筆下被認真對待。周榮池深知大自然的力量,他也洞見了自然法則的精神,這直接關乎工業文明深入過程中日漸丟失的對自然的敬畏。周榮池將自然規律或自然法則作為整體性思維貫穿至其散文創作的始終,他在自己的文學世界中無數次確認勞作人民對太陽和土地的虔誠,肯定四季輪回是自然中真實有力的秩序,春去秋來,夏收冬藏,生長與凋零相繼出現,村莊與太陽同醒共眠,世界和他的勞作將一如既往。南角墩的秩序就建立對節刻的尊重,給每一個節刻應該有的樣子。
周榮池以一種頗具靈性的方式深入探究南角墩的四季輪回,場景與場景之間的轉折過渡平和而又自然。如此的筆法下,周榮池的散文呈現出了更為豐富的闡釋空間,他以自己的價值判斷和審美趣味,將生死衰敗作為書寫的最大立足點,解構重塑著南角墩的生活。追憶之中,周榮池體悟著生活,也認識了自己。這其中透露著他的審美情結,貫穿著一種傳統文化繼承下來的審美精神,以感情的潤澤,將這種傳統的精神與每一個時代中的個體諧振。生活與藝術的關系,最終都將落腳至作家與生存的個性環境的關系,以故鄉風物為寄托的依戀才會產生真實的生命體驗,才能給人以真實的審美體驗。周榮池以回憶性的在場寫作,賦予南角墩的四季以全新的生命,將四季與農人的生活互動完整呈現。周榮池很少有封閉的自我喃喃呢,也絕少旖綺的辭藻附麗,他以平實的語言重抵現場,以根植于生活層面去尋找個人化書寫的飛躍。周榮池的散文書寫始終與生活有著強烈的貼近性,他提醒著我們,文學的功能之一便是呈現那些被日常生活遮蔽的意義。周榮池明白文字不再與靈魂共鳴,寫作就失去了對話的力量。因此,周榮池始終以沉入生活的底部的方式回歸歷史的深處,他口中淺吟的南角墩如同蕭紅筆下的呼蘭河,沈從文文集里的邊城又或者蘆焚喃喃自語的果園城,都是精神地圖中的標紅點。生活的水岸滋養著周榮池的創作,深深的鄉戀情結落腳到實在的“日子”,而這也最終成就了周榮池獨一無二的審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