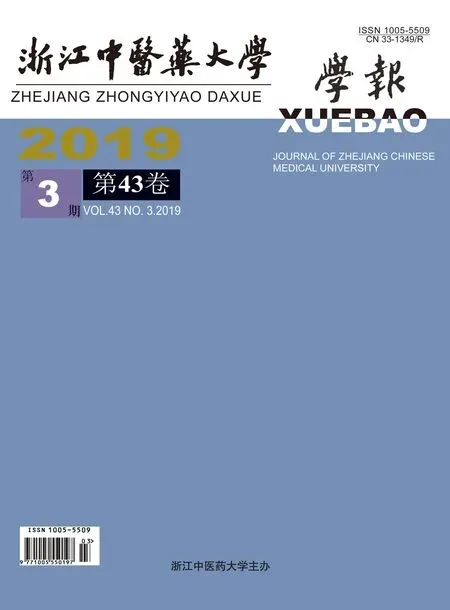基于《保嬰撮要》淺析薛氏父子疳證論治特色
張春輝王雅琴陳鑫麗張俊杰
1.浙江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杭州 310053 2.浙江中醫藥大學
疳證在小兒疾病中占有一定比重,為小兒四大證“痘麻驚疳”之一。“疳”字最早出現于《諸病源候論》中,但主要是指一類慢性消耗性疾病,并非兒科專有名詞,至宋代,疳證逐漸分離成為小兒專有病名[1]。錢乙[2]16《小兒藥證直訣》言“疳皆脾胃病,亡津液之所作也”。即疳證,是因小兒脾胃受損,氣液耗傷而形成的一種慢性病證,其主要表現為形體消瘦、面黃發枯等特征。
薛鎧、薛己父子二人均為明朝江蘇名醫,尤在兒科、外科方面見長。《保嬰撮要》便是由薛氏父子二人合著而成的兒科巨著,其內容豐富,采擷各家醫論,父作子繼,成書時薛己已年近七十,學術思想成熟,臨床經驗頗豐,值得后世對其整理鉆研。全書共二十卷,包含小兒疾病的病因、病機及治則,更附有大量醫案及方藥治法,其中關于小兒疳證的醫案數量達六十余例,具有較高的臨床參考價值。現將其治療小兒疳證的學術思想略作整理,以饗同道。
1 辨明五臟為要
小兒疳證病癥眾多,或煩渴,或泄瀉,或潮熱往來,又或頭面手足浮腫。盡管疳證癥狀多樣,但薛氏父子認為辨證要點不出于五臟。錢乙[2]16-17根據病變五臟不同將疳證分為肝疳、心疳、脾疳、腎疳、肺疳,但又有筋疳、骨疳及冷熱肥瘦之分,而薛氏父子將其歸納,并入五臟疳證之中,即五疳。
1.1 肝疳 肝屬風,故肝疳又有風疳之名,其在竅為目,因此肝疳多以雙目癥狀為主,出現赤腫、發癢或生白翳。《內經》提到:“諸風掉眩,皆屬于肝。”故小兒肝疳可伴有頭搖目剳。剳,即“眨”,即小兒不由自主頻繁眨眼。又有“筋疳,瀉血而瘦”[2]16,《證治準繩·雜病》中認為肝風傳于腸胃,能夠出現下血癥狀,因此筋疳同樣屬于肝疳范疇[3]。疳證以虛為主,故肝疳常有肝經血虛風熱,但薛氏父子[4]207于醫案中提及“若肝經濕熱,兼用瀉青丸”,因此不可忽視存在肝經虛中夾實的情況。
1.2 心疳 心屬火,因此心疳常常伴有發熱癥狀,如頰赤或身體壯熱。但疳證常有熱,除身體發熱,還可出現瘡疥或口瘡。薛氏父子[4]126于發熱癥中指出:“小兒之熱,有心、肝、脾、肺、腎五臟之不同。”心主藏神,因此心疳之證除發熱頰赤之外,更為突出的是有睡中驚悸的癥狀。錢乙[2]2有云:“心主驚……虛則困臥,驚悸不安。”
1.3 脾疳 脾疳,又稱為肥疳,癥狀大多為肢體黃瘦,皮膚干澀,常有瘡疥。小兒疳證病因有三,一為病后脾胃虧損,二為用藥過傷,三為飲食起居失宜。或津液內亡、虛火妄動,或膏粱積熱,傳化不能,因此所生瘡疥之火,仍有虛實之分。盡管原因多種但最終損傷脾胃,脾主肌肉,脾胃受損,脾失健運,則肌體黃瘦,皮膚干澀。同時水谷運化失常,或停積宿滯,或腸鳴瀉下,故常有疳痢、疳瀉等癥狀。
1.4 肺疳 肺主呼吸,因此肺疳常有喘嗽不已,故又稱氣疳。同時肺開竅于鼻,肺疳有熱生瘡多在鼻部。《保嬰撮要·作喘》中提到:“喘急之癥……有因膏粱積熱熏蒸清道者。”[4]151小兒飲食不加節制,過度進食肥甘厚味,導致脾胃積滯生熱,從而傳于肺經,出現作喘。因此,肺疳之熱與脾胃積熱亦有很大聯系,在清肺熱的同時不可忘記瀉脾胃積熱。
1.5 腎疳 腎在體為骨,因此腎疳又有骨疳之稱,肢體常瘦削。同時《醫宗金鑒》于腎疳篇中指出,“患此疳者,初必有解顱、鶴膝、齒遲、行遲、腎氣不足等證”[5]。小兒若為腎疳,則其先天稟賦必然有所不足。加上小兒疳證后期津液虧損嚴重,必當損及腎陰,腎虛受熱,故常有潮熱往來、五心煩熱、盜汗骨蒸。同時齒為骨之余,疳火上炎,則有口臭齒黑甚至齦爛牙宣。
2 調養脾胃為主
薛氏父子[4]223指出“小兒雖得乳食,水谷之氣未全,尤仗胃氣”,因此脾胃功能對于小兒生長極為重要。但因小兒生理特點,其脾胃常為不足,加之若有用藥過傷或飲食不節等原因,小兒脾胃更易虧損而導致其功能失常。疳者,干也,脾胃虛弱,津液生化不足,或輸布失常,從而影響其他臟腑正常生理功能。因此雖疳證有五疳之分,但脾胃失調仍為其主要病機。薛氏父子[4]206于疳證治法中表明“在小兒為五疳,在大人為五勞,總以調補胃氣為主”。
2.1 脾胃積熱 小兒嗜食甘肥之物,飲食不加節制,導致傳化失常,膏粱厚味積聚于胃而生熱。膏粱積熱,脾胃積滯,功能不調,故其運化失常,出現腹脹、嘔吐或者不食等癥狀。加之火熱陽邪,其性炎上,積熱循經而上于口舌,則口舌生瘡,甚者損害牙齦。同時,脾氣不調導致清濁不分,加上濕熱下注,小便常出現微赤或白濁。薛氏父子常以四味肥兒丸,即黃連、蕪荑、神曲、麥芽等分糊丸,予以治療。神曲、麥芽消食健脾,蕪荑行氣消積,黃連清熱,尤宜用于治療食積脾疳。若有精神倦怠、發稀如穗等脾疳嚴重者,常加陳皮、川楝子二藥以增行氣之效,即六味肥兒丸。
2.2 脾胃氣虛 “小兒諸疳,皆因病后脾胃虧損”[4]205,若胃氣虛弱損及脾土,則出現飲食少思或食而難化,同時會有作嘔作泄等癥狀,此時薛氏父子常用四君子湯以益氣健脾。若伴有疳腫者,虛中有積,肚腹緊脹,脾復受濕會出現頭面手足虛浮,此時六君子湯更宜,即四君子加陳皮、半夏以燥濕化痰。然若非痰濕重者,薛氏父子更喜用五味異功散以益中州之氣。小兒脾胃易滯,若單純補益則會出現“虛不受補”的情況,四君子湯加上陳皮,可行氣化滯、醒脾助運,以達到“補而不滯”。另一方面,薛氏父子[4]286指出異功散可治“虛熱上攻,口舌生瘡”,認為“諸疳瘡疥,因脾胃虧損,內亡津液,虛火妄動”,若伴腹脹或泄瀉,則為脾經之癥,常用五味異功散以補脾土。
2.3 元氣虧損 小兒易虛易實,其發熱作渴,必須辨明虛實。若為脾胃氣虛而導致的虛熱,常用補中益氣湯以治氣虛發熱,但若誤以為實,更用冷藥,用藥過傷,則加重脾胃虧損并耗失大量津液,從而形成疳證。對于此類情況,薛氏父子更用補中益氣湯予以治療。二人認為因久病或過服克伐之劑而導致元氣虧損,有畏寒發熱,飲食少思等癥狀或其他虛證表現,最宜用補中益氣湯。因此,對于久病成疳或用藥過傷成疳,薛氏父子以補中益氣湯為首選。
3 固本治疳并重
縱觀全書薛氏父子治療疳證相關醫案,單用一方的案例較少,多以二方或及以上配合治療。盡管造成小兒疳證的病因多種,然總歸結于小兒脾胃受損、津液虧損,甚者則損耗腎陰,故治療常以固后天或先天之本為首要,同時針對其疳證主要表現癥狀進行用藥治療,即“治疳”。因此,薛氏父子治療小兒疳證多標本同治,固本與治疳并重。
五臟有虛實,治疳分補瀉。薛氏父子指出治療疳證以辨明五臟為要的同時,需審其勝負虛實,不可妄瀉。疳證初起,皆因脾胃失調,故需調養后天之本。乳食失調,脾胃積熱,常用肥兒丸,但積滯過久,損傷脾胃,則需以肥兒丸治脾疳,以異功散生脾土。若積熱上炎于肺,則有作喘、口鼻生瘡,故以清肺飲治肺,但日久肺虛,亦不能忘補脾以“培土生金”。脾虛日久,化源不足,則心失所養,常有睡中驚悸,故以安神丸治心,異功散補脾。
脾胃積滯,傳熱于肝經,則有兩目赤腫或腦后有核,應用蘆薈丸或瀉青丸清肝熱,佐肥兒丸消脾胃積滯。但若久病肝虛,薛氏父子則多以補腎為主。書中提到“肝疳,用地黃丸以生腎”[4]206,薛氏父子認為若肝經血虛,應考慮滋補腎陰先于補脾,滋腎水以生肝木。雖薛氏父子重視脾胃,但并沒有忽視先天之本的重要性,何況六味地黃丸雖以滋補腎陰為主,但兼補肝脾,故治療肝疳需考慮使用六味地黃丸以“固本”。
同時就腎疳而言,先天之本必有受損,僅僅補脾恐有不足,因此常以地黃丸為主。然針對疳證特點,薛氏父子又用九味地黃丸,即六味地黃丸減白茯苓、澤瀉,加赤茯苓、川楝子、當歸、川芎、使君子。清代黃庭鏡[6]于《目經大成》中指出疳證必然有“蟲”,為風木所化,其認為換白茯苓為赤茯苓,加川芎、當歸、川楝子、使君子,皆用來直瀉厥陰,亦為“肝腎同治”之法。同時因疳證本就津液虧損,腎不宜再泄,故去澤瀉。《醫林纂要》將其稱為使君子地黃丸,認為腎疳瘡疥多因血澀而燥,宜用當歸滋之[7]。從中亦可窺見薛氏父子以固本與治疳并重的治療原則。
4 結語
當今社會雖然人們的物質供給已極大豐富,然而家長照顧小兒仍存在許多誤區,如過早或過晚添加輔食、輔食種類的不恰當又或是隔代喂養,小兒脾胃柔弱容易受損,造成消化功能紊亂,加之家長重視程度不夠,從而形成疳證[8]。薛鎧、薛己父子二人繼承前人治療小兒疳證的學術思想,并融入自己的理解和臨證經驗,認為小兒疳證辨證要點仍以五臟為主。又根據小兒疳證脾胃失調的特點,提出治療重點在于調補脾胃,靈活運用肥兒丸、四君子湯及補中益氣湯三方,同時不忘“肝腎同治”以及滋補腎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薛氏父子指出治療小兒疳證補母需與治疳并重,即標本兼治,應結合癥狀病程靈活組合或加減治疳藥。薛氏父子論治小兒疳證頗具特色,對當今臨證治療現代小兒疳證仍有重要啟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