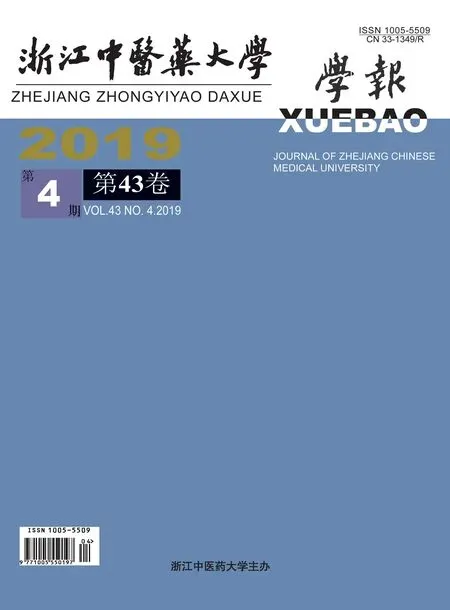徐陸周治療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臨床經驗總結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 南京 210029
腸易激綜合征是以腹痛(或腹部不適),伴排便頻率及形狀異常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種功能性腸病,病程大于6個月,且診斷前3個月內該癥狀持續存在[1]。羅馬Ⅳ標準將其分為腹瀉型、便秘型、混合型及不確定型[2]。近年來,隨著生活環境及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該病的發生率逐年升高,嚴重影響人們的工作和生活。西藥對于腸易激綜合征的治療以對癥處理為主,如止痛、止瀉、抗焦慮等,無法根治,而祖國醫學在該病的治療中展現出了巨大的優勢。雖然歷代古籍中對該病沒有獨立的病名記載,但根據臨床癥狀,可將其歸于“腹痛”“泄瀉”等范疇。臨證過程中,運用中醫藥治療不僅可以有效地改善相關不適癥狀,更能夠審證求因,辨證論治,標本兼顧,以呈陰平陽秘之態,疾病乃愈。
徐陸周教授系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江蘇省中醫院主任中醫師,師從國醫大師徐景藩教授及全國名中醫劉沈林、單兆偉教授,集孟河醫派、吳門醫派學術思想之大成。徐師從事臨床工作二十余年,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對內科疾病,尤其是胃腸道疾病的診治有著獨到的見解。徐師認為,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發病基礎在于脾虛,臨證時又以脾氣虛和脾陽虛最為多見,故而補脾氣、溫脾陽當為該病的基本治療原則,并貫穿于該病治療的始末。其次,在疾病發展的不同階段,應根據其不同的臨床表現,分清機體寒熱的輕重,牽涉臟腑功能的強弱變化,四診合參,隨證加減。因此,徐師提出應以健脾化濕為主,佐以疏肝理氣、溫腎祛風的治療大法,臨證之時,標本兼治,療效顯著。筆者有幸跟師學習,收獲頗豐,現將徐師治療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相關經驗總結歸納如下,以饗同道。
1 病因病機
根據患者的臨床癥狀特點,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可歸于“泄瀉”“腹痛”“郁證”等范疇,其病因主要與感受外邪、飲食不潔、情志失調及先天稟賦不足等有關,其病位在腸,但與脾(胃)、肝、腎等臟腑關系密切。徐師認為,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發病的前驅期,腸道一定存在慢性感染,感染遷延,日久難愈。現代醫學表明,胃腸道的感染以其黏膜充血水腫為主要病理改變,結合中醫學理論,這與濕熱致病最為相似,故徐師認為,在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發病的初期,濕熱之邪為其主要致病因素。脾喜燥惡濕,濕性黏滯,易阻滯氣機;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脾氣虧虛成為疾病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礎。脾運失健,運化失常,清氣不升,濁陰不降,水走腸間而致泄瀉。當代之人,飲食不潔,過食瓜果、生冷,形寒喜涼,寒從中生,脾陽為之所傷,以致脾陽虧虛,此時多以寒濕之邪為主要病理因素,或夾有濕熱,以成寒熱錯雜之證。肝脾同居中焦,土虛木乘,則見脾虛肝旺之證,貫穿疾病始末;若因疾病憂思,情志不舒,肝氣郁結,失于疏泄,橫逆乘脾,則進一步加重脾虛。疾病日久,脾陽虧虛損及腎陽,命門火衰,水谷不化,疾病遷延不愈,以成虛實夾雜之態。此外,徐師總結多年的臨證經驗發現,風邪存在于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病程的任何階段。風性開泄數變,善動不居,行無定所;風邪為病,發病急驟,變化無常,這均與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發作不定、時有反復的特點相類似。風為百病之長,合于寒則為風寒之邪,合于熱則為風熱之邪,合為濕則為風濕之邪,合為暑則為暑風。風邪為病,衛外不固,腠理開泄,外邪直中腸腑,小腸失清、大腸失化,水谷合污而下發為泄瀉。
2 治則治法
徐師認為,對于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治療當分期而為,依據發病的時間長短及臨床表現,常將其分為前驅期和初期、中期、后期,這也符合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疾病發展的規律。此外,對于風邪的辨治當貫穿于疾病始終,“祛風”之法不可或缺。
2.1 清熱化濕,健脾助運 徐師認為,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初期由前驅期發展而來,對于前驅期的認識,可以參考其西醫的診斷標準,在未明確診斷之前,均可以稱為前驅期。在前驅期和初期的發病過程中,濕熱這一因素扮演著關鍵角色,此時機體邪盛而正衰不顯,當以驅邪為要,故當以清熱化濕,輔以健脾助運。
《內經》有云:“濕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佐以咸甘,以苦平之。”苦能燥濕,寒可清熱,故治療濕熱之邪,當以苦寒之藥為主。徐師在這一類藥物的選擇上,喜用黃連、黃芩,但苦寒敗胃,故用量以適度為宜,黃連之用量為2g,黃芩為6g,同時佐以薏苡仁、車前子等性涼滲濕之味,薏苡仁甘補淡滲,滲除脾濕、健脾止瀉;車前子性甘偏寒,清熱利尿通淋,“利小便以實大便”,尤善治療大便水樣兼小便不利者。二者合用,再配伍茯苓、葛根等利水滲濕、升清止瀉之味,對于濕熱之邪的清利,可謂藥到證安。在健脾之藥的選擇上,徐師喜用炒白術、淮山藥等藥性平和之品,而慎用味厚性烈之物,以防攻伐脾胃之氣。《本草匯言》曰:“白術乃扶植脾胃、散濕除痹、消食除痞之要藥也,脾虛不健,術能補之,胃虛不納,術能助之。”[3]白術益氣健脾,溫而不燥,被譽為“脾臟補氣健脾第一要藥”[4]。且炒白術更長于止瀉,與淮山藥等聯用,共奏補脾益氣之功。對于炒白術的用量,藥典以6~12g為宜,然徐師在臨證時發現,對于脾虛較盛者,炒白術當超藥典使用,20g為常規用量,既能增加健脾益氣之功,又不至于耗傷陰液。
2.2 溫陽健脾,調和土木 徐師認為,若疾病于初期未予及時治療,或是失治誤治,或是受病之人仍飲食不潔,過食瓜果、生冷,形寒喜涼,則致病情進一步加重,發展到疾病的中期階段。此時濕濁未盡,寒從中生,脾陽乃傷,運化無權,又土虛木賊,但只因肝氣較脾氣偏旺,而肝木無明顯亢盛,故無明顯肝氣乘脾之證。此時機體邪不盛而正氣偏衰,以成寒濕困脾、脾陽虧虛、土虛木賊之候,故該期的治療當溫陽健脾、調和土木。
《脾胃論·脾胃勝衰論》載:“……脾胃不足之源,乃陽氣不足,陰氣有余……”[5]3可見脾陽乃運化之根。在溫煦脾陽方面,徐師擅用干姜、肉豆蔻。古籍中對于干姜的記載始于《神農本草經》,在其中被列為中品,后世醫家對干姜運用最廣的當屬仲景,其在《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運用干姜的方子多達40余首。干姜性溫熱,歸脾、胃、腎經,“能走能守”,暖脾醒脾之力強,同時兼有溫腎陽之功效,為脾腎陽虛證之要藥。肉豆蔻辛溫而澀,歸脾胃、大腸經,既能暖脾,又能固腸,溫中理脾、行氣止痛,與干姜相須為用,溫脾之力益甚。在溫化寒濕方面,徐師常選用石菖蒲、陳皮、半夏等辛溫健脾之品,石菖蒲辛開苦燥,芳香走竄,化濕醒脾開胃;陳皮溫通苦燥,辛香走竄,有行氣燥濕之功;半夏入脾胃經,善燥化中焦痰濕。三者合用,再配伍木香、烏藥等溫中行氣、寬中止痛之品,對于寒濕之邪的溫化效果甚佳。在調和土木方面,因肝氣無明顯偏盛,氣郁本經,當以疏肝調氣為主,徐師常選用佛手、香櫞皮、玫瑰花之品。佛手辛苦性溫,既可疏肝理氣,又能燥濕健脾;香櫞皮氣香醒脾,既能疏肝解郁,又可理氣寬胸;玫瑰花芳香行氣,既能行氣疏肝,又可醒脾和胃。此類藥物性多偏溫,不會過于溫燥,故無溫燥傷陰之憂。疏肝而不伐肝,又可健脾理氣和胃,在該病中期的治療中甚為佳選。
2.3 溫腎助陽,養肝柔肝 隨著疾病的進一步發展,脾虛日益加重,泄瀉、腹痛頻作,焦慮愁思,又逢工作、生活之壓力等,肝木失于調達,肝氣郁結,橫逆犯土。此時肝郁明顯,肝木亢盛,當與中期之土虛木乘相區別。同時,脾陽虧虛累及腎陽,導致腎陽虧虛,無以溫煦。故徐師認為,在該病后期的治療,應重視溫腎助陽、養肝柔肝。
葉天士[6]在《臨證指南醫案》中云:“經旨謂肝為剛臟,非柔潤不能調和也。”故當肝旺克脾,徐師常選用白芍、烏梅等柔肝養肝之品。白芍味酸苦,主入肝經,補益肝之陰血;烏梅味酸入肝,酸收斂肝、柔肝緩急。二者相須為用,共奏平肝抑陽之效。此即《本草求真》所云:“氣之盛者,必賴酸為之收……肝氣既收,則木不克土……”[7]對于久病及腎的患者,徐師常用補骨脂、吳茱萸等辛溫性熱之品。補骨脂歸于腎、脾兩經,既可溫腎助陽,又可溫脾止瀉;吳茱萸性大熱,溫陽之力更甚。二者聯用,再佐以附子、肉桂等益火暖土,則命門之火得以補益,脾陽亦得以溫煦,寒濕之邪則無以為怪。
2.4 升舉清陽,祛風除邪 徐師認為,在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疾病進程中,風邪是客觀存在的,且與其他外邪交錯成患,以致疾病復雜多變,遷延難愈,故在辨治該病之時,均當兼以升舉清陽、祛風除邪。
風邪為病,必取“風藥”治之。李東垣[5]15-18在《脾胃論》中最早提出“風藥”的概念。風藥其性味多辛溫,具有“辛、散、動、竄”等特點,能發揮“辛散、燥濕、祛風”之功效。《先醒齋醫學廣筆記·泄瀉》曰:“長夏濕熱令行,又歲濕太過,民多病泄。當專以風藥,如羌活、防風、升麻、柴胡、白芷之屬,必二三劑,緣風能勝濕故也。”[8]《醫碥》云:“泄瀉因于濕者,治濕宜利小便。若氣虛下陷而利之,是降而又降也,當升其陽所謂下者舉之也。升陽用風藥,風藥又能勝濕。”[9]《血證論·臟腑病機論》所云:“木之性主乎疏泄。食氣入胃,全賴肝木之氣以疏泄之,則水谷乃化。設肝不能疏泄水谷,滲泄中滿之證在所難免。”[10]故而風藥在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中發揮的作用,不外乎健脾滲濕、升舉清陽、疏肝理氣三點。臨證選藥,以“風藥之潤劑”——防風當為首選。防風辛、甘微溫,歸膀胱、肝脾經,具有升清燥濕之性。膀胱經藥,包括羌活、藁本,均能升舉清陽,使得濕邪從表而走,健脾滲濕之力強;同時又入肝經,長于疏肝理氣、息風止痙。臨證時,常配伍柴胡、升麻等,共同發揮升清、健脾、疏肝之功效。
此外,徐師認為祖國醫學中的“腸風”與西方醫學中的“腸動力異常”“腸道敏感性增加”具有相似之處。研究表明,腸道敏感性的增加是腸易激綜合征的病因之一[11]。馬祥雪等[12]認為,腸黏膜中肥大細胞活化后脫顆粒,是導致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腸道敏感性增加的重要因素。吳賢波等[13]研究表明,防風-烏梅藥對可抑制肥大細胞脫顆粒,減少組胺的釋放,下調肥大細胞蛋白酶激活受體-2(protease-activated receptor-2,PAR-2)表達,從而發揮抗過敏作用。藥理研究表明,粗柴胡皂苷對5-羥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組胺及醋酸引起的腸道血管通透性增加有著抑制作用[14]。還有研究證實,升麻具有抗炎、鎮痛的作用[15]。所以,防風、柴胡、升麻在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治療中療效肯定,其可能的作用機制在于抑制肥大細胞活化,降低腸道高敏感性和腸道血管通透性以及抗炎、鎮痛等。可見,風藥在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治療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3 驗案舉例
薛某,男,41歲,個體經營者,2018年6月7日初診。主訴:痛瀉間作2年余。病史:2年前,患者因夏季外出歸來熱甚,食冰箱所藏半個西瓜,并大飲涼水,致患泄瀉,每日4~5次,痛則欲泄,泄后痛減。服用“左氧氟沙星膠囊”“黃連素片”等,病情好轉,遷延數月方愈。其后,每感受外寒或飲食生冷,泄瀉則發,水樣便日行3~6次;每逢情緒焦慮、緊張之時,泄瀉亦作。刻下:腹痛腸鳴時作,痛后便解則緩,得溫則舒,腹部按之不痛,面色欠澤,疲勞乏力,四肢欠溫,舌質淡胖,有齒痕,苔白膩,左脈沉滑,右脈沉細。輔助檢查:結腸鏡檢查,所見結直腸未見明顯異常;糞檢常規示,未見明顯異常。徐師四診合參,考慮本病為寒濕阻遏、脾腎陽虛、肝脾不調,發為泄瀉。治法:健脾化濕、溫補脾腎、疏肝理氣、祛風止瀉。以自擬方“白石溫脾湯”加減,處方:炒白術20g,干姜10g,肉豆蔻10g,淮山藥 30g,石菖蒲 10g,炒薏仁 15g,木香 10g,烏藥 10g,吳茱萸 4g,補骨脂 10g,防風 10g,升麻 10g,芡實 10g,烏梅10g。共14劑,水煎服,早晚頓服。
2018年6月21日二診:患者腹痛明顯改善,大便次數減少,日行3次左右,質稀,腹寒肢冷好轉。原方改干姜為6g,吳茱萸為2g,再服14劑。
2018年7月5日三診:患者大便尚成行,日行1~2次,腹痛未作,體重稍有增加。故守方化裁再服藥30余劑,近期隨訪,諸證尚安。
按語:患者以“痛瀉間作2年余”就診,結直腸鏡檢查未見明顯異常,且其近期來癥狀反復發作,據此符合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診斷標準。患者2年前有急性胃腸炎的感染史,服用抗生素等藥物后,雖病情好轉,但脾胃乃傷,此時正處于上文所述的前驅期,常于感受外寒或飲食生冷時發病,此為寒濕阻遏,脾陽虧虛,運化無權,清陽不升,濁陰不降,發為泄瀉;而每逢情緒焦慮、緊張之時,素體脾虛,肝氣郁結,橫逆犯脾而致疏泄失常,泄瀉乃至。患者疾病日久,6月春夏之際仍覺四肢欠溫,可見脾陽虧虛損及腎陽,治當溫補脾腎,以消陰翳。方中以炒白術、淮山藥、炒薏仁益氣健脾;石菖蒲、木香化濕和中、疏肝理氣;干姜溫補脾陽;吳茱萸、肉豆蔻、補骨脂補腎助陽;烏藥行氣止痛、散寒溫腎;防風、升麻祛風升清;烏梅斂肝柔肝,配伍芡實又可澀腸止瀉。諸藥合用,共奏健脾化濕、疏肝理氣、溫補脾腎、祛風止瀉之功。二診時,患者腹寒肢冷好轉,泄瀉次數減少,因甘能助濕,補虛不可純用甘溫,久瀉不可分利太過,故改干姜為6g,吳茱萸為2g。三診時,患者諸證明顯改善,本著效不更方之原則,原方稍作改動,服用30余劑停藥,近期隨訪,病情穩定。
4 結語
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是消化科門診的常見病、疑難病,因其無明顯的器質性病變,屬于功能性疾病范疇,故西醫治療只能以對癥處理為主,而中醫藥憑借自身的理論優勢,辨證論治,使其成為運用中醫藥治療的優勢病種。徐師立足于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臨床病理特點,根據疾病進展規律及嚴重程度,將其分為前驅期和初期、中期、后期。前驅期和初期,濕熱是關鍵,此時脾虛尚輕,治以清熱利濕為主;病及中期,寒濕內生,脾氣虧虛,脾陽不足,土虛木乘,此時正虛而邪不甚,治以溫陽健脾、調和土木;疾病后期,脾腎虧虛,肝木亢盛,疾病遷延,日久不愈,此時當溫腎助陽、養肝柔肝。另外徐師著重強調,風邪是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發病的重要因素,在疾病發生的任何階段,均應運用祛風之品。臨證時,常依據不用證型靈活運用各種治法,相兼應用,主次有別,不拘泥于分期,收效顯著。以上所述為徐師多年來治療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經驗之點滴,筆者稍加整理,未能總結全面和完善,今后將進一步傳承與學習,并將徐師經驗推廣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