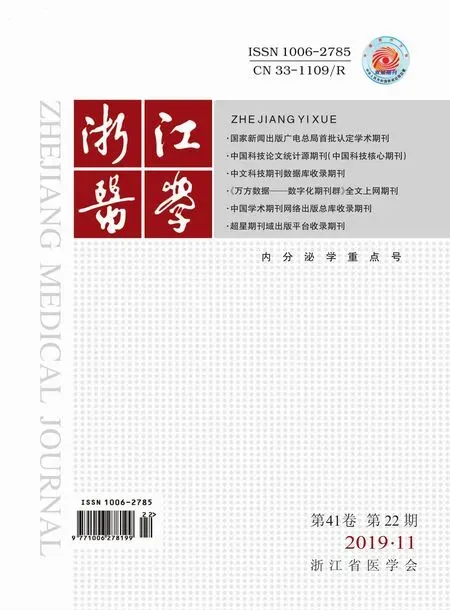腫瘤浸潤淋巴細胞在胃癌免疫治療中的意義
邵瑤健 孟立娜
胃癌是世界范圍內常見的惡性腫瘤。在美國癌癥協會2018 年全球癌癥數據統計報道中,新診斷的胃癌病例數超過100 萬(占總癌癥病例數的5.7%),其中死亡病例大約有78.3 萬(占胃癌病例的8.2%),使胃癌成為第5 大常見癌癥和第3 大癌癥死亡原因[1]。盡管篩查手段和治療措施的提高使胃癌發病率及病死率逐年降低,其預后依舊不理想,仍然有三分之一的患者行根治性切除手術后面臨腫瘤復發及轉移等問題[2]。
免疫治療是通過誘導宿主免疫系統對腫瘤細胞產生有效免疫應答從而抑制惡性腫瘤生長,其甚至可治愈某些免疫應答較好的癌癥亞型。腫瘤浸潤炎癥細胞是宿主對腫瘤細胞免疫應答的表現,以腫瘤微環境為橋梁作用于腫瘤細胞[3]。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是腫瘤浸潤炎癥細胞的主要成分之一。一項針對1 033 例行胃癌切除術患者的研究結果顯示,高浸潤密度的TIL 是宿主高效抗腫瘤免疫應答的體現,是預后良好的指標[4]。而通過重編淋巴細胞功能得到的嵌合抗原受體(CAR)更是在B細胞來源的惡性腫瘤及多發性骨髓瘤的免疫治療中取得顯著療效[5-7],進一步證明了免疫療法在腫瘤治療中的可行性。探究TIL 對胃癌免疫的影響,有望為突破目前胃癌治療的瓶頸提供新方向。
1 癌癥免疫與TIL
癌癥的發生是由單個轉化細胞及其子細胞進行性生長及擴散的結果。在健康個體中,腫瘤細胞表面產生的抗原會被樹突細胞捕獲加工處理并呈遞給T 細胞,激發特異性抗原的效應T 細胞應答,對癌細胞進行殺傷[8],這種免疫系統識別腫瘤細胞為異己并對其進行殺傷的能力稱之為“免疫監視”。宿主保護性反應和腫瘤抵抗免疫系統的能力統稱為“癌癥免疫編輯”。免疫編輯經歷了3 個主要階段:消除階段、平衡階段、逃逸階段。消除階段自然殺傷(NK)細胞及T 淋巴細胞分泌IFN-γ 抑制腫瘤細胞增殖及血管生成;平衡階段是3 個階段中最漫長的,CD8+T 細胞和樹突狀細胞分泌的IFN-γ 和IL-12 使殘留的腫瘤細胞維持在功能性休眠狀態;逃逸階段中腫瘤細胞基因及遺傳高度不穩定,通過改變其特征創造出有利的腫瘤微環境,發生免疫監視逃逸,抑制免疫細胞增殖及促進腫瘤特異性效應細胞凋亡[9]。
TIL 主要是以T 細胞、B 細胞和NK 細胞為代表,可以浸潤在腫瘤細胞內及細胞外基質中。T 細胞的亞群包括CD8+細胞毒性T 細胞(CTL)、CD4+輔助性T 細胞、CD45RO 記憶T 細胞、FOXP3+調節性T 細胞和自然殺傷T 細胞。根據浸潤部位不同,Kang 等[10]將浸潤腫瘤基質的單核炎癥細胞稱為基質TIL,而浸潤腫瘤上皮細胞內的淋巴細胞或單核細胞稱為腫瘤內TIL,并提出基質TIL 可用于預測胃癌無復發生存期(RFS)和無病生存期(DFS)。之后有學者提出TIL 對于腫瘤的調節是雙向性的,一方面樹突狀細胞將捕獲的腫瘤新抗原的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分子呈遞給T 細胞,導致效應T 細胞活化并殺傷腫瘤細胞,這些活化的細胞又能分泌抑制性細胞因子,具有抗腫瘤作用[8,11];另一方面TIL 又為腫瘤生長創造有利的微環境如炎性微環境,促進腫瘤增殖[12]。不同類型的TIL 在各類腫瘤的亞型中作用各不相同,需要區別對待。Thompson 等[13]提出CD8+T 細胞浸潤增加患者的低生存率與程序性凋亡-配體1(PD-L1)高表達相關,表明CD8+T 細胞可能參與了適應性免疫抗性的機制形成。這一觀點也在Kawazoe 等[14]的研究中得到證實。還有報道指出高浸潤密度的FOXP3+調節性T 細胞與良好的預后相關[15],并且腫瘤組織內CD8+與FOXP3+的高比值顯示著較好的總體生存率[16];而低浸潤密度的CD19+B 細胞患者有更長的無進展生存時間[17]。NK 細胞擁有直接清除腫瘤細胞的能力,與低密度的NK 細胞相比高密度浸潤的NK 細胞患者呈現較高的生存率[18]。
2 TIL 與胃癌亞型
根據胃癌組織學形式,常把胃癌分為腸型和彌散型2 類[19],但是這種分類方式并不能對治療策略起到指導作用。“癌癥基因組圖譜”中的胃癌研究小組根據癌癥失調的主要通路將胃癌分為4 個亞型:EB 病毒相關型、微衛星不穩定型(MSI)、染色體不穩定型及基因組穩定型[20]。其中EB 病毒相關型與MSI 的腫瘤組織中顯示著較多TIL 浸潤,這與免疫細胞信號通路激活相關,是適用于免疫治療的胃癌亞型。
有Mate 分析指出大約有10%的胃癌患者屬于EB病毒相關型胃癌[21],并且EB 病毒陽性患者胃癌患病風險率是EB 病毒陰性患者的10 倍[22]。相關報道指出在EB 病毒陽性的胃癌中,高浸潤的TIL 患者免疫治療后有更長的RFS 及DFS[10,23]。EB 病毒陽性胃癌患者還與PD-L1 及PD-L2 相關,大約有15%的胃癌患者9p24.1染色體區域出現擴增,這也正是PD-L1 和PD-L2 的基因座[24]。在一項以免疫微環境成分進行分組(以TILs 及PD-L1 分為4 組)的研究中,TILs 陽性及PD-L1 陰性組有67% 的EB 病毒陽性胃癌患者5 年生存率最好,而預后最差的是TILs 陰性及PD-L1 陽性組[25]。
MSI 型在所有胃癌中占比15%~30%,并且在腸型胃癌、胃竇位置、高齡患者及女性患者中多見[20,26]。MSI其實是一種遺傳變異,是由重復的核苷酸序列區域擴張或收縮組成。這種遺傳變異一般是由錯配修復1 抗原或錯配修復蛋2 抗體突變引起DNA 錯配修復酶功能障礙造成的。對于MSI 型再進行細分,將≥2 個標志物顯示不穩定定義為高頻率(MSIH),只有1 個標志物顯示不穩定定義為低頻率(MSIL)。據薈萃分析(用于分析MSI的5 類標志物由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推薦)顯示,MSIH型患者CD8+T 細胞、FOXP3+T 細胞的浸潤密度更高,FOXP3+/CD4 和顆粒酶B/CD8 的比例更高,且該型患者的死亡風險較MSIL 型低,有著更高的總生存率[27]。
另一項研究發現,MSIH 型因細胞突變數量增加,突變細胞表面的新抗原數量也會增加,從而激活免疫系統,能夠阻斷PD-1 對T 細胞表達的抑制作用[28-29]。MSI與CD8+TIL 組合標志物更是胃癌患者免疫狀態的體現,是其預后的生物標志物[30]。
3 TIL 相關胃癌免疫治療
目前免疫治療的策略可分為主動免疫和被動免疫兩大方向。主動免疫中包含采用細胞因子、疫苗接種、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等方法[31],其中以抗細胞毒性T 淋巴細胞蛋白4(抗-CTLA-4)和抗程序性死亡受體1/程序性死亡受體-配體1(PD-1/PD-L1)為代表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通過增強TIL 對胃癌細胞的免疫應答起到腫瘤殺傷作用,是近年胃癌免疫治療研究的熱點。CTLA-4是活化的T 淋巴細胞和調節性T 細胞的共抑制分子。在激活的T 淋巴細胞中,CTLA-4 通過與CD28 競爭性結合抗原呈遞細胞上的B7-1/B7-2,從而抑制CD28 介導的T 淋巴細胞激活信號[32]。抗-CTLA-4 的原理是通過與CTLA-4 特異性結合,從而減少與CD28 之間的競爭性抑制,促進T 淋巴細胞活化增殖且降低了對調節性T細胞的免疫抑制作用。在一項18 例胃食管腫瘤患者的臨床研究中,使用CTLA-4 檢查點抑制劑組患者總體生存時間中位數為4.83 個月,有30%左右患者存活時間超過1 年[33]。還有一項臨床研究正在評估CTLA-4 檢查點抑制劑與抗PD-L1 抗體聯用對于胃食管腫瘤患者預后的影響[34]。
在大約42%的胃癌患者中,PD-L1 表達升高,而這種表達的升高可能與信號轉導、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 及轉錄激活因子3 個通路相關[35]。此外還有報道稱,PD-L1 的上調與微小RNA-200/轉錄因子E 盒結合鋅指蛋白-1(ZEB-1)控制軸密切相關,而ZEB-1與上皮間質轉化及TILs 分泌IFN-γ 相關[36]。最初關于PD-L1 對胃癌預后的影響存在一定爭議,但是更多的薈萃分析證明,PD-L1 高表達是胃癌預后差的獨立危險因素[37-39]。近期一項納入173 例胃癌患者的實驗研究顯示PD-L1 陽性患者總生存率低下,且TILs 中的PD-1和PD-L1 表達量明顯高于外周血的表達量[40]。還有一項研究指出,在原發性腫瘤中,PD-L1 和PD-L2 的高表達與CTL 細胞數量減少相關,而PD-L1 在胃癌CTL 細胞上的高表達預示著Ⅱ期和Ⅲ期胃癌患者較差的生存預后[41]。這種PD-L1 的過表達常發生在EB 病毒相關型胃癌和MSI 型胃癌中,這可能與這兩種胃癌亞型的腫瘤基質中具有豐富的淋巴細胞(特別是CTL 細胞)浸潤相關[42]。因此這類抗PD-1/PD-L1 抗體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EBV 相關型及MSI 類型的胃癌中有較好的療效。
被動免疫是以過繼性細胞治療(ACT)為主,這種方法主要原理是將腫瘤特異性T 淋巴細胞注射入腫瘤組織中,例如細胞因子、抗CD3 單克隆抗體誘導的殺傷細胞及TIL 等促進腫瘤細胞溶解。研究證明,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在人白細胞抗原I 類分子限制的情況下仍能夠殺傷表達有絲分裂著絲粒相關驅動蛋白的結腸癌、胃癌細胞,證明了過繼性細胞治療的可行性[43]。而另一種細胞因子誘導的殺傷細胞主要通過刺激IFN-γ 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起到抗胃癌細胞增殖的作用。由于胃癌通常缺乏基質浸潤,故有學者提出將ACT 與化療聯合治療的方案。利用奧沙利鉑通過高頻遷移蛋白家族1 誘導抗癌T 淋巴細胞,使該免疫原性的癌癥細胞死亡[44]。雖然TIL 過繼性細胞療法在黑色素瘤的治療中顯示著較好的療效,但因TIL 本身具有刺激腫瘤細胞增殖的能力,故其在胃癌中治療的療效并不理想[45]。NK 細胞的過繼性細胞療法,因NK 細胞自身具有直接殺傷腫瘤細胞的能力,故在一項研究中胃癌患者的DFS 顯著改善,但是對于患者總體生存率沒有明顯提高[46]。
隨著更精確的腫瘤浸潤分析方法的發展,不同浸潤細胞類型在胃癌臨床預后中的意義會越來越清晰。特別是對于具有豐富TIL 浸潤的胃癌類型(如EB 病毒相關型及MSI 型),TIL 可以作為判斷預后重要的生物標志物。還有以抗PD-1/PD-L1 為代表的特異性免疫檢查點阻斷免疫療法,是未來胃癌治療的潛在候選藥物。認識TIL 在胃癌演變中扮演的角色,預示著更多的治療方案的選擇,胃癌個性化治療也將迎來新的機遇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