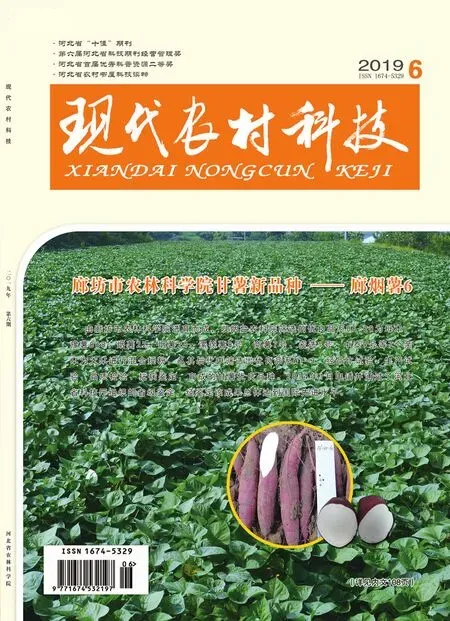委托代理理論下鄉(xiāng)村治理新體系建構(gòu)
——以南充市雙龍橋村為例
唐 敏 陳小愛
(西華師范大學(xué)政治與行政學(xué)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本文運(yùn)用委托代理理論,從治理主體出發(fā)分析鄉(xiāng)村治理面臨的諸多困境,以雙龍橋村的成功實(shí)踐為例,提出構(gòu)建鄉(xiāng)村治理新體系,這對鄉(xiāng)村治理至關(guān)重要。
1 理論前提:政治委托代理理論的闡述
委托代理理論的出現(xiàn)始于經(jīng)濟(jì)學(xué)領(lǐng)域。20世紀(jì)30年代,美國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所有權(quán)和經(jīng)營權(quán)分離”的命題假設(shè);1937年,科斯在 《企業(yè)的性質(zhì)》中第一次提出了交易費(fèi)用學(xué)說,委托代理理論初具雛形。直至上世紀(jì)90年代后,以佩爾森、貝斯利等為代表的學(xué)者開始運(yùn)用委托代理理論來分析政治選舉、公共政策等問題,極大地豐富了政治領(lǐng)域的委托代理理論。國內(nèi)關(guān)于該理論的闡述始于2001年彼得B.博斯馬、王國華和孫春霞的 《現(xiàn)代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shí)踐——以荷蘭為例》一文,他們對委托代理理論的缺陷進(jìn)行探討并以荷蘭的公共組織實(shí)踐為例。其后,委托代理理論又用于分析“集權(quán)—分權(quán)”模式、民主政治中的關(guān)系、政府信用問題、政府預(yù)算、行政腐敗、公民權(quán)利以及權(quán)力監(jiān)督體系等,至此,委托代理理論從更廣的層面逐步進(jìn)入了中國政治領(lǐng)域。
將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委托代理運(yùn)用于政治領(lǐng)域就形成了政治委托代理理論,其實(shí)質(zhì)是一種契約理論。在契約中,基于委托人和代理人雙方信息非對稱、理性經(jīng)濟(jì)人假設(shè)、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相分離的前提,委托人將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給予代理人而形成了委托代理關(guān)系,其任務(wù)是研究“如何在信息非對稱和委托人與代理人利益相互沖突的前提下來實(shí)現(xiàn)雙方利益最大化的問題”[1]。通過對政治(治理)過程中各個(gè)主體和各種委托代理關(guān)系的研究揭示各種委托代理問題,集中表現(xiàn)為代理人危機(jī)問題(委托人和代理人雙方的信息非對稱博弈)。一方面,委托人將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交付于代理人,由于知識(shí)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委托人獲取代理人的信息極其有限,作為獨(dú)立個(gè)體,在獲取代理收益的同時(shí)繼續(xù)追求額外收益的代理人可能出現(xiàn)失德的行為;另一方面,在鄉(xiāng)村治理過程中,很多政治過程都是通過代理人內(nèi)部進(jìn)行,排除了委托人的參與,缺乏透明度,造成委托人的不信任,影響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dòng)性。在我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甚至是村一級的村民委員會(huì),都是代表著人民行使權(quán)力的[1]。所以,運(yùn)用政治委托代理理論分析鄉(xiāng)村治理是具有共通性的。它作為一種理論分析工具,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思路:如何分析并解決政治(治理)過程中的委托代理危機(jī)問題來實(shí)現(xiàn)帕累托最優(yōu)。
2 問題分析:基于治理主體間的委托代理關(guān)系
在村民自治的30余年里,基層治理得到了突破性發(fā)展,但廣大鄉(xiāng)村“基層政權(quán)—農(nóng)村”行政指令式的治理體系在本質(zhì)上未曾改變,使村莊陷入半行政化狀態(tài),鄉(xiāng)村民主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受阻。
2.1 自下而上的委托代理關(guān)系:村民—村委會(huì)。在我國,一切權(quán)力都來自于人民,所以村民是鄉(xiāng)村治理體系中的“最初委托人”。村民通過直接選舉的方式將管理村務(wù)的部分自治權(quán)力委托給村民委員會(huì)代為行使,形成村民—村委會(huì)的委托代理關(guān)系。在治理過程中,由于村委會(huì)成員比普通村民擁有更多的能力、知識(shí)和信息優(yōu)勢,在獲取代理收益的同時(shí)仍會(huì)盡可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從而導(dǎo)致村級治理必然面臨兩個(gè)問題。一方面,代理人為獨(dú)占代理收益導(dǎo)致鄉(xiāng)村橫向治理主體缺失,治理能力不足。在現(xiàn)存的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村委會(huì)幾乎包攬一切村級事務(wù)成為常態(tài),村務(wù)治理能力也十分不足,如2009年前,雙龍橋村委會(huì)工作人員年齡偏大,工作方式陳舊,村務(wù)資金、信息公開度低,村支部和村委會(huì)成員固化。另一方面,代理人失德,村級監(jiān)督機(jī)制缺失。村委會(huì)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作為代理人的村委會(huì)擁有信息優(yōu)勢,而作為委托人的村民卻沒有能力約束其行為,代理人在治理中就可以暗箱操作,損害委托人權(quán)益,出現(xiàn)失德行為,如貪污腐敗、權(quán)力異化、效率低下等。要規(guī)避代理人失德危機(jī),建立村級監(jiān)督機(jī)制就顯得必不可少。
2.2 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關(guān)系:村委會(huì)—村民。將村務(wù)具體操作和落實(shí)的權(quán)力委托于村民個(gè)體形成了村兩委—村民之間的委托代理關(guān)系。村民自治的落腳點(diǎn)依然在于村民個(gè)體,我們要建設(shè)的是屬于廣大農(nóng)民的鄉(xiāng)村。換言之,村民是鄉(xiāng)村治理體系的“最終代理人”。由于城鄉(xiāng)一體化的發(fā)展,市場經(jīng)濟(jì)理念向鄉(xiāng)村社會(huì)滲透,傳統(tǒng)村民互助團(tuán)體逐漸走向衰落,村民個(gè)體化傾向加強(qiáng),逐漸呈現(xiàn)出游離于團(tuán)體外的狀態(tài),組織化程度低,缺乏集體認(rèn)同感和凝聚力。在無代理收益或者代理收益甚微時(shí)往往表現(xiàn)出參與自治積極性不高、主動(dòng)性不強(qiáng)的狀態(tài)。究其原因,從領(lǐng)導(dǎo)組織這個(gè)角度來看,基層黨組織在村級治理中并沒有發(fā)揮實(shí)際上的領(lǐng)導(dǎo)核心作用,無法將黨中央的影響力擴(kuò)散到廣大鄉(xiāng)村地區(qū),面對鄉(xiāng)村個(gè)體化現(xiàn)象,無法有力地整合鄉(xiāng)村社會(huì)資本、提高農(nóng)民的組織化程度,更無法保障村民自治的順利開展。如雙龍橋建新村前,地域分散,大多數(shù)村民在外務(wù)工,整個(gè)村莊呈現(xiàn)空心化狀態(tài),留守者僅是老人和兒童,村民大會(huì)、黨員大會(huì)召開時(shí),往往是寥寥數(shù)人。在選舉村委會(huì)成員時(shí),往往是無所謂的心態(tài),村民村務(wù)參與冷漠。
3 實(shí)踐創(chuàng)新:維系鄉(xiāng)村治理新體系的探索
治理擁有的“管理機(jī)制是合作網(wǎng)絡(luò)的權(quán)威,其權(quán)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自上而下和單一的”[2]。雙龍橋新村的建設(shè)是基于村民自愿由政府引導(dǎo)促成的。在實(shí)現(xiàn)了村集體經(jīng)濟(jì)繁榮后,著力村莊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最后在新村運(yùn)作中,集中突出多元社會(huì)組織的村級治理,形成了“一核心(基層黨組織領(lǐng)導(dǎo))一監(jiān)督(村監(jiān)委)”的多元鄉(xiāng)村治理新體系。
3.1 確立了農(nóng)村基層黨組織的核心領(lǐng)導(dǎo)地位。“鄉(xiāng)村振興”著重提出要確立農(nóng)村基層黨組織的核心領(lǐng)導(dǎo)地位。雙龍橋村響應(yīng)國家政策,最先確立了基層黨組織的核心領(lǐng)導(dǎo)地位,真正地從實(shí)踐層面使其成為鄉(xiāng)村治理的基石。首先,完善了基層黨組織的設(shè)置。雙龍橋村在引進(jìn)的臺(tái)灣企業(yè)中設(shè)置了黨組織,擴(kuò)大了覆蓋面,改變了以往一村一支部的局面,加強(qiáng)了黨組織的凝聚力。其次,整頓了軟弱渙散的村黨組織。下派駐村第一書記,重新選舉年輕化黨組織成員,實(shí)現(xiàn)網(wǎng)絡(luò)化辦公,制定明確的 《村支部書記工作條例》,提高工作效率。再次,壯大了農(nóng)村青年黨員隊(duì)伍,發(fā)揮先鋒模范作用。一方面,鼓勵(lì)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的青年向黨組織靠攏,全村共有35名黨員,13名流動(dòng)黨員,1名預(yù)備黨員;另一方面,以“農(nóng)民夜校”為載體,以時(shí)政學(xué)習(xí)、廚藝探討、創(chuàng)業(yè)培訓(xùn)、法律宣講等為學(xué)習(xí)內(nèi)容,積極發(fā)揮黨員帶頭作用,豐富村民業(yè)余生活。最后,形成了基層服務(wù)型黨組織,為群眾辦實(shí)事,辦好事。黨組織在民生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水電氣視訊全面通達(dá),幼兒園、醫(yī)療衛(wèi)生、計(jì)生服務(wù)、農(nóng)家書屋、農(nóng)家超市、便民中心等全面配套。
3.2 成立了村民監(jiān)督委員會(huì),建立健全村務(wù)監(jiān)督機(jī)制。委托代理理論構(gòu)架下的治理體系無法避免村委會(huì)權(quán)力異化等問題,建立健全監(jiān)督機(jī)制是破解這一困境最根本的措施。一方面,以制度保障作為基礎(chǔ)。雙龍橋村制定了村務(wù)公開制度(關(guān)于黨務(wù)、村務(wù)、財(cái)務(wù)和集體資源、集體財(cái)產(chǎn)、集體資金公開的具體規(guī)定)、村委會(huì)工作報(bào)告制度(關(guān)于每季度、每半年、年終等向村民會(huì)議和村民代表大會(huì)報(bào)告工作的具體規(guī)定)與村民詢問質(zhì)詢制度(關(guān)于村民向村兩委詢問和質(zhì)詢的具體規(guī)定以及設(shè)立專門的接待日、舉行村情民意溝通互動(dòng)會(huì));以明文制度的形式規(guī)定村委會(huì)必須定期報(bào)告工作以及村民擁有詢問、質(zhì)詢和監(jiān)督的權(quán)利。另一方面,以機(jī)構(gòu)保障為載體。成立了村民監(jiān)督委員會(huì),制定了 《村監(jiān)督委員會(huì)工作職責(zé)》,以具體條例的方式規(guī)定了其工作的具體內(nèi)容。村監(jiān)委是由村民委托給村委會(huì)、村委會(huì)再委托給村監(jiān)委的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所構(gòu)成的委托代理關(guān)系鏈。村監(jiān)委既要全程監(jiān)督村務(wù)的決策執(zhí)行情況,又要及時(shí)收集反饋群眾建議。它的設(shè)立既能避免村委會(huì)代理人失德的危機(jī),又能調(diào)動(dòng)村民參與村務(wù)的主動(dòng)性,強(qiáng)化村民主人翁意識(shí)和集體感。
3.3 夯實(shí)村委會(huì)的基礎(chǔ)性地位,支持多元社會(huì)組織協(xié)同參與。隨著鄉(xiāng)村社會(huì)差序格局的解體,鄉(xiāng)村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走向具有現(xiàn)代團(tuán)體格局成為一種應(yīng)然選擇[3]。雙龍橋村的多元社會(huì)組織是在村委會(huì)引導(dǎo)、治理需要的前提下自主形成的,將村級公共服務(wù)事項(xiàng)委托給多元社會(huì)組織協(xié)同治理,形成了不同的委托代理關(guān)系鏈,在村務(wù)治理的整個(gè)過程中,它們都受基層黨組織的領(lǐng)導(dǎo)、村監(jiān)委的監(jiān)督,各司其職、分工明確,改變了以往村委會(huì)—村民的二元治理窘境,提高了鄉(xiāng)村治理效率。在經(jīng)濟(jì)方面,成立生產(chǎn)合作社,統(tǒng)籌管理鄉(xiāng)村旅游、企業(yè)經(jīng)營、自主創(chuàng)業(yè)等事項(xiàng);成立勞務(wù)輸出合作社,解決勞動(dòng)力閑置問題,實(shí)現(xiàn)村村資源共享。在文化教育方面,成立農(nóng)民夜校,設(shè)立農(nóng)家書屋,提高農(nóng)民的知識(shí)技能水平;成立老年活動(dòng)中心,組織舞獅隊(duì)、舞蹈隊(duì),老年團(tuán)體精神生活富足;成立關(guān)心下一代委員會(huì),在保護(hù)未成年人權(quán)益的同時(shí),特別注重孩子的個(gè)性發(fā)展以及教育問題。在村務(wù)日常管理方面,成立業(yè)主委員會(huì),建設(shè)村貌、維護(hù)村容以及管理村民日常生活。成立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huì),調(diào)解矛盾糾紛,宣傳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紀(jì)守法,弘揚(yáng)社會(huì)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