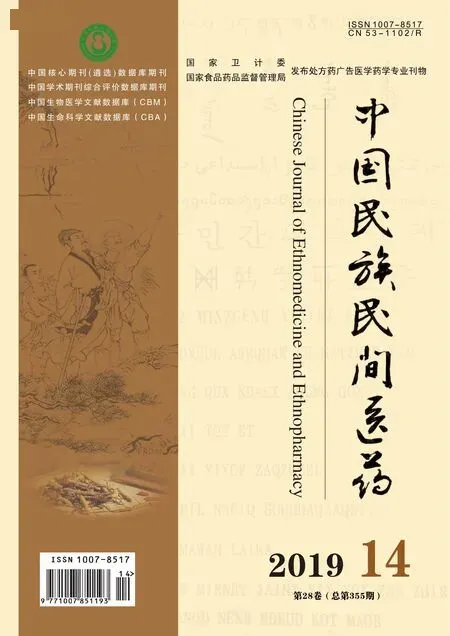基于《醫宗粹言》探析新安醫家羅周彥“元陰門”學術思想
孫宇潔 郭錦晨
安徽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8
羅周彥,明代新安固本培元派醫家,其人家學淵源,施于有政,時人譽其醫術“刀圭所至,凋瘥盡平”。所撰之《醫宗粹言》,為集古圣賢之成而析類分章的綜合性醫書,“元氣論”主述先后天元陰元陽之辯,參以六淫七情、隨類引方,可使讀者既能知所調攝而治未病,又能注重源本而知常達變[1]。新安養陰清潤派導源于朱丹溪滋陰說,與新安固本培元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羅周彥首分元陰、元陽,并創立滋陰之方,對新安養陰清潤治法的形成產生一定影響[2]。
元氣為人根本之氣,此氣發于腎,化于腎精,通于三焦,循于全身。有醫家認為,元氣的運動的表現形式在陰陽兩個方面可分為元陰元陽,亦有觀點認為,元陰元陽為腎中精氣的一部分,二者均贊同元陰在全身的體現包括精、津、液的功能,對機體起著滋養濡潤作用[3]。因元氣之精藏于腎中,故元氣又稱腎氣,元陰又稱腎陰。明代,由于命門學說的興起和發展,形成了真陰、真陽為全身陰陽之本的理論,醫學大家張景岳有言:“命門為元氣之根,為水火之宅,五臟之陰氣,非此不能滋;五臟之陽氣,非此不能發”。
1 元陰之象
羅氏十分注重元氣: “人之初生,稟受一氣,而后情欲漸開也,故立先后天元陰元陽之辯而統之曰元氣論”,并在《醫宗粹言·元氣論·元陰門》中將元陰分先天無形元陰與后天有形元陰。前者稟受于父母,是構成人體生命的原始物質;后者來源于飲食水谷精微,是促進人體生長發育、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物質。
羅氏認為無形元陰即“腎水所稟元精之氣”,陰在水火中屬水,故腎陰又稱腎水,元精是構成人體一切組織器官的物質基礎[4]。元精之氣源于父母,決于先天,與生俱來,藏于腎中,是生命發生的本源,是人體生長發育的生殖的物質基礎,氣為極細微精微物質,故無形。其“本體深藏于左腎之中,其妙用默蘊于精神之內”,故無形元陰在精神活動中亦發揮著重要作用。
據羅氏所言,有形元陰即“有形榮血之母氣”,可化生營血[5]。后天攝入的飲食水谷化生精血藏于五臟,統綜于有形元陰,他指出,后天有形元陰源于先天有形元氣中屬陰的部分,附藏于脾胃之中,故飲食水谷的吸收與有形元陰興衰息息相關,化見于人迎,其脈在心部,其用見于血,故撫病者人迎、觀其氣血運行可察有形元陰之態。
2 元陰之病
傳統中醫理論認為,元陰虧虛為房勞內傷,久病及腎,或溫病后期熱極傷陰, 情志內傷,暗伐腎水,失血耗液而致腎陰虧損,虛火上亢所產生的一系列癥狀的總稱[6]。羅氏把元氣不足作為病因看待,指出先天元氣不足和后天的消耗,皆可損耗元氣而導致疾病的發生[7]。元陰源于先天,充養于后天,故病因常為所稟受父母之陰已先有損,后天復因內傷外感使其陰愈損。
羅氏指出,先天元陰為病,病因其一為父母縱欲過度,素傷腎氣,或“因交感之際偶從七情”而致真陰已傷,其子女色欲及七情亦不知節制;病因其二為父母平素已因勞傷吐血,或因郁怒傷肝之陰,則子女所稟此氣在先天已有所虧虛。此時若復因大勞或因久怒所傷,則已虧之陰損傷更甚。先天元陰虛損者,其癥狀一為滋潤之力減弱,精神恍惚、夜臥不安,其目“然”不可視物,懼視白光、出現幻覺,二為虛火內擾,病患左脅、睪丸不定期發高熱,眼珠突然作痛,眼目忽腫而后又消……皆為肝藏先天元陰之氣不足。
后天元陰為病,其病因可能是在母胎中時,因七情內損,或因飲食勞倦,久傷脾胃,致使陰氣衰弱,則子女所受父母之陰已先有所虧虛,而后又因七情、飲食勞倦使元陰損傷更甚,使榮血缺乏生化之源,不能灌溉周身,所稟已虧之陰愈損,易生疾患。后天元陰虛損者,臨床癥狀多表現為血不榮、各種出血,“其癥故顯于榮血之間,或為吐血……或為骨蒸煩熱之類是也。而病患眼目昏花,或羞明怕日,或目流血,或筋脈痿弱,或筋緩酸痛,或寒熱往來而似瘧非瘧,或小便溺血。”
3 元陰之治
元陰虛損當以滋陰為根本之法,兼以安神、補血之藥,同時避免使用過于苦寒的藥物以免損傷元陽。
3.1 元陰之法 先天無形元陰治療之法,當遵“溫存反觀內養”,先補后天之陰,再充先天之陰。先天元陰受傷,多導致神識不清,夜不可安眠,易受驚嚇,“此為神思間無形之火動,治宜大補真陰兼以安神,則火自降而神自清”。清代新安固本培元派醫家吳澄認為,痰證之本“本于先天之真陰真陽不足”兩方,痰涎大補真元之治要先“察腎中之陰陽”,與羅氏元陰不足之治有異曲同工之妙[8]。張景岳亦有言:“諸寒之而熱者,謂以苦寒治熱而熱反增,非火之有余,乃真陰之不足也。陰不足則陽有余而為熱,故當取之于陰,謂不宜治火也,只補陰以配其陽,故陰氣復而熱自退矣”[9]。
后天有形元陰治療之法,羅氏根據人體本身元氣的強弱分兩種情況而論,一為由外傷內,因實致虛,“因七情或六淫或飲食勞倦之類傷其榮血”,血逆氣滯,不通則痛,纏綿日久,累傷母氣。因正氣已虛,不可貿然攻邪,治當攻補相兼,亦當量其輕重,藥力適中。由于腎陰為一身陰液之本,臨床常用的補陰方劑,也大都寓補腎水于方劑之中[10]。二為元氣充足,正氣不虛之患,“則不必固元而以峻劑擊之”。
3.2 元陰之方 肝藏先天元陰之氣不足以致虛火為患,此由水火不交而致心腎不濟,滋水益肝湯可治之。方中生地滋陰退熱、益精壯神,當歸、白芍補血以滋陰、強筋骨而壯元精,堅意益志、安魂定魄,與熟地同用則峻補其陰,此四味“大補真陰元精之圣藥”。細生甘草有瀉心之能及緩急之妙,降神中之火非此不治,避免使用知母、黃柏,補其陰而火自降以免苦寒太過損傷中氣。玄參可瀉心火、滋腎陰,柴胡疏散退熱,為疏肝解郁之要藥。羅氏特別指出,甘溫補五臟之陽,甘寒補五臟之陰,當先天無形元陰不足時,人參、白術、黃芪等甘溫之性的藥不可選用,當歸、地黃等甘寒之藥為宜。當正確的使用了補陰藥卻無法立刻痊愈的情況出現時,不應自我懷疑,而是因藥的用量不足,效力不夠所致,“藥非百數、功非歲月則不能挽回元氣矣”。當不服藥時覺“火動不安”即是藥已發揮療效的最好證明。
后天有形元陰不足,生化榮血之力減弱,故常有血虛不榮之癥,證治常用四仙湯。方中當歸、白芍補血滋陰、益精養筋健骨,安神益志,熟地助歸芍補血滋陰之用,同時益精填髓,細生甘草瀉心緩急,降精神之火。若體內有火熱之邪,則倍加細生甘草,發揮其清熱之用。或用滋陰益元湯,除川歸、芍藥、細生甘草、熟地外,加沙參養陰清肺,益胃生津,茯苓健脾寧心,壯其脾胃,使氣血生化得源,精神得安,麥門冬清心降火、除煩退熱,與五味子同用則補元津之氣而生津止渴,保肺金之母,生腎中之水,陰液生化得源。
4 小結
羅氏精研醫術,思維周密,在施行補陰之法時兼顧正氣而不貿然攻邪,提倡當元氣虛衰與病氣有余兩者并見時,當先補其正氣而后去邪。當正確辨證施治卻未得先期之效時,不應自我懷疑,改弦更張,而往往為病重藥輕,應堅持使用先前所立之方。同時羅氏指出,治療元陰不足,虛火上炎之證,滋陰之方不應加入知母、黃柏等性質過于寒涼的藥物,以免苦寒太過,反損人體陽氣,時時著重于培補人體正氣。其學術思想參以先賢奧旨,其補陰以精煉之語言釋醫理,并征以成效之良方,上承丹溪滋陰之理,下啟新安養陰清肺之說,其深刻的思考、嚴謹的態度對后世治學均有著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