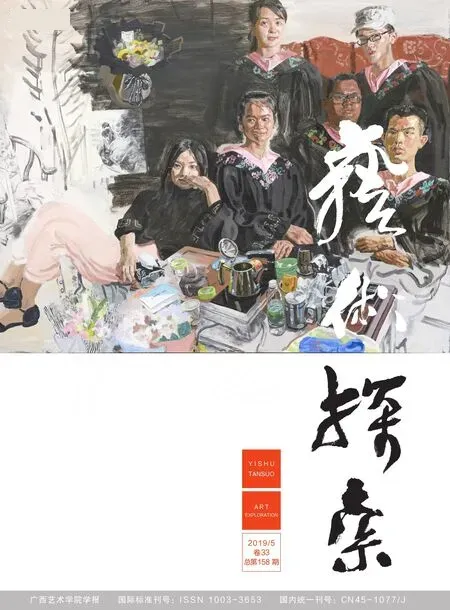反常合道:黑鏡視野下的科幻電影創意
黃鳴奮
(廈門大學 人文學院,福建 廈門 361005)
現實科技不僅是激勵科幻電影創意的契機、制作科幻電影產品的條件,而且是滋潤科幻電影內容的甘露。盡管如此,經過創意的折射,作為內容出現在科幻電影產品中的科技卻可能和現實科技頗為不同。我們可以用“黑鏡”來概括其特點。“黑”是多義詞。從自然角度看,它指和“白”相對的顏色(如煤炭般),和“亮”相對的環境(即昏暗),和“白天”相對的時段(即夜晚);從社會角度看,指管理意義上的不合制度(如黑市、黑店、黑貨、黑帖等),倫理意義上的狠毒(如腹黑、黑心等),政治或法律意義上的越軌(如黑手、黑幫、黑社會等);從心理角度看,指認識上不愿暴露或不易了解(如黑幕等),情感上傾向于隔離(如拉黑、黑名單等),意志上未經許可而進入(如利用IT特長攻擊網站的黑客行為等)。“鏡”作為名詞的本義是表面光潔,可以照形取影的金屬器具,后來擴展到其他材質和用途的光學用具,在喻義上指映射事物或生活的精神產品;作為形容詞意為明凈;作為動詞指照形、明察或借鑒。“黑鏡”本義是黑色材質的鏡子(如表面黑得發亮,足以鑒人的銅鏡),后來拓展到對紫外線和紅外線有過濾作用的墨鏡,以至于可以投映圖像的監視器、顯示器、手機等電子裝置的屏幕,在科幻界使人聯想到英美所出品的同名電視劇。本文以“黑鏡科技”作為科幻電影創意的重要特征,指的是體現“反常合道”原則的科學技術。“反常合道”本是宋代蘇軾在總結詩歌創作經驗時提出來的,[1]124指的是出乎意料之外(反常),仍在情理之中(合道)。以下所論述的科技內容的異常演繹,實際就是這一原則的運用過程。
一、黑鏡科學與科幻電影創意
科學就其總體而言象征光明,這不僅是指它卓有成效地探索自然規律,而且是指它有理有據地為制訂社會規范提供指南,同時還是指它實事求是地幫助我們規劃人生、反省自我。當然,科學原理必須符合自然規律才能成立,科學規劃必須符合社會規范才能實施,科學動機必須符合健康原則才能持之以恒。我們將符合上述要求的科學稱為常規科學。相比之下,所謂“黑科學”可能是指違背自然規律難以成立,違背社會共識(特別是同行共識)難以得到承認,違背邏輯要求難以自洽,或者那些太過玄妙、遠非同時代人所能理解的理論。至于“黑鏡科學”,則是否定之否定。它雖然違背我們所在世界的自然規律,但可能在其他世界中成立;雖然違背我們所處時代的同行共識,但可能為其他時代、其他社會中的科學共同體所認可;雖然違背我們目前所遵循的邏輯要求,但可能符合其他智能生物的思維特征。科幻電影通過對上述“其他”條件的構想,為“我們”的世界、時代、社會、族類建立了新的參考系,使人類得以拓展自知之明。這就是體現藝術精神的“反常合道”。
(一)亮起:諸事有常與科學的貢獻
“諸事有常”指的是世間任何事物的存在、發展與消亡都是有規律可尋的。尋找上述規律是科學的使命,規律本身的存在則是科學的前提。找到了上述規律,原來無序就變為有序,無常就變得有常,科學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成為智慧之光。
與人類其他知識相比,科學是可驗證、系統化的知識。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對某種經驗現象或客觀事實的正確解說和系統解釋,即科學原理。它們不僅在邏輯上是自洽的(經得起主觀推敲),而且在實踐中是可靠的(經得起客觀檢驗)。科學原理以科學實驗為基礎,通過科學假說而拓展。科學假說作為名詞是指根據已有科學知識和新的科學事實對所研究的問題作出的一種猜測性陳述,作為動詞是將認識從已知推向未知,進而變未知為已知的思維方法。它包含了某種合理想象,后者通過有待驗證的預言、有待統合的理論、有待演算的公式等形態表現出來。
科幻創作將由科學理論出發的合理想象當成確立內容合法性的重要途徑。例如,第9屆土星獎最佳科幻電影——美國《超人2》(Superman II,1981年)試圖利用能量轉化原理說明異能來源。在該片中,太陽的黃光使被囚禁在氪星幻影區的三個惡徒獲得超能力。他們攻擊了月球上的人類空間站,又來到地球上作惡。超人的對策是將他們引導到位于北極的堡壘,利用那兒的氪石紅光消除了這些惡徒的超能力。美國以變種人為題材的“X戰警”系列電影則根據生物學的變異理論來構思。在歷史上,是變異為進化提供基礎。隨機性的點突變若和生物個體、群體以至于生態的系統性相協調,便有可能顯示出相對確定的方向。經過漫長的發展,地球生物圈已經形成了豐富多樣的生命形式。正是以這樣的認識為前提,“X戰警”系列電影試圖讓觀眾相信各種異能者完全可能在適當的條件下出現。在第30屆土星獎最佳科幻電影——美國《X戰警2》(X2,2003年)的結尾,畫外音告訴我們:變異對人類發展至關重要。變異通常以千萬年為時間單位,但有時也會在幾十萬年中發生。人類的強勢存在固然對生命多樣性造成了威脅,但反過來也可能通過人為進化造就新生命,當然這存在相當的風險。
(二)黑入:諸事無常與科學的局限
“諸事無常”指的是偶然性或未知因素在世間任何事物的存在、發展與消亡過程中具備重大影響。因此,人的認識總是有局限的,即使代表人類智慧所達到的最高水平的當代科學也是如此。科學原理不等于絕對真理,科學驗證本身包含了諸多不確定性。每當人們以為窮盡了某一問題的答案時,也許新的問題就已經產生。因此,科學與其說是定型不變的分科知識體系,還不如說是分領域進行學習的求知過程(領域的劃分本身也是相對的)。
科幻電影完全可以從肯定的角度對科學加以描寫,這不僅是指自覺地將科學當成自己抒情、寫意、言理的參照系,而且是指稱頌科學在探索自然規律、指導社會生活、成就心理發展等方面的貢獻。例如,第33屆土星獎最佳科幻電影——英美聯合制作的《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2006年)設想2027年人類已經遭遇連續18年的全球性不育,大西洋北部的亞速爾群島致力于不孕癥治療的科學家組織是希望所在。
當然,科幻電影也可以從否定的角度“黑入”(不經許可而進入)科學領域。例如,在主觀層面上,展示自然界仍然存在許多現有自然科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人類社會仍然存在現有社會科學無法克服的沖突,自我意識仍然存在現有思維科學無法擺脫的矛盾。在客觀層面上,展示科學界某些理論實際上基于不周到的觀察、不可靠的數據、不嚴密的實驗,因此距離自然意義上的真理頗有距離。某些科學組織實際上和一般官僚機構或企事業單位沒什么兩樣,爾虞我詐,上下其手;某些所謂“科學家”實際上是欺世盜名之徒,為牟取個人利益不擇手段。當然,科幻電影對科學界的“黑入”是有限度的。它的基本立場是補弊救偏、治病救人,而不是大張撻伐、全盤否定。
科幻電影對科學的“黑入”,和科學的問題意識是一致的。科學作為內容包含了問題意識,承認已知與未知、正確與錯誤、名義與實際等現象是相聯系而存在、相博弈而發展的。科學如果要將探索真理的初衷貫徹到底的話,就不能不承認自身也存在懸而未決的問題,有待反思或直面。這正是許多科幻電影設定情境的思路。例如,根據美國《超能敢死隊》(Ghostbuster,1984年)的構思,提供驅鬼服務的三個前超心理學教授被紐約市政當局在公開場合宣布是騙子,實際她們是有膽有識的科學家。國土安全部已經注意到紐約的鬧鬼問題,一方面要求她們別公開宣傳有鬼,以免使公眾產生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又允許她們繼續秘密開展研究。該片涉及科學本身的邊界、合法性與傳播效應等問題。我國《我兒子去了外星球》(2018年)則揭示了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矛盾。那些打著國家級正規研究所旗號來樂泊鄉考察“外星人尸體”的科學家,實際上是冒牌貨。上述影片當然不至于導致觀眾將所有的科學家都視為騙子,也不至于讓觀眾否定科學界同樣有騙子存在。如果從中可以看出被說成是騙子者適得其反是真正的科學家,自稱是科學家者適得其反是騙子,那么,編導也許就達到了自己“黑入”的目的。
(三)穎悟:反常合道與科幻的價值
“穎悟”在這里是指將諸事有常和諸事無常結合起來思考,意識到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統一。科學之所以有活力,是由于它能夠通過實踐進行自我批判,實現自我更新。這種批判主要通過三種不同的渠道進行:一是在探索自然規律中轉變范式,二是在探索社會規范的過程中調整取向,三是在探索心理現象的過程中進行反省。科學的穎悟正是在上述過程中實現的。
對于科幻電影而言,“反常合道”本身就是一種穎悟。“反常”是對于常情常理的超越,科幻電影的創意因此擺脫了既有定勢的局限。“合道”則是對于更深刻、更廣闊的情理的回歸。從黑鏡科學的角度來審視科幻電影中所出現的各種似是而非的假定,我們不難發現“反常合道”的價值所在。例如,在我國《天才J之第二個J》(2018年)中,所謂“命運公式”和“偶然公式”貌似科學(既把握規律,又實現量化,同時還有以之為基礎的成功預測作為佐證),實際上純屬虛構。盡管如此,它卻深刻地揭示了如下哲理:命定論、偶然論看起來體現了人類作為有生命的存在物所固有的受動性,卻在一定條件下為體現人類所特有的能動性開辟了空間。“命運公式”寓指萬事皆由前定,“偶然公式”寓指萬事皆非必然,二者的對抗看起來是分別掌握這兩個公式的天才(主人公阿J和顧先生)之間的較量,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哲學觀念之間的博弈。如果能夠將二者統一起來,融而化之,那就是無與倫比的穎悟。該片編導還想到一個辦法將這種哲學分歧和民眾生活聯系起來,這就是讓顧先生設法通過智能電腦竊取天眼系統的用戶數據。這些數據是天眼系統通過全面監控搜集來的,關系到千百萬人。倘若掌握了它們,顧先生就可以用“偶然公式”來對付他們,這危害實在太大了。為了挫敗他的陰謀,阿J服藥進入自閉狀態,公司則關閉數據庫。但是,顧先生利用阿J的克隆體郭佑攻破心率鎖“鑰匙人”劉小凡的心理防線,從而進入數據庫。因此,戰斗正未有窮期。顧先生所進行的這種攻擊已經超出純觀念的黑鏡科學,而涉及下文所說的黑鏡技術了。
二、黑鏡技術與科幻電影創意
技術既是科學在具體領域的應用,又是科學研究所需要的支持條件。技術與工具好比硬幣之兩面。技術是工具的精神化,工具是技術的物質化。工具制造體現技術所達到的水平,技術開發決定工具所具備的性能。技術可以按不同標準予以分類,如根據行業應用分為農業技術、工業技術、服務業技術等;根據工程屬性分為材料技術、能源技術、信息技術等。就科幻電影而言,我們主張從內容角度區分如下三類技術:(1)常規技術。特點是合乎自然規律,遵循社會規范,有益心理健康。縱使現在還沒有,只要經過努力,水到渠成,總是會開發出來,并獲得應用。(2)黑技術。指違背自然規律不能開發,違背行為準則不準開發,或有害心理健康不宜開發的技術。縱使現在已經有,只要被發現,就有可能被禁止。有時,這一范疇又指雖然已經存在但卻保密,遠遠超出同行水平的技術。(3)黑鏡技術。雖然因為違背我們所處世界的自然規律而不能開發,但卻有望在遵循不同規律的其他世界中得以開發;雖然因為違背我們所處社會或時代的行為準則而不準開發,但卻有望在遵循不同準則的社會或時代中得以開發;雖然因為違背我們所屬族類的邏輯要求而不宜開發,但卻有望在遵循不同要求的族類中得以開發。科幻電影通過對上述“不同”條件的構思,為“我們”的世界、社會、時代、族類的技術發展昭示了新的可能性,使人類從更廣闊的角度審視技術的價值和前景,這同樣是體現藝術精神的“反常合道”。
(一)亮起:技術水平與工具的分類
與技術一樣,工具可以按照不同標準予以分類。在任何科幻電影中,幾乎都可以發現有關工具的描寫。這些工具大致可以依其來源區分為兩類:一是天然工具,如美國《金剛之子》(The Son of Kong,1933年)、法國《伊甸木》(Eden Log,2007年)中作為武器的樹枝等。最為吸睛是那些有奇效的工具,如我國《賽爾號2·雷伊與邁爾斯》(2012年)中圣靈系精靈能夠生成保護盾的幻影寶石,我國《丑小鴨歷險記》(2016年)中烏鴉長老用以甄別來自月亮的機械鴨的身份并預測其未來的水晶球,等等。不過,它們通常并非科幻電影的特色,因為在神話、玄幻、魔幻之類影片中不乏此類構思。二是人造工具,其中有些是普通工具,如我國短片《倫敦魅影》(2013年)中的電視轉播塔等。該片之所以躋身科幻之列,是由于描寫外星人青青計劃利用它發射病毒以馴化觀眾。至于電視轉播塔本身,沒有超過人類現有的技術水平。另外一些是“超工具”,即超過人類現有技術水平的工具,如中國香港《想飛》(2002年)中可以將人類即時虛擬化的三維成像工具等。
以人類現有技術水平為標準,可以將科幻電影中所出現的超工具區分為以下三類。
一是超級工具。它們雖然目前屬于幻想,但未來或許可以造出來,如美國《飛俠哥頓》(Flash Gordon,1936年)中可以使人隱身的機器,美國《蝙蝠俠歸來》(Batman Return,1992年)中可以變成直升機的雨傘,我國《超能特務》(2016年)中用于通信聯絡的手臂植入芯片,我國《鋼鐵飛龍之再見奧特曼》(2017年)中可以無線遠程升級的智能機甲,我國《生化英雄之奪魂》(2016年)中可以引發基因重組的針劑,等等。
二是超能工具。它們是人類永遠造不出來的,如永動機等。倘若說超級工具代表有望轉變為現實性的可能性,超能工具則代表無法轉變為現實性的可能性。前者之所以目前不存在,主要是技術難度問題;后者之所以將來也不會存在,主要是違背科學原理問題。例如,臺灣地區《詭絲》(2006年)設想了“孟杰海綿”,它可以吸收附近的電磁波,將鬼魂收納其中,分體成簾將人鬼隔開,這正是超能工具之例證。“超能”有時又稱為“異能”或“超能力”,對人來說主要是指無法用人體科學來解釋的能力,對工具來說則是指無法用自然科學解釋的技術。能力與技術在某些條件下是相通的。例如,我國《超能廢物》(2016年)描寫異能局擁有監控各地異能波動情況的系統,若有人使用超能力,馬上就能發現。某些科幻電影試圖將超能者與超能工具的影響擴展到公眾之中,以強調其重要性。例如,在我國《超能聯盟之極品天使》(2018年)中,院長計劃將自己研制的試劑添加到供水系統,以控制市民,結果其陰謀被三位異能者粉碎。
三是超性工具。這是擁有自覺意識的工具。它集中體現了工具本身所包含的價值悖論。在現實情境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背反:一方面,工具是為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務的;另一方面,工具自身可以成為人類活動的目的。在科幻情境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悖論:人本身是為其他存在物服務的工具,工具反倒成了具有明確自我意識的主體,因此實現超性化。契機可能是偶然的外部原因,如美國《霹靂五號》(Short Circuit,1986年)中機器人遭雷擊;也可能是內部進化,如日本動畫電影《攻殼特工隊》(Ghost in the Shell,1995年)中的黑客程序傀儡王演變。相關的影片還有美國《傻子》(Puzzlehead,2005年),美、澳、新合拍片《絕密飛行》(Stealth,2005年),我國網絡大電影《墓志銘》(2016年)、《來自火星的她》(2017年),等等。若從技術水平判定,這類工具是人類所不可能造出來的,如果奇點的到來需要有外在于人類主觀努力的因素的話。它們又是人類在理論上應當可能造出來的,如果我們承認技術進步是大趨勢、大概率,那么,早晚有一天人類會以造出超性工具標志著自身進入了新階段、新境界。不過,這同時意味著對人類的否定,因而也是悖論。
(二)黑入:技術弊端與工具的批判
自從初民運用工具以制造工具之后,就有了技術。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迄今為止人類的歷史就是技術進步的歷史,或者說技術進步在人類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盡管如此,技術的進步有時意味著人類技能的退步,技術的應用有時意味著人類廝殺的升級,技術的登臺有時意味著人類的下臺。正因為如此,某些人對技術無節制的發展憂心忡忡,另一些人雖然對技術的副作用保持警惕,卻又不遺余力地發展技術,因為不這樣做就要落伍,就要在人與人的競爭中挨打。技術本身并非無差別的整體,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者相反)的較量在技術領域同樣清楚地表現出來。正因為如此,常規技術包含了自身的否定因素,即黑技術。它可能意味著水平高到足以淘汰常規技術的地步,也可能意味著包含了與常規技術相對立的價值取向。技術進步就是在常規技術與黑技術的矛盾推動下實現的。
科幻電影是在技術的孕育下誕生的,但這并不妨礙它認識其弊端并予以揭露和批判。就創意而言,科幻電影“黑入”技術界至少有如下途徑:(1)展示技術人員的不能免俗,譬如,也有瘋狂、野蠻或利令智昏的時候。不僅如此,他們對技術執迷不悟的愛好有可能導致某些損人不利己的行為。美國《隱身人》(The Invisible Man,1933年)可以為例。(2)展示技術服務的消極后果。人們因為訴諸技術而獲得了諸多便利,但是,倘若過分依賴科技,或許“人將不人”。例如,我國《天眼計劃》(2017年)描寫人們依賴手機,迷戀手機游戲,在玩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泄漏自己的各種信息,甚至被別有用心的人監控。(3)展示技術中介的利欲熏心。技術中介本來是為溝通技術主體和技術對象服務的,但是,他們有向利益集團演變的趨勢,甚至反過來操控技術主體和技術對象的命運。像我國《天眼計劃》中的董事長雷恩就是如此。(4)展示技術手段的負面價值。例如,香港《黑俠2》(2002年)中的基因炸彈若爆炸的話,可以將全城居民怪物化。又如,我國《太空熊貓總動員》(2014年)中的熊貓控制器是鼠司令用來吸引追隨者的,對熊貓本身只有害處。(5)展示技術內容的巨大風險。例如,我國《天才J之謎題里的倒計時》(2018年)描寫事關40億人安全的大數據落入野心家手里。(6)展示技術本體的失控狀態。以日本“哥斯拉”三部曲(2017—2018年)為例。機械哥斯拉本是人類為對付怪獸哥斯拉而制造出來的武器,它被廢棄后繼續自動運作,吸收納米金屬,自動復制加工,不斷發展壯大。(7)展示技術方式的違背人性。例如,我國《別懟我之暴走校長》(2018年)描寫想要成批制造天才的冒牌校長利用機器強行灌輸知識,結果弄得接受實驗的學生七歪八倒。(8)展示技術環境的生態惡化。例如,在美國《宇宙靜悄悄》(Silent Running,1972年)中,人類已經能夠翱翔太空,但地球上所有植物卻趨于滅絕。(9)展示技術機制的難乎為繼。例如,我國《太空熊貓歷險記》(2013年)描寫天狼鼠王使出黑暗隕石——基因異變武器,太空熊貓用基因精靈——五行能量對敵。他們的交戰引發宇宙大爆炸。
(三)穎悟:反常合道與科幻的思路
從黑鏡技術的角度來觀察科幻電影所描寫的超工具,我們發現了“反常合道”原則的具體化。超工具能否造出來,取決于相關技術是否符合自然規律;超工具是否應當造出來,取決于相關技術是否符合社會規范;超工具是否需要造出來,取決于相關技術是否符合價值判斷。科幻電影不僅考慮到上述常情常理,而且將超工具及相應技術置于反常條件下予以構想,描寫人們造出了正常情況下本來造不出、不應造、不值得造的超工具(或者說開發出了相應技術),操作目標是借以展示它所可能導致的自然變動、社會變動和心理變動,根本目標則是揭示人性的奧秘。例如,美國《基因世代》(The Gene Generation,2007年)描寫海登博士擅自使用其屬下克里斯汀所開發的代碼轉換器,結果將自己變成怪物,站立在籠子里,對生物編碼的利弊加以思考。這種工具能夠即時重組DNA,可以瞬時治愈所有疾病,但也是潛在的武器。除了發明者之外,其他人操作它,都會面臨不可預測的后果。我國《生化英雄之奪魂》(2016年)描寫了一種可以引發基因重組的針劑。其效果取決于被試者原先的人格特征。用曾經參與開發的鐘逸的話說,藥物只是起放大根本基因的作用。“你吃完藥有什么樣的表現,就說明你是什么人。”
科幻電影還揭示了人的工具化的可能性。例如,在上述《天才J之第二個J》中,螞蟻金服公司總裁助理劉小凡被選定為天眼系統數據庫的“鑰匙人”(Keyman一詞的字面意義),因為他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跟隨李總多年,對公司忠心耿耿;二是情緒起落幅度大,關鍵心率不易被捕獲。劉小凡的心率波動越大,對應的天眼系統數據庫被啟動的可能性就越低。上述兩個條件是矛盾的。為保證其忠誠,公司高層強調他所肩負的責任的重要性;為保證他不嘗試用關鍵心率擅自啟動數據庫系統,公司高層有意冷落他,直到予以開除。處在這樣的矛盾體驗之下,劉小凡后來終于中了陰謀家顧先生的圈套。該片中的“鑰匙人”實際上也是一種超工具。
三、黑鏡藝術與科幻電影創意
以上所述的黑鏡科學與黑鏡技術可以統稱為“黑鏡科技”。我們稱科幻電影為“黑鏡藝術”,正是由于它將黑鏡科技置于前景,作為區別于其他類型片的主要標志。科幻電影本身的創意同樣遵循“反常合道”的原則。藝術的“反常”有多種涵義,其中最重要的是下述三條:不同于令人遺憾的常態,不同于令人厭倦的常事,不同于令人拘束的常規。藝術的“合道”也有多種涵義,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三條:一是憧憬性,將理想的光輝投射到作品所描寫的情境中,令遺憾在想象中得到滿足;二是虛構性,將假定當成塑造人物、設定背景、展開情節的基本方式,并且公開聲明作品內容的假定性,從而給受眾以新鮮感,讓他們接觸新事物,開拓新眼界;三是創造性,將不同于既往、既有、既定當成自己的追求,運用新手法,形成新風格。上述特點對科幻電影產生了深刻影響。與此相應,我們可以從憧憬性、虛構性和創造性的角度來認識科技電影中有關工具的描寫(它們是科技內容的具體體現)。
(一)亮起:科技內容的憧憬性
憧憬性是以人的愿望為標準來衡量的,總是呈現為亮色,而且總是指向未來。相比之下,不符合人的愿望的對象具備遺憾性,后者總是呈現為灰色,而且總是指向過去。在強調幻想之特色的類型片中,為了彌補遺憾、實現憧憬,人們往往訴諸法寶。例如,我國網絡大電影《異能少年之末路反擊》(2018年)中的焰心石是帝王陵密室最有價值的寶貝,可以使持有者滿足心愿,但只限三秒鐘,而且使用多次后效力消失,變得暗淡無光。它是盜墓者覬覦的對象,也是天心月復仇的依托。自從科學昌明之后,人們轉而寄希望于作為工具與產品之統一的科技,后者也確實為滿足人們的愿望提供了新的條件。不過,如果直截了當地將科技當成體現憧憬性的手段或途徑的話,那只是科普電影的思路。科幻電影往往采取另一種做法,即描繪科技發明或應用所帶來的新遺憾。例如,西班牙《電氣旅館》(El hotel eléctrico,1908年)描寫顧客聽信宣傳入住電氣旅館,以為可以享受一番,沒想到因那兒出故障而被弄得狼狽不堪。美國羅伯森(John S.Robertson)執導的《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1920年)描寫醫學博士亨利發明可使身體變形的魔藥,以為可以體驗人生,沒想到是毀了自己。在美國《逃出克隆島》(The Island,2005年)中,管理人員用謊言欺騙克隆人,所描繪的理想世界其實是摘取他們新鮮器官的實驗室。為了消除上述科技誘生的新遺憾,我們究竟該做些什么呢?這是許多科幻影片試圖引導觀眾思考的問題。
(二)黑入:科技內容的虛構性
所謂“虛構性”是相對于現實性而言的。在日常交往中,人們之所以需要虛構,往往是由于不便直言。畢竟不吐不快、有為而作,但又要回避矛盾、減少風險,因此訴諸虛構。藝術將虛構當成自己的特色,固然存在自我保護的動機,但更重視擺脫現實束縛之后自由想象的快樂。進入網絡時代之后,黑客在線活動也有虛構身份的時候,目的主要是轉移目標,避免被安全專家(或安全程序)識破。以上所說的是主體身份的虛構性。以下所說的是科技內容的虛構性。
從創意的角度看,科技內容的虛構性是以工具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可能性為標準來衡量的。如果真的存在過(如今可能有,也可能沒有),那是具備歷史的現實性。如果現在就有(過去可能有,也可能沒有),那是具備當下的現實性。如果未來必定會有(此前可能有,也可能沒有),那是具備未來的現實性。其中,凡是只在特定時段才能擁有的,可以視為具備純粹意義上的時段現實性,包括純粹歷史的現實性、純粹當下的現實性、純粹未來的現實性。由于當代科技水平比古代高,因此,多數古代存在過的工具即使一度消失,也是可以被仿制出來的。如果未來科技水平比現在高的話,那么,未來人同樣可以仿制現代人所擁有的各種工具,即使它們已經失傳,只要他們意識到其存在。
從技術的角度看,工具至少在下述意義上可能是虛構的:(1)科學意義上,指人類過去、現在、未來都造不出來,如永動機。(2)歷史意義上,從特定人類共同體的整體發展水平看,某些工具是可以造出來的,但未必真的存在過,原因可能是當時人們并未意識到對它的需要。(3)倫理意義上。用特定人類共同體的技術水準衡量,某些工具完全可以造出來,只是社會規范不允許,因此沒有存在過。
藝術將“虛構”理解為即使聲明其存在仍不失效用的假定性。至于其范圍,其實是沒有限制的,如果它以純粹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或藝術自由為自己辯護的話。不過,它不能違背樣式規范,例如,不能聲明是科普片卻違背公認的科學原理,不能聲明是歷史片卻違背公認的歷史事實,不能聲明是倫理片卻違背公認的行為準則。盡管如此,科幻電影中的下述內容又是允許的:(1)雖然違背公認的科學原理,但卻表達了探索客觀真理、人類良知或宇宙規律的熱望。因為“公認”實際上是受一定社會歷史條件限制的,被公認的科學原理未必等于絕對真理,所以我們不能反對藝術家就“公認”的相對性加以探索。藝術家完全可以表現科學工作者出于良知而和科學共同體發生的沖突,這正是人性的一種表現方式。(2)雖然違背公認的歷史事實,但卻表達了探索客觀過程、人類良能或社會規律的動機。歷史上雖然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進而現實中沒有,甚至未來也不會有),但是,藝術家可以假定它發生過(同時不憚于聲明“此事出于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以此為前提,探索人性在這樣的條件下有什么表現。(3)雖然違背公認的行為準則,但卻表達了探索主觀世界、人類良心或心理規律的意圖。對于特定人們共同體而言,不論從道德、禮儀或法律的角度看,都有些事情屬于不允許做的范圍。但是,藝術家可以假設某些人做了,或者另一些人們共同體允許這樣做,或者某些異乎尋常的條件下只好、只能、只得這樣做。以此為前景,探討人們為什么這樣做(這也是人性的一種表現)。
(三)穎悟:科技內容的創造性
科技內容的創造性是以它們與既有理論和實踐的相關性為標準來衡量的。真正獨創的科技內容不僅歷史上沒有過,現實生活中未曾有,甚至還沒有其他人想到過。但是,正如俗話所言,“說有易,說無難”,指出某種存在物有所依傍相對容易,指出某種存在物無所依傍非常困難。例如,可以說我國《流浪地球》(2019年)中建造行星發動機、推動人類所在行星離開即將毀滅的太陽系是創造性的解決方案。但若仔細推敲的話,這樣說還是有點問題的。且不論在該片據以改編的原著誕生之前科幻界有否類似構思,單就利用發動機驅動交通工具這一點而言,那肯定是盡人皆知的常識。雖然這部影片大膽將地球本身當成了交通工具,但詩人不早就寫過“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毛澤東《七律二首·送瘟神》)嗎?其實,評價科技內容的創造性還可以有另一個標準,就是將參照系由作者創作所在的意義網絡轉移到觀眾鑒賞所在的意義網絡。如果科幻影片所提供的某種科技內容激發了觀眾眾多的聯想、議論,那么,應當說它是有創造性的。這便是后結構主義者所說的“可寫性文本”,[2]155符合互文性的要求。就此而言,《流浪地球》是很成功的。除此之外,依然可以有第三種標準,亦即將作者與觀眾溝通起來的作為中介、平臺或IP(知識產權)衍生品的意義網絡。從互聯網思維的角度看,如果科幻影片以其科技內容形成了眾多鏈接,激發了再創作熱,那也應當被認為是具備創造性的。從心理的角度看,穎悟是大腦中眾多暫時神經聯系的出乎意料的突然整合,我們不妨以此觀察科幻電影給整個社會的意義網絡帶來的變化。如果它所呈現的科技內容給世人帶來了新視角、新理解、新熱點,這就是促進了社會心理中的穎悟,因此也應當從創造性的角度予以肯定。
上文依次探討了黑鏡科學、黑鏡技術、黑鏡藝術和科幻電影創意的關系。它們都遵循“反常合道”的原則。“反常合道”雖然誕生于我國古代,但直到如今仍有其適用性。科技內容在科幻電影中的異常演繹完全可以充當它的注腳。反過來,上述演繹又豐富了“反常合道”的含義,證明了我國古典文論與當代影像藝術之間良性互動的可能性。我國科幻電影要想形成自己的特色,條件之一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將傳統美學觀念和當下藝術實踐有機結合起來,這正是本文以“反常合道”和“黑鏡”為參照系探索科幻電影創意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