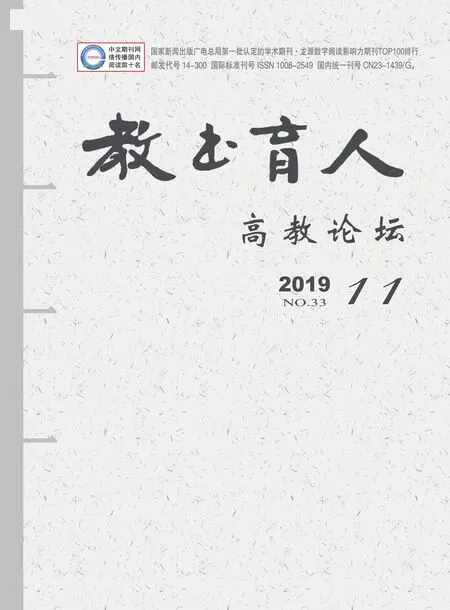“遭遇”價值下高校思政教育的創新途徑
袁秋月 (西南大學教育學部)
一 “遭遇”的內涵及教育價值
(一)“遭遇”思想的形成
“遭遇”是德國教育人類學家博爾諾夫非連續性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范疇。博爾諾夫繼承了存在主義哲學和文化教育學關于人非連續性發展的思想,并在非連續性發展觀的基礎上創建了他的非連續性教育思想。在系統論述非連續性教育的基礎上,博爾諾夫著手研究非連續性教育的范疇和形式,遭遇作為其中的重要一維受到博爾諾夫的重視,他在專著《教育人類學》一書中詳細闡述了他的遭遇思想,包括遭遇的內涵,遭遇的教育意義等。
(二)“遭遇”的含義及教育價值
博爾諾夫認為“只有少數重大的特定的經驗可以稱作遭遇,它們闖入人的生活,突然地、往往令人痛苦地中斷人們的活動,使之轉向一個新的方向。這主要涉及與他人的遭遇,他們命中注定要進入人們的生活(在教育領域與教育者的遭遇)。”縱觀已有研究,學界對遭遇教育價值也做了較多的探索,指出了“遭遇”在學生生命發展的意義和作用。但已有研究主要從宏觀上探索其在教育中的應用,且多集中于中小學生教育,鮮有文獻研究“遭遇”機制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關系,本文僅對兩者的內在聯系做初步探討,以期對高校思政教育的創新有所啟發。
二 “遭遇”機制為思政教育提供新途徑的可行性
(一)理論依據
博爾諾夫對“遭遇”的地位做了以下闡釋:“如果要對精神世界產生真正的內在的理解,真正的遭遇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教學必須拓寬文化知識,闡明理解范圍。在這些基礎上才會產生充分的遭遇。但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產生真正的觸及人心靈深處的、改變其全部生活的遭遇,那么所有的文化知識都不起作用,所以也就無關緊要了。”從博爾諾夫的闡述中,可以看出“遭遇”與常規教學并不是對立的,因為非連續性事件的教育意義本身也要以連續性教育為基礎。強調“遭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創新性不是要完全摒棄以往的教育形式,而是在思政課程的基礎上建立起“遭遇”機制,讓遭遇的發生成為可能。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將思想成熟和政治立場的建立看成是連續的、理性生成過程,強調外部環境靜態、線性的和確定性,忽視大學生成長和生命發展過程的非理性、動態的、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實際上,這些外部因素以突然的、令人震驚的形式出現往往可能改變大學生對思想政治的立場和態度,引發大學生的自我反思以及對人生的重新審視與抉擇。因此,“遭遇”的機制無疑豐富了對高校思政教育的認識,為其提供一種新的途徑與思路。
(二)現實依據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強調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要求創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在2018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指出,“要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工作的主線,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識教育、社會實踐教育各環節,貫穿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各領域。”但目前高校思政教育仍局限于思政課程、輔導員談話、專題講座等“說教”形式。以“遭遇”為切入點,可以發現師生交流、名著選讀、教育口號、課程教學等都是大學生思政教育的重要遭遇事件。在實際的教育過程中,可以充分挖掘輔導員、授課教師、課程教學、名著閱讀等教育要素,努力實現“全員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標。
三 “遭遇”機制下創新高校思政教育的途徑
根據博爾諾夫的闡述,遭遇的來源可能是某個人、某部作品、某句話,也可能是其他教育事件,結合當今高校思政教育的具體情況,筆者認為可以從改變師生交流方式、鼓勵學生閱讀經典名著、巧用教育口號、營造良好思政教育氛圍這四個方面來構建“遭遇”機制下的高校思政教育。
(一)“一個人”:教師“喚醒式”交流
博爾諾夫認為,在人的心靈深處存在著一種所謂“本源性”的道德意識,這種道德意識通常處于沉睡狀態。“教育的責任之一就是喚醒受教育者處在沉睡狀態的道德意識,使他們回到本源上去,使一個人可能真正認識自己和自己所處的世界,同時也理解自己的當下處境、歷史及未來,使一個人對生命充滿渴望。教師如果以恰當的方法和時機給學生以心靈的震撼,就會空前增加他的自我意識。教育就在于不斷地通過對人的‘喚醒’,使人不斷開拓新的生活。”因此,無論是在思政課、通識課、專業課上,還是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授課教師和輔導員只有帶著“喚醒”導向的意識去與學生交流,師生之間才會有真正的精神交流與心靈對話。非連續性教育的“喚醒”、號召等形式,體現了教師對學生的關愛,這種平等式的“喚醒”將打破傳統思政教育中耳提面命式的“說教”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尊重與引導。思政教育中的“喚醒式”交流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喚起學生內心潛在的自省意識,使其“直觀”自己的不足與錯誤,從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二是喚醒學生的危機意識,讓他們正視社會中的動蕩與危機,從而直面自己作為新時代青年,對國家的責任與擔當。實現“喚醒式”交流需要教師以平等的、交心式的態度去與學生交流,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內心世界,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學生自身的想法,強制“洗腦”,如果教師能真正以喚醒的心態去面對學生,思政教育將會呈現出一種全新的面貌。
(二)“一本書”:發揮經典著作的震撼力
從“遭遇”思想看,一部經典著作對人的震撼作用往往可以改變一個人的人生軌跡,例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洗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如今的高校思政教育忽略了名著的影響力,實際上,無論是馬列主義作品集還是我國革命偉人著作,抑或文學巨作,都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可替代的震撼作用。經典著作難以發揮其“遭遇”作用是因為當代大學生閱讀量少,閱讀質量亦不高,即使各專業都開展名著選讀課程,但大多都是為了應付閱讀任務,走馬觀花,最終流于形式。要激發名著閱讀對人的震懾能力,必須提升大學生閱讀經典的“質”,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第一是要鼓勵學生讀原文,在碎片化閱讀盛行的時代,少有學生能完整品讀經典,自然也難有深刻感悟。只有原原本本研讀經典,才能品味語言的魅力,邏輯的力量,從而挖掘到原著蘊含的思想和價值導向;第二是教師需點燃學生的閱讀激情,學生的閱讀興趣往往需要教師帶動,教師可以創新名著選讀授課模式,營造良好的閱讀氛圍,一旦學生在某部著作中感到“沖擊”,便會主動探索更多經典;第三是基于實踐感悟經典,經典名著之所以能讓人感到震撼,是因為人們在其中找到了“自我”的某些影子。在閱讀經典時,若能結合具體的實踐,聯系自我的困惑,反觀自己的人生,必定會在某些片段感同身受,反思原有的思想觀念。
(三)“一句話”:“催化”思想的轉向
在我國的教育活動中,教育口號常常發揮著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為了一切學生”等都是大眾所熟知的話語。根據博氏的非連續性教育思想,非連續性事件都伴有極大的強度。教育口號都帶有強烈的情緒色彩且具有鮮明的導向性和強大的宣傳號召功能,同樣是促進大學生發生“遭遇”碰撞的非連續性教育事件。教育口號雖短小卻精悍,短短“一句話”就有可能對大學生思想轉向產生催化作用,創新高校思政教育不應忽視教育口號的引導干預功能。
盡管教育口號可以有多種表現方式,但任何一種話語方式都是一定思想的表征,都是一定教育價值觀的載體。在各種新潮教育思想的影響下,一些極端的教育口號層出不窮,如“只要學不死,就往死里學”“為國學習,努力自愛”......種種話語使得大學生靜默無聲地服從“教育口號”的訓導,但難以從心理層面達成真正的理解與共識,且很可能出現逆反、抵制等現象,這與“遭遇”思想的“號召、喚醒、警示”作用背道而馳。想要教育口號發揮思政教育的作用,首先,要端正教育口號背后的指導思想,堅持以科學的思想來指導教育口號的制定;其次,還要注意教育口號表達的方式,從規訓的單一方式走向多元對話的方式,煥發教育口號的詩意魅力;此外,教育口號的制定還需結合大學生的現實生活,即“標語口號提出的要求應適當超越受教育者目前的思想品德基礎,有提升其思想品德水平的可能,同時這一超越又不能高到教育者經過努力也難以達到的高度。”總之,既要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又要凸顯對大學生的人文關懷。
(四)“一種氛圍”:營造“處處思政”的新環境
根據博爾諾夫的理論,遭遇作為教育過程中必然的東西,無法回避,只能正視。但“一種認真對待自己使命的教育必須能引導成長著的一代人與精神世界的人物進行這種決定的遭遇,所有的教學都要以此為方向。”可見,我們雖然不能預料某個特定的遭遇,但我們可以在盡可能大的范圍內創設一種遭遇的“良好氛圍”,以期使遭遇發生后朝一個好的方向發展。由此,學校的思政工作不在于道德說教,不在于向學生灌輸一系列的律令和法則,而在于營造一個“處處思政”的環境,日常生活、日常行為思政化,使學生處處都能感受到“正能量”。具體地講,校園里的物質氛圍、精神氛圍、制度氛圍、行為氛圍,都是高校思政教育的隱形資源。目前,已有許多高校在嘗試創設新的思政教育氛圍,例如江西的某些高校建立了“黨委書記面對面”“校長約吧”、學校領導“雙體驗日”等制度,成立了江西高校網絡思想政治中心,并搭建了贛教云服務平臺和課堂資源的共享服務中心。正如江西省教育廳廳長葉仁蓀所說,通過這些新形式能讓思政工作入腦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