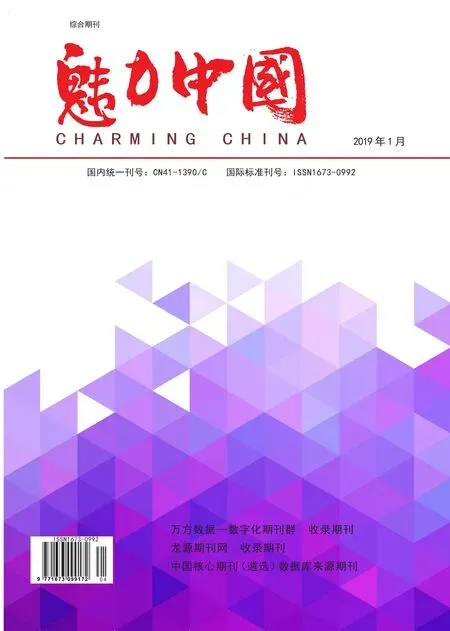從《逍遙游》談人物形象的塑造
閆興保 郝瑜 李錦濤
(武警警官學院,四川 成都 610213)
一、《逍遙游》中人物形象特點
《逍遙游》中獎人物的狀態鎖定在“逍遙”之中,隨風而舞,或疾或徐,頗有一派“鳥歸山林,魚回深池”的喜悅,該作品中雖然沒有具體的人物形象名稱,但是卻代表了這樣一個人群——隱士。隱士的人格特點是尋求詩意的棲居,是人性的一種回歸,是對仕隱情結的一種解脫,寄豪情壯志于大自然,游歷在山風間,從漫步晨光秋風掃落葉的無人之境到沉醉于山水風流間的秀美,看慣了爾虞我詐,便要到自然中去逍遙,羽化成風就要飛翔。
二、《逍遙游》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莊子》變形人形象中,還有一群特立獨行趨于神化的人——神人、至人、真人、德人、圣人等,他們身上有著莊子所認同的理想人格和處世方式,傾注著莊子對人生最高境界的向往。所以,他們的出現與莊子的人生追求密不可分。鑒于此,下文我們通過了解莊子的人生理想,試著去理解莊子塑造這些神奇人物的緣由。
崔大華說:莊子思想發源于對人的精神自由(逍遙)的追求。
可見,對精神自由的追求,乃是莊子人生理想的目標。《莊子》開篇即命名為逍遙游,通過描寫背部和翅膀都異常寬闊的大鵬要靠風才能飛翔,船要靠水的厚積才能負載東西等,來表明世間萬物都是有所待的,即是不自由受限制的。包括人也一樣,哪怕像宋榮子、列子這樣忘毀譽忘禍福不求名利超凡入圣的人,也依然是有所不足的。進而指出真正的逍遙: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圣人無名。
可見,莊子所追求的逍遙是一種無待的境界,即擺脫了一切依靠與束縛,達到精神絕對自由的境界。“天地之正”即為自然之道,莊子認為人若順萬物之性循自然之道,以游于無窮的境地,就走向了無待,達到了逍遙。徐復觀說:
人所以不能順萬物之性,主要是來自物我之對立;人情總是以自己作衡量萬物的標準,因而發生是非好惡之情,給萬物以有形無形的干擾。自己也會同時受到外物的牽掛、滯礙。有自我的封界,才會形成我與物的對立;自我的封界取消了(無己)。
縱觀莊子的思想世界,唯有作為最高范疇的“道”有這樣的特質,逍遙意味著沒有物我的界限,即能遨游于無窮的境地,恰與“道”之未始有封和廣闊無垠相契合。從某種程度上說,莊子追求的逍遙境界正是“道”的境界。“道”投射到莊子的人生理想中,成為其最高人生追求。
由此,只要把握“道”的境界就可達到逍遙,獲得絕對自由。不過,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可知,“道”不可聞不可見不可言,并不能為我們器官所感知,理智所了解,而只能通過體認獲得,默默體道之人才是真正得“道”之人,請看:
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
(至人)體盡無窮,而游無朕。
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那么如何體道呢?莊子提出第一步是“心齋”,
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于聽,
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要心志專一,不用耳朵聽而用心聽,不用心聽而用氣去感應。因為耳朵的作用止于聽外物,心的作用止于感應現象,氣乃是空明的故能容納萬物。所以清虛空明的心境,即為心齋。“虛”在此既被理解為“道”的體現,即“唯道集虛”,又是進一步把握“道”的前提,消除世俗的不潔之物,使心靈保持干凈空明是得道的前提。第二步是“坐忘”:
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
要超脫形體的拘執,免于巧智的束縛,和大道融通為一。超脫形體就是要擺脫生理帶來的欲望,免于巧智就是要擺脫所謂的知識活動。沉溺于形體的享受,便會生發出名利富貴的欲望,進而損耗心神。請看: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蕩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可見欲望對人的傷害是極大的,恬淡寡欲寂寞無為,才會讓人身心均受益。莊子云:
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像嬰兒一樣無意識無欲望,福禍自然不會來,在社會中就可以保全自身。舍棄巧智既是舍棄巧智對欲望的推波助瀾,讓人不肆意妄為,也是消解人既有的認知和知識結構,《齊物論》中提到,成心是是非之分和是非之爭發生的根源,而成心多來自于人固有的認知,它限制人認識的高度和廣度,以自己的成見之心去看待世界,世界便多了種種熙熙攘攘的聲音。人既不受外界世俗的干擾,心靈空明容納天地萬物,又從形軀智巧中提升出來,從個體小我通向宇宙大我,便臻至大通的境界了。當人合通萬物沒有自我的封界與是非標準時,便不會受物的牽累,由此就達到了我們之前說的無待的境界。對此,陳少明論述到:“人如何能‘神’起來,這是只能想象而無法普遍經驗的事情。因而從生活意義而言,似乎不再它想成為什么,而在它想擺脫什么。后者有更切實的思想價值。我們知道,要進入‘逍遙’境界的途徑,無論‘無己’、‘喪我’,還是‘心齋’、‘坐忘’,其基本動詞‘無’、‘喪’、‘不’、‘忘’,全是否定性的。它要舍棄的不是某些東西,也不是太多東西,而是幾乎所有的東西。”鄭笠也說:“他對‘道’的認識既不通過邏輯推理的方式,又區別于‘積學以儲寶’式的經驗積累,他不正面地肯定‘有’,而是主張‘無’。對于人世間種種的‘有’,他采取‘無’、‘忘’、‘外’、‘去’、‘棄’等否定、剝離與消解的方式,消解到‘無’,反至‘道’的最高境界。”這些學者的分析,都指出了達到逍遙達到“道”的境界的方式,是對“心齋”“坐忘”等體道方式的進一步深刻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