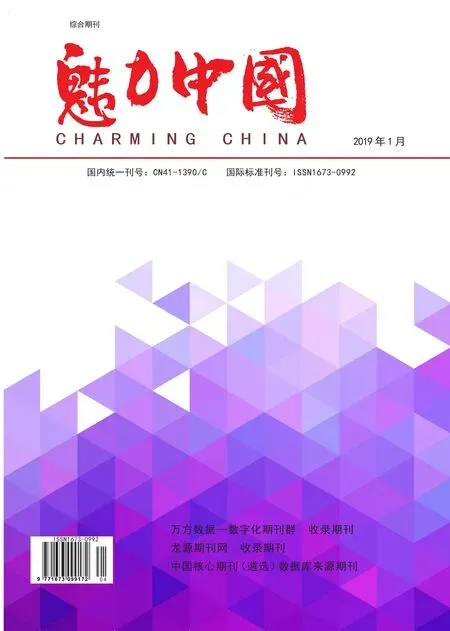周口太昊陵廟的生殖文化崇拜探究
賈柯
(周口市關帝廟民俗博物館,河南 周口 466000)
引言:生殖崇拜是太昊陵廟廟會中民間信仰的一種極具代表性的形式,這種生殖文化與當地民俗文化、廟會文化等存在著緊密的關聯。因此,做好周口太昊陵廟廟會的生殖文化崇拜研究,有助于大眾更好的理解廟會禮儀及各種活動所蘊藏的含義。
一、生殖崇拜文化的出現成因
人類經過漫長的發展,在歷史的長河中終于形成了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文化現象,即:生殖崇拜。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發展,與物質的生產、人類的繁衍息息相關。人類自原始社會階段就已經表現出了對生殖器的崇拜訴求,比如,他們具有強烈的祈求生育、繁衍子嗣的愿望。原始社會時期,社會生產力不足、人口數量較少、生存環境十分惡劣,在其中生存的氏族人類需要應對自然災害、疾病、野獸等危險,當人類發現“人類的壽命僅能維持一段時間,不過利用繁衍的手段可
以實現生生不息后”就明白必須通過“生育”對戰死亡與災難。特別當自然災難造成的影響特別巨大時,人類會產生越發強烈的生殖祈求,為了保證社會生產力充足,原始人就會十分關注生育問題,所以從原始社會便產生了生殖崇拜文化。趙國華在《生殖崇拜文化論》中提出,在人類的原始文化中,“食”是服務于“生殖”的,人類自身的再生產文化即生殖崇拜文化是人類精神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1]
由于人類文明快速發展、更新,在人類的日常生活與工作中生殖崇拜文化的影響力逐漸降低,不過在時間長河中依舊存在,這主要和中國現代文明社會強調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儒家觀念存在很大關系。因此,在尋常百姓的生活中,生殖崇拜依舊存在,并以廟會這種特別的形式,有效的展現在了公眾視野當中。
二、針對廟會中生殖崇拜所引發的習俗展現與生命觀的分析
(一)對“子孫窯”進行扣摸的習俗
周口太昊陵廟中有直接呈現生殖文化崇拜的體現,主要表現為對“子孫窯”的扣摸求子習俗。在太昊陵廟顯仁殿的東北角基臺墻壁上就存在一個“子孫窯”,相傳只要摸一摸便能子孫滿堂。當代社會,去扣摸“子孫窯”的人主要以孕齡婦女為主,在觸摸時必須平心靜氣。相傳,扣摸次數會對孩子的性別產生影響。由此可見,“子孫窯”象征著女陰。與此同時,在原始社會初始階段,當時的人類生產力較低、對生殖繁衍理解不深,僅僅明白女性生殖器在后代生育中發揮的作用,忽略了男性生殖器與性交的價值,因此,崇拜女性生殖器是從原始社會生殖崇拜時期率先出現的。[2]
巫術是人類表示自己對生殖器崇拜的直接體現之一,其中扣摸“子孫窯”行為便屬于巫術的一種。傳統的性巫術也被成為繁殖巫術,生殖及巫術崇拜意識的結合產物就是我們所說的性巫術崇拜。所謂巫術崇拜,指人類希望對超自然利用通過幻想手段加以控制,達到將人類愿望實現的目的,性巫術的使用目的就是為了幫助人類得到生殖能力。
在《金枝》一書中說道“巫術有兩種,首先是基于接觸律原則,通過彼此接觸產生神秘的感染力;其次是基于相似及模仿律原則,通過和相似或模仿的東西觸摸,就能獲得其感染性質。”性巫術具有廣泛的應用意義,首先可以在人類繁衍中運用;其次能夠在動植物繁殖中運用;最后還可以在祈求雨水等中運用。所以,人類希望觸摸“子孫窯”得到生殖魔力,實現生子愿望。因此,女陰崇拜在對“子孫窯”扣摸的習俗中被展現的淋漓盡致。[3]
(二)廟會經跳舞與生殖崇拜
在廟會舉行期間,人祖爺是必須通過儀式、上香等進行祭拜的,而舞蹈祭祖形式也是不可缺少的環節之一。其中,最為知名的就是經挑舞。經挑舞又被稱為擔經挑,通常由中老年婦女自發的進行組織、表演。相傳,該舞蹈只傳女性、不傳男性,內容以伏羲和女媧為主,舞者需穿全套黑服,還要將2m長黑色紗巾包裹在頭部,黑紗底端有很多長穗,代表龍尾,當舞到高潮時,舞者之間要背靠背相互摩擦,表示伏羲和女媧交合的狀態。[4]
人首蛇身的女媧、伏羲交合的畫作曾在中原南陽地區被發掘而出。當人類進入母系氏族社會后期與父系氏族社會初期后,生活中的男性作用更加突出,原始人利用對飼養牲畜的觀察,逐漸的發現了人類生殖、繁衍的行為方式,并漸漸的了解女性受孕需要直接性交才能實現,所以原始人感覺只有對男女交合使的狀態進行模仿,才能得到強大的生殖力;因此,就演變出了“陰陽交合,始化萬物”的全新生命觀。
同時,巫術也包含經跳舞,經跳舞就是對男女交合形態在進行模仿,他們覺得通過模仿交合行為就能獲得相似的結果,從而實現人類的繁衍生息。同時,面對歌舞狂歡的歡喜氣氛,求子者也可以去深深的感悟,這對婦女生育是有利的。比如在對“子孫窯”扣摸期間,一些人感覺摸一下還不夠,他們一定會在子孫窯中插入手指在摩擦一會,通過對男女交合狀態的模仿,希望獲得強大的生殖能力。
出現經跳舞的原因,首先是對伏羲、女媧對人類繁衍做出的貢獻行為的感謝;其次是人類對男女交合生殖力崇拜的展現;同時也直接體現了古代男女暢談情愛、自由交合風氣的意識。而且一部分專家學者將這種行為稱為“野合”的標志性行為,這其中對民間信仰的生命觀進行了有效展現。
周口太昊陵廟會有著很多神話傳說,比如女媧和伏羲滾磨成親、捏土造人,實現了人類的生育繁衍等。之后,伏羲邀請大量的男女通過在太昊陵廟中相識的方式做媒成親。所以,人們給予女媧與伏羲的尊稱是“高媒”。當伏羲逝世后,后人在淮陽太昊陵廟會處將其下葬,并建造了高大的陵墓,通過年年祭拜的方式進行祭祀,由于其香火旺盛,所以就變成了廟會。《周禮》在記載地官“媒氏”的職責時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這就是我國古代著名的由官方召集的男女狂歡的“仲春之會”。《詩經》中的一些篇章,如《溱洧》、《桑中》等等,也都與當時的仲春之會有關。[5]
由此可知,太昊陵廟的前身也許屬于古代男女狂歡的地方。之所以出現了性巫術這種遺留的文化,主要可能和民間信仰觀念存在較大的關系,同時,這也是人類“兩種生產”本能相互鉗制產生的現象。由于農耕經濟生產文化在中原區域根深蒂固,所以每年是否能夠得到足夠的作物收成和當地人存活息息相關,因此,糧食生產與人類繁衍的重要性便不分伯仲。由于原始人對大量事物并沒有明確的區分概念,所以并不知曉人和自然物的明確界限。他們僅僅認為“動植物繁殖與人類繁衍基本一致”。
所以,“類比聯想”這種簡單的思維模式被原始的人類大量的運用,他們始終都認為人類生命的繁衍和農業的發展原因一致,并互相影響。因此,人生觀與農事觀系統聯系越發緊密,并逐漸演變成了人類民間傳統的主流信仰觀念系統,同時也讓“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命觀”在民間信仰中得以顯現、流傳。所以,每年春天廟會經跳舞舞者會通過對男女交合狀態進行模仿,去感受春季神奇而又強大的生殖力,希望借此強化人的生殖水平;其次,也是希望自然環境與農作物能夠被人類的生殖力行為感化,提高其生命活力,實現增產豐收的目的。該現象主要展現了“天人合一”理念,因此可以說“春天的節日和農事信仰、生殖崇拜信息相關,同時春天開展的所有活動均希望發揮生殖感染魅力,從而實現作物的茁壯。”
(三)“樓子”——周口太昊陵廟廟會不可或缺的祭器
相傳“樓子”是人祖爺非常喜愛的祭器,有香樓子、木樓子兩種。在進行人祖爺的祭拜活動或者當某人得子后舉行還愿儀式的時候,會使用木樓子作為祭器。而人祖爺此時則具備了祖先神與生育神雙重身份。
通常楊木是木樓子主要制作材料,木樓子是一根棍子形狀,一頭很尖,和尖頭處相距15cm的棍身處是朝四方向上開口的木斗。木樓子之間體積存在差異,但外表都是紅色或粉紅色。需要求子的人當孩子2歲左右時,便去廟會“請”木樓子,然后在漏斗里裝入貢品等,讓孩子舉過頭頂,并送至太昊陵前恭敬的放置。木樓子生殖崇拜色彩濃厚,專家覺得木樓子頭端的斗型實際上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這是對男根的崇拜;而木樓子上木斗則是對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二者的結合則是對男女交合生殖魅力的崇拜。
木樓子的木斗平面投影是一個朝上開口的梯形,代表女陰,而目光恰巧經過木斗中部穿出,由于木棍代表男性生殖器,所以木樓子整體象征著男女交合形態,而選擇紅色,則是對女性懷孕后經血的象征,由此可見男女交合的生殖魅力還是很受崇拜的。
隨著中華文明的興起以及大量華夏子孫開始尋根問祖、認祖歸宗,太昊陵廟的朝祖廟會已經成為了聲勢浩大的廟會之一。在周口地區的太昊陵廟廟會往往匯聚了天南地北多個省份的人,這里每天朝祖、燒香、許愿的人數以萬計、數不勝數。由此可見祖先的力量極具號召力;不過廟會的底色依舊是生殖崇拜,原因是“人類祖先繁衍的最終需求,實則為生殖崇拜的產物。”在古代發展中,祖先和生殖崇拜往往是緊密交織,無法分割。比如,在紅山文化等古文化遺址開發區,均有石祖等代表男根象征意義的文物出土。而“祖”字古作“且”,在甲骨文中正作挺勃的男根之形,猶“妣”之為“匕”,像女陰。對此,郭沫若先生《甲骨文研究·釋祖妣》已詳細論析。[6]
所以,在太昊陵廟會中,很多人會通過對“子孫窯”的扣摸,希望實現自己的求子愿望,可見人們認為女媧祠與子孫窯密不可分,從而對女陰崇拜文化進行推崇;同時,還會用手指模仿男女交合狀態,渴望借此獲得強大的生殖能力。由于女性生殖作用被放大,所以具有女陰特征的“子孫窯”魅力不斷提升。不過,當期求子成功還愿期間,則通過對鄉鎮男性生殖器的木樓子對人祖進行祭拜,由此對男權地位對女權地位的壓制性進行了展現;不過,這也是對“陰陽交合,始化萬物”生命觀的一種展現。
(四)對泥泥狗的分析
周口地區廣為流傳、揚名四海的當屬淮陽泥泥狗,這是人們在祭祀人祖爺與人祖奶時使用的具有高度抽象變形的物品,是通過口傳心授、流傳至今的重要崇拜物。求子是周口太昊陵廟的主題,因此,生殖崇拜文化含義也深入泥泥狗當中。通常會選擇膠泥制作泥泥狗,然后用輔助設施塑造生動的形象。常見的有神話故事里面的飛鳥、走獸等。完成造型制作后要送入火種焙烤、晾曬,然后用黑色鋪底,選紅白黃綠等對裝飾花紋進行彩繪。而且泥泥狗也具有自己獨特的特點,如選材是遠古內容、技法簡答樸素、顏色古樸大方、造型各異等。根據造型及顏色應分成大花、小泥鱉、中小板三大種類。而泥泥狗以大花貨種類最多,其色澤濃郁,線條用彩色勾畫、黑色墊底,中部又繪有大色塊,最終才得大花之名。
其造型多樣,有兜肚猴、光板猴、貓拉猴、猴頭燕、斑鳩、雞、狗、人頭獸等100多種。大花貨高低不等,一般為7厘米至30厘米左右,較大造型有猴山、猴樹等。泥泥狗種類繁多,姿態各異。不僅僅是以狗為主要表現內容,同時也包括猴、虎、鳥、魚、人等。[7]此類現象具備了明顯的變形特征,其中以鳥變與猴變為主。其中四不像、盤腳猴、猴頭燕等屬于猴變主要類型;斑鳩、雞等飛禽屬于鳥變主要類型。猴變與鳥變都是對女陰崇拜等生殖崇拜內容的體現;其中女陰崇拜主要由猴變體現,男根崇拜則主要由鳥變體現。
以猴變形進行分析,兩只猴子的外形明顯是對雌雄交合含義的展現,其所代表的的就是對男女生殖結合的崇拜,而面猴的紅白色則是對女陰形狀的展現。以鳥變形分析,可以發現男根采用了屹立挺拔的鳥形實現了突出展示,代表男根在生命繁衍、子孫滿堂目標的實現中具有重要價值,側面反映了人們對男性生殖的高度崇拜,代表著當地民眾追求、渴望無上生命、生殖力的訴求。同時,泥泥狗外表中的花葉紋等圖案紋飾,明顯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這屬于崇拜女陰生殖文化的另類體現方式。
結束語:總之,周口太昊陵廟的廟會文化通過借助生殖崇拜文化作為發展底色,在配合展現生殖崇拜的各類行為及活動,有助于人們更好的理解“陰陽交合,始化萬物”的生命觀,對推廣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天人合一的生命觀具有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