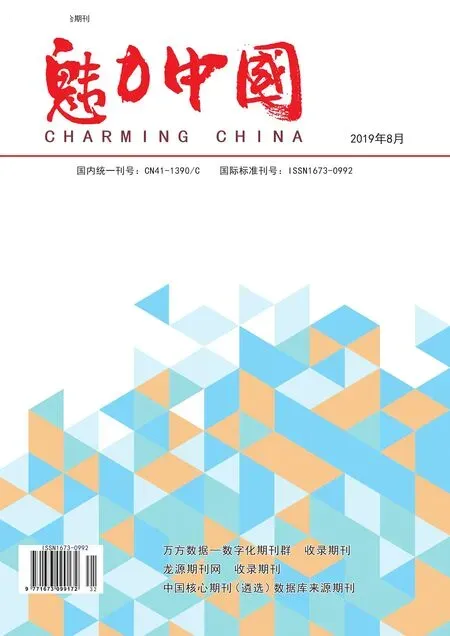巧妙利用生成資源,讓課堂意外變精彩
喬海燕
(河北省張家口經濟開發區第一小學,河北 張家口 075000)
正像我們無法預知我們將來的人生一樣,課堂中將會跳動一些怎樣的音符,我們同樣無法提前知曉,因為學生作為一種活生生的力量,帶著自己的知識、經驗、思考、靈感,興致參與課堂活動,并成為課堂教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而使課堂教學呈現出豐富性、多變性和復雜性。對智慧沒有挑戰性的課堂教學是不具有生成性的,沒有生命氣息的課堂教學也不具有生成性。
一、尊重學生,重視獨特
《新課標》明確提出:“閱讀是學生個性化的行為,珍視學生獨特的感受、體驗和理解”。每個人的知識背景、生活經歷、處境、心境的差異,必然會對同樣的文本產生不同的理解,更何況是充滿奇思妙想的少年兒童。因此,在語文課堂中,要特別重視學生的獨特體驗。
有一次教學《火繞云》時,臺上的小組正繪聲繪色地介紹著火繞云變化多端的形狀,小胡同學突然站起來說:“我認為作者寫得并不美。”一時間臺上臺下面面相覷,所有學生看著我。我稍微停頓了一下,耐下心來追問:“你為什么認為寫得不美?”他說:“因為火燒云的顏色太多了,形狀也太多了,作者應把顏色和形狀結合起來寫。”這個見解真富有創意!于是我繼續鼓勵他來改編課文,小胡展開了想像的翅膀:“ー會兒,天空出現一匹赤色的馬,馬頭向南,馬尾向西,馬是跪著的,像等人騎上它的背才站起來。過了兩三秒鐘,那匹馬腿伸開了,馬脖子長了,顏色越來越黃。看的人正驚呆時,馬變模糊了,好像被太陽烤化了,成了一塊淡黃色的大綢子。”臺上匯報的學生在他的啟發下也都情緒昂揚,紛紛參與到對課本的改編當中。
二、順水推舟,匠心引導
在與文本對話交流的過程中,面對學生在文本解讀過程中出現的錯誤、疑問,老師可以順著學生的錯誤思維,循根探源,找準切口循循善誘,啟發學生自主思考,自悟解決。
在我教學《涼州詞》一詩時,小組交流到“一片孤城萬仞山”這句話,小左同學提出疑問:“城堡是高聳雄偉的,應該是‘一座孤城’,詩中卻用了‘一片孤城’,是不是用錯了?”臺上的同學被難住了,用求救的眼光望著我。這問題是由于學生以往的體驗和文本之間發生了錯位而形成的。一個“片”字,表面上似乎有悖常理,實則精妙無比。我隨“誤”而導,在現實與文本的沖突中點燃學生思維的火花。
師:在我們的生活經驗中,“片”字一般是用在哪些事物上的?
生:一片云、一片樹葉、一片花…
師:這些事物都有什么共同點?
生:看上去都顯得很單薄。
師:那么這詩中的孤城單薄嗎?
生:孤城,孤零零的一座城,確實有點單薄。
生:城被萬仞高山重重包圍,沒有依靠,很孤獨,很單薄……
師:如果你就是這城中的一名士兵,此時,你的感受如何?
生:孤獨、寂寞,無依無靠。
師:那大家說是“一座孤城”好,還是“一片孤城”好?
臺上的小組代表馬上接過我的話:所以我們組進行一下總結……
在此例中,一個小小的量詞,由于教師很好地抓住了學生即時生成的疑問,喚醒了學生的體驗,從而挖掘出了文本所蘊藏著的豐富的內涵,同時也讓合作學習達到了新的高度。
三、因勢利導,升華情感
法國著名的兒童學家盧梭說:“兒童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如果用我們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們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簡直是最愚的。”在課堂中,當學生的想法與我們預設的答案有偏差,甚至背道而馳時,教師要因勢利導,讓學生充分獨立地思考,不受約束地發言。
請看王菘舟老師在執教《我的戰友邱少云》一課的教學片段。
師:(播放完“邱少云被烈火燒身”的視頻后)面對這樣一位戰士,你有什么話想對他說嗎?在精彩紛呈的回答中,卻出現了一種極不和諧的聲音:“邱少云,你真是一個傻瓜。你應該試著在地上打滾讓火熄滅呀,說不定敵人此時正睡著了呢。”(全場一片愕然)
師:孩子,你不希望邱少云死,對嗎?
師:將心比心,誰不希望自己好好活下去呢?相信邱少云也一定有這種想法,對吧?但是,做為一名軍人,面對殘酷的戰斗形勢,我相信,一定還會有另一種聲音在他耳畔想起。大家聽,另一種更加強烈、更加堅定的聲音在對他說……數秒鐘后,小手如林。
在前面的學習中,學生對邱少云的壯舉已經有了較為深刻的體驗,心中也早已涌動著對英雄的崇敬之心和緬懷之情。也正是因為心中存有對英雄的“不舍”,オ會在學生的心中產生與現實不符的美好愿望。片段中,老師尊重個性,因勢利誘,在有如剝筍般的層層追問中,將學生帶入了深度觸摸文本的境界。在老師的引導下,學生對文本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對生命的理解也逐漸清晰,理性。面對復雜的戰情,面對危險的處境,學生心中強烈的情感得以宣泄、噴發,得以升華,邱少云這一人物形象在學生心中也變得更為豐滿,更為立體。
總之,每一節課都是不可重復的激情與智慧的綜合生成過程。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要尊重學生發表見解和提出的問題的權利,尤其是當學生發出“不和諧的音符”時,需要的是平等,民主,寬容和開放。有了師生互動中的即興創造,教學才成為一種藝術,才充滿生命的氣息,才會讓我們的語文課堂煥發出蓬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