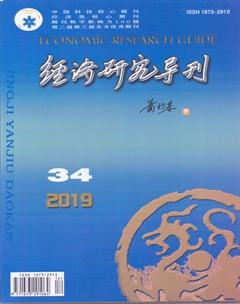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的內(nèi)涵淺析
沈楠
摘 要:財(cái)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chǔ)和重要支柱,構(gòu)建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是推進(jì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必然要求。從歷史發(fā)展、國際比較、政策理論這三個(gè)角度,對財(cái)政制度的內(nèi)涵進(jìn)行分析,認(rèn)為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具有法制性、共治性和全域性等特點(diǎn)。
關(guān)鍵詞: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內(nèi)涵;共治性;全域性;法制性
中圖分類號:F810.2? ? ? ?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19)34-0075-02
一、背景介紹
當(dāng)前的中國經(jīng)濟(jì)是積極融入全球化的開放體系,是國際貿(mào)易環(huán)流中重要一方,正深刻影響著世界經(jīng)貿(mào)格局。但是,目前中國面臨國際貿(mào)易霸凌主義抬頭,以及國內(nèi)經(jīng)濟(jì)下行壓力加劇的雙重考驗(yàn)。如何打贏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jiān)戰(zhàn),如何走出三期疊加這一特殊時(shí)期,是對國家治理的一大考驗(yàn)。財(cái)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chǔ)和重要支柱,必須充分發(fā)揮其職能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biāo)是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jì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圍繞這一改革總目標(biāo),在深化財(cái)稅體制改革方面,首次提出了要建立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另外,在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中,習(xí)近平總書記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了要加快建立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從這些表述中,我們不難看出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的構(gòu)建內(nèi)嵌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biāo)一脈相承。然而,目前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的內(nèi)涵尚屬于探索期,學(xué)術(shù)界并未給出明確的定義。因此,本文試從歷史發(fā)展、國際比較、政策理論這三個(gè)不同的角度,對現(xiàn)在財(cái)政制度的內(nèi)涵進(jìn)行粗淺的分析。
二、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的內(nèi)涵
(一)從歷史發(fā)展角度看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從財(cái)政制度的發(fā)展角度,可以大致將這70年分為三個(gè)階段。
1. 1949—1993年。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94年進(jìn)行分稅制改革,這段時(shí)間無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如何分權(quán),國家在資源配置當(dāng)中都起到了支配性作用。也就是說,在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期,市場發(fā)揮作用的空間非常有限。而此時(shí)的財(cái)政是國家財(cái)政,財(cái)政資金主要用于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包括工業(yè)體系的完善和國有企業(yè)的發(fā)展等,長期忽視了公共服務(wù)的提供。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國家公共部門普遍存在經(jīng)費(fèi)不足的問題,事業(yè)單位也越來越倚重使用者付費(fèi)。而這一時(shí)期的稅收制度,由于1966—1976年這十年非稅論的影響,改革開放前我國稅制非常不健全,僅有6個(gè)稅種,改革開放以后,稅制進(jìn)入了恢復(fù)期,逐步從6個(gè)稅種擴(kuò)張為32個(gè)稅種,形成了稅種雜亂,稅率層級多,內(nèi)外資企業(yè)有別的稅收體系。
2. 1994—2012年。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提出了要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chǔ)性作用,這就要求政府的職能定位發(fā)生轉(zhuǎn)變,政府主要職能應(yīng)定位在彌補(bǔ)市場失靈和不足,以及提供基本公共服務(wù)上。此時(shí),財(cái)政的定位也發(fā)生了轉(zhuǎn)變,從原來的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型的國家財(cái)政轉(zhuǎn)變?yōu)榱斯卜?wù)型財(cái)政。而這一時(shí)期的稅制,也進(jìn)入了深化改革階段。首先,撤并了一些不合時(shí)宜的工商稅,比如說合并了內(nèi)外資企業(yè)的所得稅,實(shí)現(xiàn)稅負(fù)的公平;其次,增值稅從生產(chǎn)型轉(zhuǎn)為消費(fèi)型,進(jìn)一步提高了稅種設(shè)置的合理性。
3.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jìn)入新時(shí)代。現(xiàn)階段我們依然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但也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更好地發(fā)揮政府的作用,提出了國家治理論。國家治理理論是對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期國家分配論的繼承和超越。一方面,國家治理理論認(rèn)同并承襲了國家分配論所依據(jù)的馬克思主義國家學(xué)說,重視國有經(jīng)濟(jì)的主導(dǎo)作用,認(rèn)同政府對經(jīng)濟(jì)的有效干預(yù)。另一方面,國家治理理論是當(dāng)代馬克思主義,它對國家分配論進(jìn)行了修葺。國家治理理論認(rèn)為,政府應(yīng)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定性作用的基礎(chǔ)上,更好地發(fā)揮作用。也就是說,把原來處于對立狀態(tài)的政府和市場統(tǒng)一起來,這使得政府的定位更加清晰,既不把政府職能定位得過寬,又不把政府職能定位在彌補(bǔ)市場失靈和不足這一狹小的領(lǐng)域。現(xiàn)代國家治理,需要一個(gè)有為的政府,一個(gè)善做善成的政府,一個(gè)善治的政府,這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的善治性。與現(xiàn)代國家治理相適應(yīng)的是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是對公共財(cái)政的繼承和發(fā)展,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依然強(qiáng)調(diào)財(cái)政的公共性,只是公共產(chǎn)品的提供,并不是政府一家的“獨(dú)角戲”,而強(qiáng)調(diào)多主體的社會參與。現(xiàn)代財(cái)政將政府與市場的關(guān)系拓展為政府、市場和社會的三元結(jié)構(gòu),政府不僅是治理主體,也是被治理的對象,企業(yè)組織、社會組織、自治組織不再是被治理的對象,也是治理主體。以社會組織為例,政府通過財(cái)政資金支持、購買服務(wù)等形式,引導(dǎo)社會組織的健康發(fā)展。另一方面,社會組織可以通過自籌款項(xiàng),在政府作用薄弱的領(lǐng)域內(nèi),彌補(bǔ)福利供給的不足,為政府減負(fù),這體現(xiàn)的是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的共治性。而這一時(shí)期的稅收體系框架已經(jīng)較為完整,目前18個(gè)稅種也符合我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內(nèi)在要求,但稅收的法律遵從度不高,18個(gè)稅種當(dāng)中,只有6個(gè)稅種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尚有12個(gè)稅種是以國務(wù)院暫行條例方式明確。因此,財(cái)稅體系改革的首要任務(wù)就是完成稅收法定,這體現(xiàn)的是現(xiàn)代財(cái)政的法治性。
(二)從國際比較角度看
1.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干預(yù)不斷增強(qiáng)。從凱恩斯革命開始,資本主義國家一直重視國家對經(jīng)濟(jì)的調(diào)控和干預(yù),尤其是在從冷戰(zhàn)時(shí)期開始逐步形成的新型國際化競爭格局中,資本主義國家干預(yù)經(jīng)濟(jì)的力度、廣度、深度都在增加。比如,美國自2008年以來,為克服國際金融危機(jī)以及進(jìn)行后危機(jī)治理,實(shí)施的一系列的財(cái)政援助計(jì)劃,擴(kuò)張性財(cái)政政策,大規(guī)模的國有化與私有化行動相繼調(diào)整,以及利用先發(fā)優(yōu)勢,獨(dú)享國際市場規(guī)則的修訂和解釋權(quán),長期操控國際市場,瘋狂圍堵和打壓中國復(fù)興。這些事情使得中國政府更加清醒地認(rèn)識到國際市場競爭明明暗暗地顯示出國家發(fā)展權(quán),國家安全權(quán)的競爭,是國家綜合實(shí)力的全方位較量,包括了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和社會等多方面。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chǔ)和重要支柱,財(cái)政必須要從單一的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跳出來,服務(wù)于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gè)全面的戰(zhàn)略布局。也就是說,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的影響范圍具有全域性的特點(diǎn)。
2.資本主義國家財(cái)政法治更為完善。在財(cái)政法制較為成熟的國家,專門性財(cái)政法律可以達(dá)到30—40步,我們還遠(yuǎn)遠(yuǎn)達(dá)不到這個(gè)規(guī)模。目前我們國家已制定的財(cái)稅領(lǐng)域基本體制法,只有預(yù)算法,而實(shí)際發(fā)揮作用的主要是體系龐雜、數(shù)量繁多、效率較低的規(guī)范性文件。法者,治之端也。今年2月25日習(xí)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時(shí)強(qiáng)調(diào),改革開放40年的經(jīng)驗(yàn)告訴我們,做好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各項(xiàng)工作離不開法治,改革開放越深入越要強(qiáng)調(diào)法治。因此,要想在國際競爭的浪潮中更好地劈波斬浪,必須要落實(shí)財(cái)政的法治性。
(三)從政策理論角度看
財(cái)政關(guān)系的四個(gè)要素,包括事權(quán)、財(cái)權(quán)、財(cái)力和支出責(zé)任,前面兩個(gè)“權(quán)”是上層建筑,后面兩個(gè)“錢”是經(jīng)濟(jì)基礎(chǔ)。1994年我國進(jìn)行分稅制改革,形成了財(cái)權(quán)上收中央,事權(quán)下沉地方的財(cái)政格局,導(dǎo)致了地方財(cái)力不足、無法履行財(cái)政職能的困境,也就是說,地方政府存在財(cái)權(quán)小、事權(quán)大,沒有足夠的財(cái)力來落實(shí)支出責(zé)任的現(xiàn)實(shí)問題。此時(shí),財(cái)政關(guān)系的四要素存在失衡。面對這一難題,中央不斷優(yōu)化轉(zhuǎn)移支付方式,著力提升地方政府財(cái)力及統(tǒng)籌使用能力。在地方政府可支配財(cái)力改善的情況下,能夠較好地承擔(dān)事權(quán),落實(shí)相應(yīng)的支出責(zé)任,達(dá)到事權(quán)、支出責(zé)任和財(cái)力的均衡。因此,從結(jié)果導(dǎo)向來看,事權(quán)、支出責(zé)任和財(cái)力的匹配,是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改革的邏輯歸宿。這種邏輯關(guān)系在十九大報(bào)告中也有體現(xiàn),十九大報(bào)告中指出,“建立權(quán)責(zé)清晰、財(cái)力協(xié)調(diào)、區(qū)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cái)政關(guān)系。”這里的權(quán)責(zé)清晰,指的是事權(quán)和支出責(zé)任對應(yīng)清晰,財(cái)力協(xié)調(diào)指的是承擔(dān)事權(quán)、落實(shí)支出責(zé)任要匹配相應(yīng)的財(cái)力。事權(quán)、支出責(zé)任和財(cái)力的平衡匹配體現(xiàn)的是分級財(cái)政制度的規(guī)范化。再看財(cái)權(quán),財(cái)權(quán)是財(cái)力的來源,要想科學(xué)高效地行使財(cái)權(quán),必須要落實(shí)稅收法定。因此,財(cái)政制度規(guī)范化和稅收內(nèi)容規(guī)范化,共同體現(xiàn)的是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的法制性。
三、具體結(jié)論
通過以上三個(gè)角度的分析,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無論從哪個(gè)角度看,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都具有法制性。法制性是構(gòu)建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的本質(zhì)要求,與全面依法治國思想一脈相承,是當(dāng)前財(cái)稅體制改革的首要工作和重要載體。其次,財(cái)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chǔ)和重要支柱,必須全面服務(wù)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現(xiàn)代財(cái)政影響范圍的全域性是新時(shí)代財(cái)政定位的必然要求,是應(yīng)對國內(nèi)外政治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變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構(gòu)建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的基本要求,同時(shí)還是推進(jìn)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發(fā)展的基本抓手。再次,從政府及財(cái)政的職能定位來看,新時(shí)代政府應(yīng)尊重市場,服務(wù)與引導(dǎo)市場經(jīng)濟(jì),在自身財(cái)稅改革逐步完善的基礎(chǔ)上,服務(wù)于現(xiàn)代國家治理體系建設(shè),這表明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改革的核心問題是正確處理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guān)系,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的共治性。共治性是構(gòu)建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的核心要求,政府在處理與市場、社會關(guān)系時(shí),應(yīng)遵循市場、社會優(yōu)先的原則,合理界定政府的職能范圍,創(chuàng)新履職方式,充分發(fā)揮財(cái)政資金的引導(dǎo)作用,將有限的財(cái)力發(fā)揮出“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最后,新時(shí)代需要一個(gè)有為的政府,一個(gè)善做善成的政府,一個(gè)善治的政府,善治性是構(gòu)建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的最終要求。綜上所述,本文認(rèn)為,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是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相適應(yīng)的一種財(cái)政制度,具有法制性、共治性和全局性等特征。
參考文獻(xiàn):
[1]? 靳東升.中國稅制改革40年:回顧?總結(jié)與思考[J].地方財(cái)政研究,2018,(11):20-33.
[2]? 靳瀾濤.從公共財(cái)政到現(xiàn)代財(cái)政:政策邏輯與理論構(gòu)造[J].公共財(cái)政研究,2018,(4):29-40.
[3]? 賈康,劉薇.構(gòu)建現(xiàn)代治理基礎(chǔ)[M].廣州:廣東經(jīng)濟(jì)出版社,2017.
[4]? 馬海濤,肖鵬.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財(cái)稅改革回顧與展望[J].地方財(cái)政研究,2018,(11):4-19.
[5]? 付敏杰.國家能力視角下改革開放四十年財(cái)政制度改革邏輯之演進(jìn)[J].財(cái)政研究,2018,(11):33-45.
[6]? 林光彬.中國財(cái)政改革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邏輯[J].稅制改革,2016,(2):7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