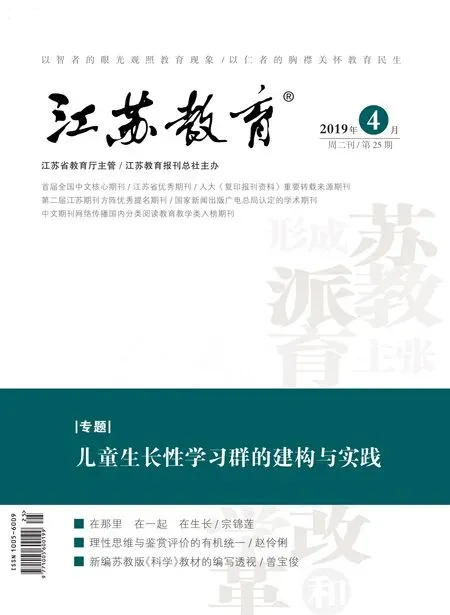場景閱讀的意蘊及其優化策略
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數字技術”“移動網絡”等技術開始改變著教師的教學方式和學生的學習方式。結合數字技術、移動網絡的時代特性,一些教師開始關注多媒體技術,借助互聯網信息技術與設備,營造出一種閱讀場景,從而調動學生的各種感官,讓他們從簡單的“讀”進入到文本場景中全息體驗,實現“閱讀在場景中,在場景中閱讀”。
一、場景閱讀的意蘊
(一)閱讀概念的界定
“一本好的書也是可以反復閱讀的書,你在重讀時會發現這本書好像與你一起成長了。你會在其中看到新的事物——那是你以前所沒有看到的東西。”[1]閱讀是觸及學生個體生命成長的過程,學生在閱讀活動中建構生命意義,將閱讀中所學到的知識轉化為技能并遷移應用到真實情景中去解決復雜問題,進而促進學習者元認知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等高階能力的發展。
《如何閱讀一本書》認為閱讀過程的概念可分為三個部分,即方法策略、思考能力和背景知識。其一,背景知識是閱讀活動的基礎。背景知識,既指學生對文本中文字信息的成功攝取和有效傳遞,也指學生在閱讀時已經擁有的相關、相似的“知識背景”。這些背景知識讓閱讀過程成為一個利用已有圖式和語篇線索不斷猜測和印證的過程。其二,思考能力是閱讀活動的前提。閱讀的過程其實是學生處理信息的過程,也是學生知識量的積累和質變的飛躍的過程。在閱讀時,學生的思維處于活動狀態,通過在文本中提取信息并將它們內化為知識而改變其原有的圖式結構,創造出新的觀點和知識。其三,方式策略是閱讀的保證。閱讀方法和閱讀技巧決定著閱讀的效率和能夠獲得的閱讀效益的最大可能性。閱讀本體的復雜性、數字閱讀環境的多變性以及閱讀信息的海量性,讓閱讀方式的選擇成為一門藝術。
(二)場景閱讀的內涵
如上所言,閱讀是聯結學生已有知識與文本中人類文明成果、已有認知與學生發展的活動,它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而場景則為兩者的聯結提供了媒介,場景閱讀成為促進閱讀活動真正發生的有效教學方式之一。
場景讓信息呈現直觀化。學生對于背景知識的攝取有時是片面的,甚至是缺失的,但網絡卻能將大千世界囊括其中,并以場景的方式直觀呈現。文本中的人物、情節、作者的傾向被一一安置在“場景”中,學生在閱讀活動中獲得多方面的發展。
場景讓閱讀過程創新化。數字技術、移動網絡在場景閱讀中的運用,能夠充分調動學生的理解力、洞察力、邏輯推理等多種思考能力,促進學生認知能力發展。
綜上所述,場景閱讀就是指在實際的教育教學過程中,教師依據閱讀文本和學情,借助各種信息技術手段與設備,營造出特定的場景,從而調動學生的各種感官,讓他們從簡單的“讀”進入文本場景中全息體驗,讓學生與文本的內容、思想深刻交融,全面提升閱讀能力。
(三)場景閱讀的基本特征
沉浸性。長久以來,學生與閱讀文本之間的傳播關系是單向的,當他們面對知識譜系時,往往容易陷入“單向度思想”。教師可以利用網絡和多媒體技術將相關的視頻、圖像、音頻融入文本閱讀,甚至結合學生的經歷體驗,在課堂中表達與分享,在分享中內化知識。這樣,因真實感受而產生的沉浸性體驗,會引導學生突破淺閱讀,收獲深刻的閱讀體驗。
交互性。所謂交互,是一種對象之間相互作用并導致彼此之間發生積極改變的過程。從某種程度上說,學生在場景中閱讀,就會與自己選擇或者營造的場景形成自然的交流,讓他們由單純讀文本到全身心地思考文本,充分調動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從而使其閱讀潛力得到挖掘。
構想性。因為信息的抽象性和不完整性,學生在腦中還原信息的準確度往往不高。而如果借助互聯網,讓學生置身于所創設的場景中,根據場景的提示,或可較大程度地激發學生的靈感和想象,創造更為豐富的精神場域與境界,學生的閱讀體驗也會更豐富,獲得更多的思考與感悟。
二、場景閱讀的優化策略
(一)場景閱讀,要在“點”上觸擊
場景閱讀可以圍繞一個“點”展開。這個“點”可以是一件“物”。在學習狀物類的課文時,如果只是讓學生通過單純的朗讀去把握課文,則很難將作者所描繪物體的特點充分地展現給學生,而借助互聯網與多媒體,將學生安置在真實的場景中,則會改善教學效果。
例如教學蘇教版三上《石榴》一文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播放一段石榴結果的動態視頻,讓學生觀察石榴開花結果的過程。然后再回歸文本,了解石榴花的形狀,了解石榴結果的過程,品味石榴的滋味,進而體會作者對石榴的喜愛之情。
這個“點”也可以是一處情景。在閱讀時,文本中有很多情景是學生未曾經歷過的,這會讓他們難以走進文本,疏離作者寫作的初衷。比如教學蘇教版五下《水》時,教學目的之一是讓學生了解到缺水地區的酸楚,讓學生懂得愛水、惜水、節水。但許多學生本就是水鄉的孩子,那里有充沛的雨水、流淌的河流、觸手可得的自來水,難以感同身受地體會缺水之苦。教師可以借助網絡視頻全面呈現缺水村落的全貌,讓他們直觀皸裂的大地,干涸的河床,鄉里人因干旱而干裂的嘴唇,繼而對比呈現下雨時鄉里人拿著鍋碗瓢盆接水的場景,讓學生設身處地地感受雨水的珍貴,得到水時的興奮、痛快。
這個“點”還可以是一個事件。雖然具有故事性的文本較其他文本更能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但當他們的興趣只是停留在走馬觀花地瀏覽,那事件中人物的精神,錯綜復雜的故事情節也很難在學生腦海中扎根。這時,教師就可以選擇在真實的場景中進行閱讀教學。例如在學習關于歷史事件的課文時,可以采取讓學生觀看影片、按角色朗讀課文或者自演歷史劇的方法創設真實的場景,全面感受文本傳遞的內容和思想。
(二)場景閱讀:要在“線”上觸碰
恰如陶行知先生所言:“好的先生不是教書,不是教學生,乃是教學生學。”在文本與文本之間總能找到共性將它們串聯起來,而場景便是那根線。教師作為學習的引導者、閱讀的指路人,如果可以按照場景的劃分將課內文本與課外文本相連接,并引導學生舉一反三,遷移學習,培養學生的自主分析能力和獨立閱讀能力。
以蘇教版六上《青海高原一株柳》為例,作者陳忠實運用對比的手法設置了兩個場景:一邊是異常蒼涼的青海高原,一邊是風調雨順的家鄉灞河。學生通過這兩個場景的對比感受到高原柳頑強的生命力。根據這篇文章,教師將兩篇具有相似場景的文章《生命的選擇》和《兩棵松樹》分享給學生。通過分析,學生便會發現這兩篇文章都是通過場景的對比,來贊美在逆境中獨成風景的美好品質。借助場景,讓學生習得遷移方法,讓閱讀變得深刻。
(三)場景閱讀,要在“面”上觸摸
每個文本都是一個個場景的設置,按照一定的序列把相關的場景相互串聯融合,或許會產生宏大的場景版圖,彰顯歷史的脈絡和人類的文明。當學生帶著對閱讀特有的感悟在文本與文本之間來回穿梭、不斷建構,那么他們所“拼湊”出來的或許是一個時代的版圖,或許是一個帝國的興衰更替。
例如蘇教版六上《一本男孩子必讀的書》一文,課文中設置的場景是一個孩子在仔細翻閱父親所贈的“傳家寶”——《魯濱遜漂流記》。文中男孩對這本書的珍視很容易引起學生的閱讀興趣:《魯濱遜漂流記》到底是一本怎樣的書?魯濱遜的故事是在什么樣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呢?教師適時點撥解惑,學生便會刨根問底地去尋找蛛絲馬跡。每個孩子都是一個個體,他們對于文本的選擇都具有獨特性,如果將他們的描述加以“拼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麥哲倫環球航行,馬可波羅訪問中國,鄭和下西洋……將這些場景按照時間維度聯結排序,學生會發現,閱讀中竟然隱含了一個時代的概貌——大航海時代。
三、場景讓兒童與閱讀深度融合
在信息時代,語文閱讀教學面臨著種種挑戰,如何巧妙地利用新技術服務教學,這是語文教師必須深思的問題。場景閱讀策略的實施,實際上是讓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自覺地從“點、線、面”三個維度展開深度閱讀,從而達成“閱讀在場景中,在場景中閱讀,讓場景連接閱讀”的目的。
以點為場景,讓學生在真實的情景中感受文本所營造的氛圍,以自己的情感體味作者的情感,使學生與作者建立聯結、產生共鳴。以“場景”為線進行閱讀的串聯,則讓學生有意識地進行知識與能力的遷移,活學活用。當學生遇到同一類型的文章,他們便能很快挖掘文章的內涵,領會作者的意圖,將相關的場景相互串聯與融合,構成立體的時空。在此過程中,學生的思維能力、生命境界不斷提升,逐漸認識自我,獲得成長。
注:本文獲2018年江蘇省“教海探航”征文競賽一等獎,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