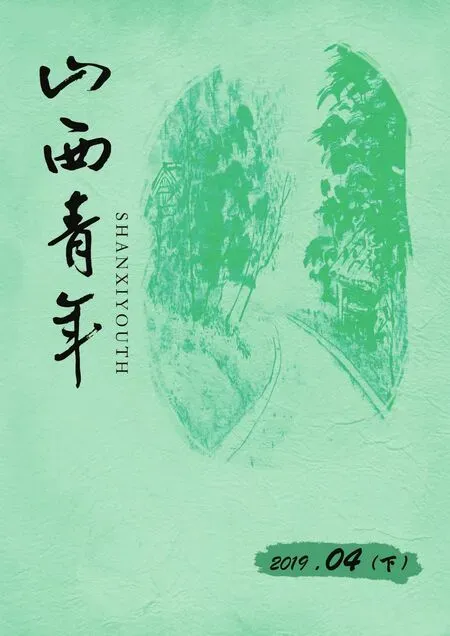對蘇格拉底“美德即知識”命題的新思考
郭姣姣 郭曉蓓
(安康學院政治與社會發展學院,陜西 安康 725000)
在蘇格拉底生活的時代,民眾的思想在智者派的助推下日益活躍,但智者們作為“販賣知識的商人”,其教學行為帶有明顯的功利性;而這種功利性的弊端促使蘇格拉底作為一名有責任、有擔當的哲人開始審察教化萬民正確的價值取向究竟為何;其試圖建立一種美德主義倫理學,用以改善人的靈魂和復興雅典城邦。
蘇格拉底非常反對智者們如兜售產品般兜售他們的知識,認為這種行為會導致社會偏向功利主義與享樂主義,對雅典的發展十分不利。在蘇格拉底看來,只有當人民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善”,才能使國家穩定繁榮,而這種“善”需要人們不斷學習以反思自身,通過承認自己的無知來獲得;由此,蘇格拉底提出了著名的論斷——“美德即知識”。
蘇格拉底強調人們可以通過認識自己去追求知識、實踐美德,人們只有通過學習知識才能對美德有一個清晰、理性的認識,才能明白什么是美德,進而積極去自覺的踐履真正的“善”,實現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一、美德是否可教
關于這一問題,在《普羅泰格拉篇》中,記載著蘇格拉底曾與普羅泰格拉展開過一場辯論——蘇格拉底認為只有少數人才能掌握美德,因此美德不可教,但美德必然是知識;而普羅泰格拉則認為美德是可教的,但美德并不是一種知識,它取決于個人的觀念。由此可見,兩人對于美德能不能教的爭論關鍵就在于美德到底是不是知識。普羅泰格拉認為美德是知識以外的東西,其取決于個人,并非統一的、對任何人都適用的具體知識;但是蘇格拉底認為美德是一種特殊的知識,它來源于理性的自省,并不受外界或主觀的影響,人們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反思,就能超越一切直達洞察本身的境界,美德的獲得需要建立在“認識你自己”的基礎上,也就是人們要承認自己的無知,這樣才能不斷追求和接近有知。
蘇格拉底和普羅泰格拉就美德是否可教這一問題并沒有得出確切的結論,這源于兩人立場本就不同,所以對美德的定義也就是迥異的。普羅泰格拉代表的是智者學派的觀點,即美德取決于個人,因此沒有絕對的標準,只能靠外在強制獲得,所以可教。然而蘇格拉底所說的美德并不是依靠外在的強制,而是通過不斷學習和反思去追尋自我本身的“善”,來達到美德教育的目的;他曾在《歐緒德謨篇》中這樣規勸他人:“一切表面上的善只有當他們為知識所引導時才是善的,因此每一個人都應該追求成為有知識和有智慧的人。”蘇格拉底反對智者教授美德,因為如果美德可教,就不會被人們所自覺的反省和重視,這也是他認為美德是知識,但不承認是美德可教性的真正原因。
處于當代的我們在理解美德可教與否這一問題時,必須采用唯物辯證法加以辨析,這就可以得到形式上的美德是不可教的,因為這樣會偏向功利主義,但是能夠引導人的心靈感悟和升華的美德內涵又是可教的。
二、美德教育的功能
既然美德是知識,也具有可教性,那么美德教育有什么功能呢?梁啟超先生說過:“精神——美德,實為知識運用的根基,具有優先地位……一般的教育者,也不注意這方面提倡,只天天設法怎樣將知識去裝青年的腦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爾后多的知識才有用,茍無精神的人為社會計、為個人計,都是知識少裝一點為好,因為無精神生活的人,知識愈多、痛苦愈甚,做歹事的本領也越多,蓋人茍無安身立命之具,生活便無所指歸,生理心理,并呈病態……因此,我可以說為學的首要,是救精神饑荒。”由此可見,美德對于人們的生活、發展和社會進步都具有推動作用;總體來看,美德具有五大功能,分別是認識功能、調節功能、教育功能、評價功能和平衡功能。認識功能引導人們知善向善,調節功能幫助人們應對矛盾尋求和諧,教育功能傳播正確的價值觀啟迪蒙昧,評價功能區分善惡繼而懲惡揚善,平衡功能則使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平衡相處。
通過美德教育,能夠引導人們追求人生價值的實現,提高生活的幸福感,也使社會更加和諧、穩定。美德教育如若偏廢,很容易導致物欲橫流,公德淪喪,人們隨之失去精神追求,文明也會遭受重創;所以,美德教育意義堪稱重大,必須由全社會共同關注的重要現實問題,尤其是我國現在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注重美德教育和精神建設對于社會的進步大有裨益。
三、“美德即知識”何以可能
蘇格拉底將哲學研究的方向從自然界轉向了人類自身,并且主張哲學家應該關心現實的社會生活,而哲學教學的目的就是喚起學生對日常生活的反思和省察,關注并思考人生的意義。
“美德是知識”的命題固然有其局限性,因為并非知識越多,美德就會越多,二者不是正比關系。知識只能作為明理的基礎,從知識到美德還應該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即通過學習知識樹立明理基礎,在這一基礎上將所習得的知識用來指導實踐,才能實現真正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