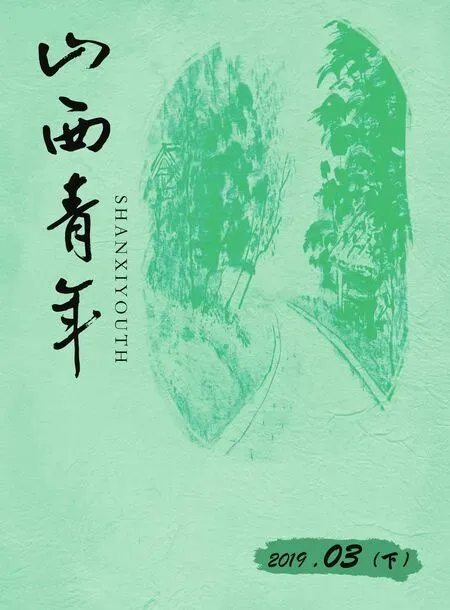共同體意志與中國優勢
李瀚洋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1620)
一、國家的內核是共同體意志
在古希臘城邦中,人民結合成了一個聯系緊密的小共同體,通過這個小共同體的集體決策方式來體現其共同意志。這種方式的背后原因是由于每個參與者對自己的權利的聲張與保護,希望集體對自己的權利得以照顧。而這種要求的根源是在古希臘之前的原始社會即存在著殘酷斗爭的自然界中長期形成的,這就使得人對于自身權利的保護與追求成為了人的天性。因此,集體活動的內核是共同體意志,是一種集體意見中最大部分的整體統合。[1]這樣的共同體意志是得到整體成員所承認的,也是整體成員所共有的。早期的國家以具有血緣聯系特定民族為居民構成,所以國家自然地帶有民族性特征[2],身處其中的自然人對國家的認同與民族意識是疊加在一起的。這時的共同體意志是強烈且牢固的。
當共同體意志從小的共同體經過長久的發展,直到民族國家產生之后,由于共同體意志與人的天性有著天然的“捆綁”關系,國家的內核就是共同體意志,應該符合人的本性。[3]人的天性是在自然中長期形成的。[4]因此,在理論上,國家對于人權的保護應當是全方位的。這種全方位的保護是因為從小的共同團體到國家的產生,不僅僅是人數、范圍上的擴大,在人與主體的形勢上也發生了質的改變。在小的團體中,個人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但在面對國家時,個體形式存在的人和公民處于完全的“弱勢”,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不應當在“保障人權”上留有空當,那樣無法真正反映出背后的共同體意志。
如同在小的共同體時期一樣,在國家締結之后,需要對這種“國家的保障”進行政治行為上的確認。也就是說,政治上的行為是為了實現國家對于人權的保障功能,也是對于共同體意志的彰顯。為了實現這樣的功能,在以共同體意志為核心的基礎上,出現了多種政治形式。如盧梭認為只有體現全體人民意志的公意才是民主的,也才是合法的。[5]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全體一致同意只是一種理想化的政策達成路徑。于是邊沁便認為應當保證“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6]。他認為,為了得到這一結果,犧牲少數人的利益是可以接受的,只要這種犧牲能提高社會幸福的總量,這個犧牲就是有必要的。
二、西方國家對于共同體意志內核的偏離
毫無疑問,邊沁的做法容易產生“多數人的暴政”。使得部分人的權利受到侵害,哈耶克認為群體數量的大小與群體利益的大小之間沒有必然聯系,而且還可能成反比。[7]因為民主本身并不能防止公權力脫離其本身的軌道。如西方國家的代議制民主就是通過計算選票來得出共識,并且被認為是民主的。但是在實際上,直接將選票認為是多數人的意志,是存在著很大的偏誤的。在這類投票活動中,投票選舉的結果很容易受到策略性投票和議程控制的操縱。對于投票本身來說,投票是模糊的,選票的計算過程是人為控制的。這種不穩定性與模糊性,使得選舉的過程容易受到政黨或者精英的控制,出現多數原則被少數控制所取代這一現象。同時,不同的計票方式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賴克甚至認為,投票是沒有意義的。其認為選舉結果是人為產物[8]。唐斯認為,一旦新政府被選出來,大多數選民將寧愿政府在每一個問題上都遵照少數人的而非多數人的意見,因為他們與其他多數人共同擁有的觀點相比,人們總是更強烈地維護自己的少數人共有的觀點。[9]同時,還存在理性人的假設,如果收益比收集信息的成本低,或者投票對于被投票的主體并沒有影響,則理性的選民都會選擇政治冷漠或者在信息收集方面保持理性的無知。[10]這樣的后果可能是比什么都不做更加糟糕的。[11]因此并不能反映共同意志,甚至往往形成了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背離。其根源在于,近代的民主往往是精英主導下的民主,因此哪怕方式上非常的合理,程序上,形式上都帶有著相當大的合理性,但是其結果是受到精英的操縱的。而且從具體的選舉制度來看,選民投票所產生的只是代表或者新的政府,選民往往并不會直接參與到具體的政策過程中。也就是說,在選舉結束之后,選舉出的代表的決策,更加難以去反映出多數人的意志。包括在協商民主中,哈貝馬斯看到了協商在政策制定中影響力的有限性,認為協商僅僅限于公共領域中,但是公共領域只是圍繞政治中心的外圍,它可以影響決策但是無法進入到實質性的決策過程中,也無力推翻中心主導的局面。[12]
這些例子都表明,在西方國家中單單靠民主是不能夠實現對于公民的權利的實現的,西方國家不斷地追求民主,卻產生了對于共同體意志反映的偏差。基于這種偏差,西方國家又產生了限制權力的使用做法,希望讓權力正確的滿足公民對于保護自身權利的需求。[13]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利益,但是也是基于在特定國家的基本權利與公民知情下的共識的長期博弈而形成的并不是可以對于別的國家的方式方法照搬照抄的。[14]西方國家的法律與制度的建立時間有先有后就證明了這一過程是博弈產生的。[15]
西方國家不考慮掌權者的自我約束情況,通常采用分權制衡與人民制約的方法,希望繼續國家的發展這一博弈過程。理論上,分權是一種控制權力的重要方法。權力的集中會使得個人的自由遭到扼殺,在分權的社會中才能有自由的空間。[16]分權可以使得權力不會集中在單個個人手中,西方國家的民主可能性源于此。[17]同時權力自身還有擴大其規模的傾向。[18]人民制約則是通過人民有效地掌握一部分權力,或者人民可以對于權力施加影響來間接控制。體現在私人領域中,人民會采取使用法律的方式保護自己的權利。在公共領域中,公民會主動行使自己的知情權、言論自由權、監督權等權利對公權力加以影響。但是這些僅僅是基于歷史的一種結論性的理論構建,并不能用來完全指導未來的國家走向,這里西方國家已經徹底偏離了共同體意志的本質。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對于共同體意志的反映優勢
如今,全世界的人的命運已經非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但是這聯系看起來卻和遠古時期的共同體不同。很難去找到一個唯一的邏輯一致的社會選擇規則,可以將個人理性轉化為集體理性。[19]西方的民主是基于“人是政治動物”以及“人是理性動物”[20]的理論,前者是說明人參與政治生活是為了通過政治生活來保障自己的權利,后者是假設公民形成的集團亦可以理性的前提。但是假設畢竟只是假設,只是一種理想的狀態。人的政治生活相對于人有意識的集體生活以來的時間仍然是太短了,四萬年來,人的基因本質上都沒有任何的改變[21],其動物性的部分必然對人本身有所影響,如亞當·斯密的對于經濟人的理性假設[22]已經在很多情況中受到質疑,如奧爾森認為在大集團與小集團中會出現不同的利益決策產生不同的后果。[23]我們要認清的是,人類還在不斷地認識發展的過程中。對于這種文明的事實是必須要考慮的。[24]
在當前社會,在國家與自然人中,都存在著強烈的不確定感,在不同群體之間生活方式差異化,利益訴求多元化,彼此之間的差距甚至看起來是絕不可能調和的。分化與多元化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社會現象,我們應當認識到這一現實,對于在這其中出現的新的聲音、異議加以包容。并且要通過整合與同化,達成新的共識,而不是將其排除在外。可見的是,當前各個國家均在通過強化利益共同體來整合各方利益,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在強調美國的國家利益,強調美國全體國民的福祉。因此通過對于共同意志的再認識,承認目前的社會多元化,認識到需要對于共同意志進行再認識,接納、包容各種公民,是現在的西方憲政首先要優化的地方。
值得分析的是,當前的歷史進程只是人類物種進化中的一個短暫的瞬間,自然人的身上仍然帶有相當程度的動物性,就個體而言,歸屬感是人類所共有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感,正是因為這種歸屬感,自然人才能尋找同類,在群體中獲得自我肯定和內在的生物驅動力量。而面對當前社會上多元化的問題,現代國家并不能像古代社會中一樣,采用暴力或戰爭的手段進行整合,現代國家應當通過制造環境優勢與社會人文優勢等國家軟實力,以先進的國家價值觀、優厚的社會福利制度、良好的自然環境等方面具有的比較優勢來增強對人們的吸引力,通過除了暴力戰爭以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要明白的是,人類的文明史在人類物種的歷史長河中是相當短暫的,人類的動物性趨向于優美、良好、健康的自然環境。建立環境優勢與公民的共同意志是息息相關的,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生理需求是人類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它是最強烈的不可避免的最底層需要,也是推動人們行動的強大動力。當一個人為生理需要所控制時,其他一切需要均退居次要地位。人是非理性的動物,在文化等方面有強烈的趨同性。叔本華、克羅齊都強調藝術對人共同意志的激發與關聯[25-26]。對于社會人文上的舒適感是廣泛存在于人群中的,足矣反映出其在共同意志中的重要性,而對于社會人文優勢的建設往往是現代國家所忽視的一方面,這一點則是后發國家彌補其其他方面劣勢的“加速道”。同時,叔本華認為,人的情感中存在著利己心、惡毒心、同情心作為人行為的推動力,只有同情心具有道德價值,人與人之間通過同情心可以建立起共同的意志[27],因此社會福利優勢是必須建立且存在著不能簡單用國家的福利支出的多少來衡量的優勢。更多的體現在公民對于福利的“周到”和“感動”,承認這種來自社會與國家的“善舉”。
而對于當前的中國,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社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是具有反映共同體意志方面的優勢的。西方國家當前的社會模式,是在歷史的長期進程中發展起來的。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也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中國的國情上發展起來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種族、社會張力,都與西方國家有著巨大的差異。如上文所述,西方國家的民主,是為了反映公民的共同意志。而中國共產黨,本身就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意志,中國這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已經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公民是最契合的。同時當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全方位的,在文化、生態、環境等方面,充分而全面的發展。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的,“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后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后果不堪設想。”[28]我們應當認清我們社會的本質是建立在中國民族的共同體意志上的,當前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模式就是最適合中國發展的,應當堅定不移的跟黨走,共同建設美好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