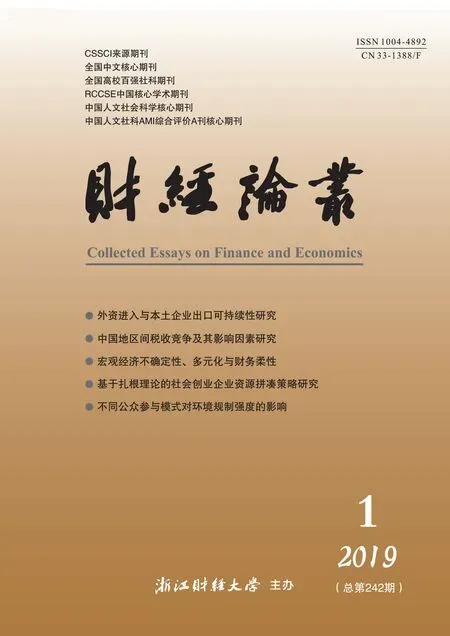中國地區(qū)間稅收競爭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來自動態(tài)空間杜賓模型的經(jīng)驗(yàn)證據(jù)
劉清杰,任德孝,劉 倩
(1.北京師范大學(xué)新興市場研究院,北京 100875;2.北京師范大學(xué)政府管理學(xué)院,北京 100875)
一、引言及文獻(xiàn)綜述
長期以來,稅收優(yōu)惠是各地招商引資的重要籌碼,對地方政府提高政績和企業(yè)提高利益都具有重要影響,但是多數(shù)優(yōu)惠政策游走在法律和政策法規(guī)之外,存在尋租和腐敗空間。并且地區(qū)間競相制定稅收優(yōu)惠降低稅負(fù)的行為制造稅收“洼地”,影響公平競爭。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清理和規(guī)范稅收優(yōu)惠政策被提上議程,規(guī)范法律法規(guī)之外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也在深化預(yù)算管理制度改革中被確定。然而在各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存在巨大差異的中國國情下,“一刀切”的治理政策無法實(shí)現(xiàn)預(yù)期效果,探究地區(qū)間稅收競爭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對于規(guī)范地區(qū)間稅收優(yōu)惠具有重要現(xiàn)實(shí)意義。地區(qū)間稅收競爭指的是地方政府在其能力范圍內(nèi)為各自利益需要制定的非合作稅制影響到稅基在地區(qū)間流動的行為,異質(zhì)性政府因各自稟賦形成差異化稅率,長此以往造成資源配置更加不平等,最終會在這場稅收競爭中逐步拉大區(qū)域間貧富差距。國外研究稅收競爭的主要稅種是資本稅,地方政府之間競爭主要是基于資本要素的競爭,而稅負(fù)作為企業(yè)的一項成本往往是企業(yè)進(jìn)行投資決策時所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為降低企業(yè)成本以吸引資本流入,地方政府通過各種稅收優(yōu)惠政策展開競爭。企業(yè)所得稅作為直接稅較難轉(zhuǎn)嫁,并且在地方政府稅收收入中占有較高份額,企業(yè)對所得稅稅負(fù)的敏感度相對于間接稅較高,這種高稅負(fù)彈性使地方政府以其作為競爭手段,影響企業(yè)的投資和選址決策,本文以企業(yè)所得稅為研究對象考察中國地區(qū)間稅收競爭行為。
稅收競爭領(lǐng)域的學(xué)術(shù)研究伴隨的是稅收競爭模型中競爭雙方的同質(zhì)性假設(shè)向異質(zhì)性假設(shè)演變的過程,并逐漸在稅收競爭模型中引入地區(qū)屬性差異,從標(biāo)準(zhǔn)的稅收競爭模型發(fā)展到不對稱稅收競爭模型。Zodrow & Mieszkowski(1986)[1]和Wilson(1986)[2]將稅收競爭理論通過模型規(guī)范化,認(rèn)為地區(qū)之間為了流動稅基而展開的競爭是競相降低稅負(fù)的“逐底”競爭。早期的稅收競爭文獻(xiàn)對于研究地區(qū)之間的稅收競爭提供了有價值的視野,然而,這些文獻(xiàn)過于依賴地區(qū)之間同質(zhì)化的假設(shè),認(rèn)為因此地區(qū)間競爭均衡下選擇相同的稅率。而這些假設(shè)隱藏了轄區(qū)之間的潛在沖突,模型無法解釋政府實(shí)際上不對稱的政策回應(yīng)。例如Elschner & Vanborren(2010)[3]所提到的,對于歐盟國家,即使資本流動性在增加,政府之間的競爭壓力也在增強(qiáng),然而有效平均稅率的變化仍然很高,基本在2007年時從保加利亞的8.8%到德國的35.5%。尤其是,這些假設(shè)難以支持轄區(qū)之間所存在的外生不對稱,在設(shè)置資本稅稅率時轄區(qū)規(guī)模所扮演的角色引起了學(xué)者的關(guān)注。Bucovetsky(1991)[4]和Wilson(1991)[5]在理論上構(gòu)建了不對稱稅收競爭模型,不對稱稅收競爭模型是在標(biāo)準(zhǔn)稅收競爭模型的基礎(chǔ)上放松假設(shè)而發(fā)展起來的,轄區(qū)的生產(chǎn)要素包括以人口為主的非流動要素和以資本為主的流動要素,當(dāng)某個轄區(qū)在稅收競爭中非流動性要素規(guī)模相對于競爭轄區(qū)較大時,調(diào)整資本稅率將在較大程度上影響資本的稅后回報率,因而在選擇稅率的同時形成了不對稱轄區(qū)間的策略互動。Bucovetsky(2009)[6]將兩個轄區(qū)的競爭結(jié)果擴(kuò)展到適用于多個轄區(qū)的情況,后續(xù)學(xué)者從勞動力不完全流動和資本流動成本異質(zhì)性等角度對不對稱稅收競爭模型的拓展做了大量嘗試。
中國學(xué)者周黎安(2007)[5]提出政治晉升錦標(biāo)賽理論,將國外錦標(biāo)賽競爭理論用于介紹中國官員晉升事實(shí),解釋中國經(jīng)濟(jì)快速發(fā)展的制度原因,這也為中國地區(qū)間的稅收競爭行為提供理論基礎(chǔ)。在此基礎(chǔ)上,謝喬昕和宋良榮(2015)[7]提出官員晉升競爭是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的重要動機(jī),通過動力機(jī)制與壓力機(jī)制對地區(qū)企業(yè)實(shí)際稅負(fù)構(gòu)成影響。中國學(xué)者通過大量工作論證了地區(qū)間稅收競爭的存在性,基于空間計量模型研究得出中國地區(qū)間存在策略互補(bǔ)的稅收競爭。已有學(xué)者結(jié)合中國的地區(qū)發(fā)展現(xiàn)狀,在財政分權(quán)背景下從地方政府異質(zhì)性約束視角理解實(shí)際稅率的分化水平,認(rèn)為不同地區(qū)由于發(fā)展定位不同,競爭時針對稅收競爭具有不同的策略選擇,這為進(jìn)一步研究地區(qū)間稅收競爭差異化的策略互動特征提供啟發(fā)。然而這些文獻(xiàn)并沒有對影響稅收競爭的地區(qū)屬性差異進(jìn)行系統(tǒng)分析,而且不同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可能形成差異化的結(jié)論。受此啟發(fā),本文研究中國地區(qū)間的稅收競爭特征及影響稅收競爭策略互動的因素,從地區(qū)異質(zhì)性的角度剖析稅收競爭的影響因素,為進(jìn)一步緩解稅收競爭規(guī)范稅收優(yōu)惠提供對策建議。
本研究與以往的研究不同在于,一方面,本文研究地區(qū)間稅收競爭存在性時不僅考察了地理相鄰的地區(qū)間競爭水平,同時引入經(jīng)濟(jì)相鄰空間權(quán)重,分析對比經(jīng)濟(jì)權(quán)重下地區(qū)間稅收競爭程度,這符合中國中央集權(quán)制下各地方政府官員受到晉升激勵的社會現(xiàn)實(shí);另一方面,以往研究稅收競爭的影響因素較少,多是考察集聚經(jīng)濟(jì)對稅收競爭的影響,本文基于不對稱稅收競爭理論,從地區(qū)屬性的角度研究異質(zhì)性轄區(qū)間稅收競爭受到影響的因素,考察人口規(guī)模、工業(yè)化水平、對外開放水平對地區(qū)間稅收競爭時的作用機(jī)理和影響水平,為進(jìn)一步緩解稅收競爭提供可供參考的對策建議。
二、理論假設(shè)
Mintz & Tulkens(1986)[8]和Wildasin(1988)[9]研究非同質(zhì)地區(qū)的稅收競爭中的博弈問題時提到,決定資本在地區(qū)間配置的因素不僅是本地區(qū)稅負(fù),周邊其他地區(qū)的稅收政策下的稅負(fù)水平也對資本流動具有重要影響。地方政府通過影響地區(qū)稅負(fù)的稅收政策進(jìn)行博弈,對資本等要素在地區(qū)間配置具有重要影響外,也可能對地區(qū)間經(jīng)濟(jì)發(fā)展?jié)摿π纬芍匾绊憽I蚶s和付文林(2006)[10]研究中國的地區(qū)間稅收競爭時認(rèn)同這一觀點(diǎn),認(rèn)為資本在地區(qū)間流動在受到本地區(qū)稅負(fù)影響的同時也受到周邊地區(qū)稅收政策的影響。而空間距離是稅收競爭下的企業(yè)選址時的一個重要考量因素,也是影響資本流動的主要因素,Anselin et al.(1996)[11]指出勞動力流動往往表現(xiàn)出地域性的特征,這是因?yàn)槠鋾艿轿幕?xí)慣傳統(tǒng)以及與空間距離相關(guān)的遷移成本的影響,同理資本流動也具有很強(qiáng)的地域性。
資本具有空間聯(lián)動特征,更容易在空間相鄰的地區(qū)間流動,中國地區(qū)間為招商引資而展開稅收競爭在制定本地區(qū)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需要觀察周邊地區(qū)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并做出反應(yīng),本地區(qū)相對于周邊地區(qū)的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低時對吸引資本來說形成比較優(yōu)勢,從而在競爭中占有主動地位。通過稅收競爭可以向企業(yè)傳遞信號表明本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實(shí)力,吸引資本的激勵是相對的,稅負(fù)的高低也是相對的,因此決定本地區(qū)對資本的吸引力的不僅是本地稅負(fù),周邊地區(qū)稅收政策也對本地區(qū)產(chǎn)生重要影響,由此引起了空間地理相鄰地區(qū)間的稅收競爭。
因此,本文得到的第一個研究假設(shè)如下:
假設(shè)1:中國地理相鄰的地區(qū)間存在為爭奪資本而展開的競相進(jìn)行稅收優(yōu)惠的稅收競爭,并且地區(qū)間稅收優(yōu)惠行為是具有空間正相關(guān)性的。
隨著區(qū)域間開放透明度逐漸增加,地區(qū)之間出現(xiàn)相互借鑒和取經(jīng)使合作關(guān)系變得緊密,然而根據(jù)晉升錦標(biāo)賽理論,地區(qū)之間進(jìn)行合作的同時,官員可能因?yàn)閷x升位次的爭奪而展開競爭,尤其是在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相當(dāng)?shù)牡貐^(qū)之間這種現(xiàn)象更加明顯。因此,結(jié)合已有學(xué)者研究成果和地區(qū)間整合現(xiàn)狀,我們預(yù)期經(jīng)濟(jì)實(shí)力越相近的地區(qū)之間,越可能存在競爭,相對來說合作也越困難。已有研究認(rèn)為在國家內(nèi)部地區(qū)間的整合主要根據(jù)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分為強(qiáng)強(qiáng)型整合、弱弱型整合和強(qiáng)弱型整合,其中強(qiáng)強(qiáng)型整合模式的整合基礎(chǔ)好,組織機(jī)構(gòu)沒有超行政區(qū)功能,然而這種模式因?yàn)槿菀资艿街鲗?dǎo)城市的影響,行政阻礙較大,地區(qū)間競爭非常激烈,最終整合的質(zhì)量較低。弱弱型整合模式以淮海經(jīng)濟(jì)區(qū)為例,整合過程中基礎(chǔ)不高,組織機(jī)構(gòu)也不具有超行政區(qū)的功能,不存在明顯的主導(dǎo)城市作用,整合的地區(qū)間仍處于初級階段的競爭,整合動力弱,進(jìn)程慢,整合的質(zhì)量不高。強(qiáng)弱整合型以江陰-靖江工業(yè)園區(qū)為例,這種整合的基礎(chǔ)介于強(qiáng)強(qiáng)型整合和弱弱型整合,這種模式下的地區(qū)間整合動力大,具有明顯的主導(dǎo)城市作用,整合組織機(jī)構(gòu)較少,不具有超行政區(qū)功能,整合質(zhì)量高于前兩種模式[12]。
強(qiáng)強(qiáng)型地區(qū)間競爭激烈的原因可能來自中央集權(quán)下地方政府官員的激勵機(jī)制——政治晉升錦標(biāo)賽,周黎安(2007)[12]提出政治晉升錦標(biāo)賽理論認(rèn)為異質(zhì)性地方政府參與稅收競爭的主要激勵來自地方官員為了政治晉升而與競爭者地區(qū)官員所競爭的相對位次,晉升錦標(biāo)賽理論成為研究中國財政問題的主要路徑,基于這樣的中國現(xiàn)實(shí)分析中國異質(zhì)性地區(qū)稅收競爭的主要特征。中國區(qū)域合作困難,難以進(jìn)行經(jīng)濟(jì)整合,地方保護(hù)主義現(xiàn)象明顯。相對于地理鄰接的競爭強(qiáng)度而言,經(jīng)濟(jì)實(shí)力越是接近的地區(qū)越不容易合作,這導(dǎo)致不同經(jīng)濟(jì)帶區(qū)域整合程度存在差異,京津地區(qū)的區(qū)域整合程度就低于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qū),經(jīng)濟(jì)實(shí)力越相近的地區(qū)官員面臨晉升位次的競爭就越激烈,難以合作,而發(fā)達(dá)地區(qū)與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的區(qū)域合作則相對更容易一些。
因此,結(jié)合中國現(xiàn)實(shí)本文得出的第二個研究假設(shè)如下:
假設(shè)2:中國經(jīng)濟(jì)水平差異較大的地區(qū)間合作程度更高,經(jīng)濟(jì)水平越接近的地區(qū)間越可能存在稅收競爭,且比地理相鄰的地區(qū)間的競爭更激烈。
不對稱稅收競爭模型最初的假設(shè)多是基于地區(qū)人口規(guī)模不同而進(jìn)行的,在不對稱稅收競爭模型中,主要做了以下幾方面假設(shè):地區(qū)之間非流動要素人口規(guī)模不同,其他方面完全相同;每個地區(qū)的人口數(shù)量保持穩(wěn)定;資本在地區(qū)之間完全流動;私人產(chǎn)品和公共品的消費(fèi)數(shù)量決定地區(qū)居民效用,其中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設(shè)f′(ki)為資本邊際產(chǎn)品,扣除稅后,f′(ki)-ti為資本在i地區(qū)的稅收凈回報,那么在轄區(qū)間稅收競爭達(dá)到均衡時的資本回報率就是r=f(k1)-t1=f(k2)-t2。其中t1和t2就是競爭轄區(qū)1和2在均衡時的稅率。當(dāng)增加轄區(qū)1的稅率時將導(dǎo)致資本從轄區(qū)1進(jìn)入轄區(qū)2,直到兩個轄區(qū)的資本稅收凈回報率相等時的兩轄區(qū)稅率為均衡稅率。結(jié)論是規(guī)模大的轄區(qū)設(shè)置較高的稅率導(dǎo)致資本外流,而這種外流程度相對小的轄區(qū)較輕,這是由于高稅率被資本化為資本稅收凈回報,因此規(guī)模大的轄區(qū)相對設(shè)置的稅率更高,而規(guī)模小的轄區(qū)由于受到正外部性的影響,有較強(qiáng)的動機(jī)降低稅率。
人口規(guī)模在一個地區(qū)的增長促進(jìn)勞動力要素形成空間集聚的同時,也對城市聚集發(fā)揮經(jīng)濟(jì)效應(yīng)奠定基礎(chǔ)。因?yàn)槌鞘腥丝谝?guī)模增長而形成的集聚經(jīng)濟(jì)主要是在城市化經(jīng)濟(jì)和地方化經(jīng)濟(jì)兩方面表現(xiàn)出來,地方化經(jīng)濟(jì)指的是產(chǎn)業(yè)發(fā)展形成的內(nèi)部規(guī)模經(jīng)濟(jì),原因是專業(yè)化分工提高了生產(chǎn)效率,勞動力市場共享降低了企業(yè)招聘成本和尋找勞動力的成本,同時在產(chǎn)業(yè)內(nèi)形成知識共享與溢出等。城市規(guī)模越大,同一產(chǎn)業(yè)的企業(yè)聚集越多,地方化經(jīng)濟(jì)越明顯。城市化經(jīng)濟(jì)指的是在產(chǎn)業(yè)間形成的規(guī)模經(jīng)濟(jì),主要表現(xiàn)在產(chǎn)業(yè)間協(xié)同與知識溢出,以及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經(jīng)濟(jì)性。城市人口規(guī)模越大,產(chǎn)業(yè)數(shù)目越多,城市化經(jīng)濟(jì)越顯著,人口聚集與經(jīng)濟(jì)要素集聚具有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作用;工業(yè)化發(fā)展具有要素集聚效應(yīng),工業(yè)集聚作為產(chǎn)業(yè)集聚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之一,發(fā)生在工業(yè)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整個過程,工業(yè)生產(chǎn)較少依賴地區(qū)的自然條件,容易形成規(guī)模經(jīng)濟(jì),具有正反饋?zhàn)饔茫虼斯I(yè)活動通常集中在具備優(yōu)勢條件的地區(qū),這些地區(qū)的交通便利并且自然資源相對豐富,從而形成最為顯著的空間集聚效應(yīng)。具體來看中國地區(qū)間工業(yè)化形成的集聚效應(yīng)更多來源于資本要素工業(yè)集約式發(fā)展,因此應(yīng)該重視和發(fā)揮資本集聚的正面功能[13]。
對外開放對稅收競爭的作用機(jī)制方面,已有研究建立空間集聚模型分析地區(qū)間經(jīng)濟(jì)對外開放對地區(qū)產(chǎn)業(yè)布局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在貿(mào)易成本逐漸下降的時候,產(chǎn)業(yè)在具有初步優(yōu)勢的地區(qū)形成集聚,然后通過累積循環(huán)機(jī)制形成中心外圍的制造業(yè)-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布局,這為后續(xù)的實(shí)證分析奠定基礎(chǔ)[14]。學(xué)者研究中國各地區(qū)的對外開放程度對產(chǎn)業(yè)集聚的促進(jìn)作用,認(rèn)為對外開放對產(chǎn)業(yè)集聚的促進(jìn)作用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擴(kuò)大出口市場規(guī)模放大本地市場效應(yīng)以實(shí)現(xiàn)規(guī)模經(jīng)濟(jì)和產(chǎn)業(yè)集聚,另一方面通過促進(jìn)資本積累,實(shí)現(xiàn)技術(shù)擴(kuò)散和創(chuàng)新,以推動產(chǎn)業(yè)集聚的形成,發(fā)揮累計循環(huán)機(jī)制的作用。從對外經(jīng)濟(jì)開放對促進(jìn)區(qū)域市場整合及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高的角度論證了對外開放有助于區(qū)域市場一體化的形成,實(shí)現(xiàn)產(chǎn)業(yè)集聚[15]。而產(chǎn)業(yè)集聚形成的集聚經(jīng)濟(jì)對地區(qū)稅負(fù)具有正向影響是以新經(jīng)濟(jì)地理學(xué)為基礎(chǔ)的,學(xué)者將新經(jīng)濟(jì)地理學(xué)與稅收競爭結(jié)合建立序貫博弈模型,認(rèn)為處于核心區(qū)的企業(yè)由于產(chǎn)業(yè)集聚形成集聚經(jīng)濟(jì),企業(yè)因此獲得集聚租,地方政府可以從集聚租中征稅,因此其提出假設(shè)認(rèn)為經(jīng)濟(jì)越發(fā)達(dá)的地區(qū)越可能成為稅收競爭中的領(lǐng)導(dǎo)者角色,保持較高稅負(fù),所以產(chǎn)業(yè)集聚的存在對稅負(fù)具有正向影響,有助于緩解競賽到底的稅收競爭,這已經(jīng)得到國內(nèi)外學(xué)者的論證,前述文獻(xiàn)綜述部分已有梳理。
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三個理論假設(shè):
假設(shè)3:人口規(guī)模、工業(yè)化、對外開放水平與地區(qū)稅負(fù)具有顯著正向相關(guān)性,主要通過促進(jìn)要素集聚形成集聚經(jīng)濟(jì)影響地區(qū)間稅收競爭中的稅收優(yōu)惠策略選擇。
三、模型構(gòu)建及變量說明
為檢驗(yàn)理論假設(shè)的有效性,本文將構(gòu)建動態(tài)的空間杜賓模型,建立地理和經(jīng)濟(jì)空間權(quán)重矩陣進(jìn)行模型估計與實(shí)證檢驗(yàn)。
(一)動態(tài)空間杜賓模型構(gòu)建

(1)

(2)

轄區(qū)i的福利水平ui依賴居民的私人消費(fèi)ci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gi,兩者依賴位于轄區(qū)i的資本要素的規(guī)模bi:
ui=u(ci(bi),gi(bi),Xi)
(3)
方程(3)中的Xi表示轄區(qū)的特征向量。將(1)引入(3)使其地區(qū)福利最大化,得出轄區(qū)i的最優(yōu)稅收政策,依據(jù)轄區(qū)的外生特征(Xi,Yi)和鄰居轄區(qū)的稅收政策,得到:
(4)
因此,通過估計簡化的反應(yīng)函數(shù)(4)檢驗(yàn)稅收競爭行為,通常情況下通過線性或者log線性形式表達(dá)如下:
(5)
其中,ρ0是常數(shù)項,ρx,ρy是參數(shù)向量,εi是隨機(jī)項,ρ1是標(biāo)量參數(shù),空間反應(yīng)函數(shù)的斜率(參數(shù)ρ1)可能是正值或者負(fù)值。稅收競爭理論認(rèn)為i省份在t年的稅率Ti,t是通過鄰居省份稅率決策而形成的反應(yīng)函數(shù),基于此考慮空間效應(yīng)構(gòu)建空間效應(yīng)模型,本部分使用空間杜賓模型進(jìn)行估計:
(6)
其中,i表示的是地區(qū)屬性,t表示的是時間,τi指的是衡量的稅率,Xi衡量的是外生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w是進(jìn)一步將討論的空間權(quán)重矩陣,λ,β,μ,θ,η,φ,ψ是估計的參數(shù),θ是估計矩陣,di是地區(qū)一系列固定效應(yīng),T是時間趨勢,εi是誤差項。β代表的是反映函數(shù)的斜率。w權(quán)重矩陣反應(yīng)每個“鄰居”[注]此處的“鄰居”指的是空間上設(shè)定的空間權(quán)重下的概念,不局限于傳統(tǒng)的地理相鄰,還包括經(jīng)濟(jì)權(quán)重下的經(jīng)濟(jì)水平相近的地區(qū)之間。稅率對本地區(qū)稅率的影響,基于本部分的理論分析,地方政府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相當(dāng)?shù)牡貐^(qū)展開更加激烈的競爭,以爭奪晉升位次,這個權(quán)重使用地理相鄰權(quán)重和經(jīng)濟(jì)相鄰權(quán)重來進(jìn)行衡量。
空間權(quán)重:空間地理權(quán)重,根據(jù)空間單元是否具有共同的邊界設(shè)定矩陣,如果具有共同的邊界相應(yīng)元素設(shè)為1,否則設(shè)為0,假設(shè)海南與廣東廣西相鄰;空間經(jīng)濟(jì)權(quán)重,依據(jù)省份人均產(chǎn)出水平的相近程度來設(shè)定,以地區(qū)實(shí)際人均GDP進(jìn)行考察。空間權(quán)重矩陣Wij=1/|pgdpi-pgdpj|,其中pgdpi和pgdpj分別表示樣本期內(nèi)i省份和j省份人均產(chǎn)出均值,考察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重要性。為消除數(shù)據(jù)的量綱影響,對權(quán)重矩陣進(jìn)行行和為1的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
(二)研究變量及數(shù)據(jù)來源
1.研究樣本。基于已有文獻(xiàn)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對稅收競爭的研究范疇為地方政府之間的橫向稅收競爭,在放松同質(zhì)性地方政府假設(shè)時,僅考察同一層級不同規(guī)模的地方政府行為。選用省級樣本作為本文研究樣本,省級地方政府可視為同一行政轄區(qū)的同一層級單位,由此研究得出的結(jié)論更符合本文關(guān)于橫向不對稱稅收競爭的研究目的,也更具有適用性。因此本文的研究樣本是除西藏、港澳臺外中國30個省級單位。本部分選擇樣本考察期為2002~2015年,選擇以2002年為研究樣本期開始的理由主要是∶2002年的企業(yè)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方案,在稅收征管方面做了較大變動,而稅收征管作為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的重要手段之一,2002年的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地方政府的稅收競爭程度,因此本文研究樣本時間以2002年為起始日期。這期間的企業(yè)所得稅征管范圍調(diào)整具有更強(qiáng)的外生性特征,因?yàn)樗侵醒胝?002年實(shí)施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時一次性規(guī)定的。
2.研究變量。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Ti,t: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的測算方法為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企業(yè)所得稅稅收收入/地區(qū)GDP,這種測量方法得到已有學(xué)者的認(rèn)可[16][17][18];人口規(guī)模lnpopi,t-1目的是為了捕捉地區(qū)人口規(guī)模效應(yīng),使用年末人口數(shù)取對數(shù);工業(yè)化水平lnindusti,t-1可以用來呈現(xiàn)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規(guī)模,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越高的地區(qū)規(guī)模也越大,使用非農(nóng)業(yè)GDP/農(nóng)業(yè)GDP后取對數(shù)表示[注]另外使用非農(nóng)業(yè)GDP/總GDP衡量工業(yè)化水平進(jìn)行穩(wěn)健性檢驗(yàn),檢驗(yàn)結(jié)果沒有顯著變化。;經(jīng)濟(jì)開放水平openi,t-1使用地區(qū)進(jìn)出口總額占地區(qū)GDP的比重來表示。
控制變量:人口結(jié)構(gòu)變量是一個省的人口學(xué)特征,這個特征可能影響地方政府的稅收政策偏好,使用少年兒童撫養(yǎng)比cdri,t-1和老年人口贍養(yǎng)比odri,t-1作為一個省人口學(xué)特征的代理變量。人口結(jié)構(gòu)因素是衡量一個地方社會因素通過影響地方政府的稅收政策偏好而對稅收決策產(chǎn)生影響進(jìn)而影響稅收競爭結(jié)果;轉(zhuǎn)移支付依存度transferi,t-1:財政分權(quán)以后稅權(quán)向中央集中,同時事權(quán)下移,導(dǎo)致中國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支出主要依賴轉(zhuǎn)移支付,轉(zhuǎn)移支付依存度的衡量用轉(zhuǎn)移支付總額(含稅收返還)在財政一般預(yù)算支出中占比多少來表示。

表1 描述性統(tǒng)計結(jié)果
表1中是測算的研究變量數(shù)據(jù)結(jié)果,從統(tǒng)計結(jié)果可以看出全樣本平均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為0.981,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均低于平均水平,而東部地區(qū)遠(yuǎn)高于平均水平,并且東部地區(qū)的平均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幾乎超過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平均值的兩倍,中部和西部地區(qū)的平均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相差不大。從工業(yè)化水平來看,東部地區(qū)以2.68的水平高于全樣本均值2.098,而中部地區(qū)和西部地區(qū)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西部地區(qū)略低于中部地區(qū)。從經(jīng)濟(jì)開放水平來看,東部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開放水平為0.736遠(yuǎn)高于全樣本平均0.338,中部和西部地區(qū)的開放水平相近,都遠(yuǎn)低于全樣本平均,未達(dá)到平均值的1/3。由此可見,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可能受到工業(yè)化水平與經(jīng)濟(jì)開放水平的正向影響。
標(biāo)準(zhǔn)差衡量的是一組樣本數(shù)據(jù)集圍繞平均值的離散程度,東部11個地區(qū)之間的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差異性遠(yuǎn)超過中部和西部地區(qū),中部和西部內(nèi)部地區(qū)間的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出現(xiàn)趨同現(xiàn)象,東部內(nèi)部地區(qū)之間的工業(yè)化水平差異性遠(yuǎn)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后者地區(qū)內(nèi)部的工業(yè)化水平出現(xiàn)趨同現(xiàn)象,經(jīng)濟(jì)開放水平也表現(xiàn)出與工業(yè)化水平相似的現(xiàn)象。結(jié)合稅收競爭理論,可能在經(jīng)濟(jì)水平相近的地區(qū)之間因?yàn)槿鄙俦容^優(yōu)勢,更容易產(chǎn)生為招商引資而競相降低稅負(fù)的逐底競爭,從而表現(xiàn)出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趨同現(xiàn)象。以上統(tǒng)計描述得到的結(jié)論僅是直觀推測,需要通過進(jìn)一步的實(shí)證檢驗(yàn)使結(jié)論更嚴(yán)謹(jǐn)。
四、估計結(jié)果及分析

對空間杜賓模型估計得到的結(jié)果如表2所示,Wald檢驗(yàn)和LR檢驗(yàn)結(jié)果認(rèn)為地理權(quán)重和經(jīng)濟(jì)權(quán)重下應(yīng)該在顯著性水平1%內(nèi)拒絕將模型簡化為空間誤差模型或空間滯后模型,因此無論是在地理權(quán)重還是經(jīng)濟(jì)權(quán)重下,空間杜賓模型均具有更好的擬合效果;Hausman檢驗(yàn)結(jié)果為固定效應(yīng)面板模型更合適,又根據(jù)對固定效應(yīng)模型的檢驗(yàn)認(rèn)為應(yīng)選擇時間個體均固定的固定效應(yīng)模型。鑒于此,本部分僅報告了偏差修正的雙固定效應(yīng)模型和動態(tài)固定效應(yīng)模型。

表2 模型估計結(jié)果
注:*、** 和*** 分別表示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
從表2中可以看出稅負(fù)的一階滯后項對稅負(fù)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說明稅收優(yōu)惠政策存在路徑依賴特征,因此在模型中加入稅負(fù)的時間滯后項是合理的,動態(tài)空間杜賓模型更符合現(xiàn)實(shí)情況。從動態(tài)空間模型估計結(jié)果來看地區(qū)間稅負(fù)的空間策略互動,在地理權(quán)重下稅收空間反應(yīng)系數(shù)為正值且顯著,這論證了假設(shè)命題1,即地理相鄰的地區(qū)間存在圍繞資本展開的稅收競爭,一個地區(qū)放松稅收征管或者提高稅收優(yōu)惠力度會導(dǎo)致地理相鄰的周邊地區(qū)也放松征管或調(diào)整優(yōu)惠政策以做回應(yīng),地理相鄰主要是鄰近省份之間由于資源等的趨同導(dǎo)致在吸引資本方面競爭力不具有明顯差距,主要依靠稅收優(yōu)惠作為競爭手段進(jìn)行招商引資,這就使政府對鄰接省份的稅收政策非常敏感。為探究中國地理相鄰的地區(qū)間稅負(fù)因?yàn)槎愂崭偁幊尸F(xiàn)的空間集聚特征,對2015年中國地區(qū)間稅負(fù)水平進(jìn)行全局空間自相關(guān)分析,觀察地區(qū)間以稅收優(yōu)惠為手段的稅收競爭行為特征。
本文測算空間Moran指數(shù)后得到稅負(fù)的空間集聚效應(yīng)。從2015年測算的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的地理上空間集聚效應(yīng)可以看出,除河北、北京、廣東外,中國的地區(qū)之間稅負(fù)呈現(xiàn)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分布,在地理相鄰的地區(qū)間存在稅收競爭。同時應(yīng)該注意到的是多數(shù)地區(qū)呈現(xiàn)出“低-低”集聚,可見中國目前超過2/3的地區(qū)可能處于稅負(fù)“逐底”的惡性稅收競爭中,而處于“高-高”集聚的地區(qū)有6個,可以看出這些地區(qū)均為沿海發(fā)達(dá)地區(qū),可能在這些地區(qū)存在的競爭優(yōu)勢緩解了競相降低稅負(fù)的競爭。處于“低-低”集聚中基本位于中國的東北部和中西部,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相對處于中低水平,結(jié)合測算出的各地區(qū)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結(jié)果來看,這些地區(qū)的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相對較低,而“低-低”集聚的特征說明其鄰接地區(qū)稅負(fù)也處于較低水平,地理相鄰的地區(qū)之間的稅收競爭傾向于“逐底”的空間競爭態(tài)勢。
在經(jīng)濟(jì)權(quán)重下稅負(fù)的空間反應(yīng)系數(shù)為正值且比地理權(quán)重下的系數(shù)更高更顯著,這論證了本文的假設(shè)命題2,即在經(jīng)濟(jì)權(quán)重下地區(qū)間存在稅收競爭,這是基于晉升錦標(biāo)機(jī)制下的地方官員晉升博弈理論,地方政府官員會為了晉升位次而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相近的地區(qū)之間展開競爭,由于涉及經(jīng)濟(jì)相近的地區(qū)間地方官員晉升位次的波動,因此競爭更加激烈。說明關(guān)于轄區(qū)不僅與地理鄰接地區(qū)競爭同時與遠(yuǎn)距離的非鄰接經(jīng)濟(jì)相近的地區(qū)之間競爭的結(jié)論在中國同樣適用。經(jīng)濟(jì)權(quán)重下的稅收競爭比地理相鄰地區(qū)間的競爭更激烈。從估計的系數(shù)結(jié)果來看,經(jīng)濟(jì)權(quán)重下的策略互動程度明顯高于地理權(quán)重,地理相鄰的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的反應(yīng)系數(shù)為0.174,經(jīng)濟(jì)相近的反應(yīng)系數(shù)為0.823,并且更顯著。相對于地理鄰接的競爭強(qiáng)度而言,經(jīng)濟(jì)實(shí)力越是接近的地區(qū)越不容易合作,這導(dǎo)致不同經(jīng)濟(jì)帶區(qū)域整合程度存在差異,也可以解釋為何京津地區(qū)的區(qū)域整合程度要低于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qū),經(jīng)濟(jì)實(shí)力越是接近的地區(qū)將越難合作,而發(fā)達(dá)地區(qū)與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的區(qū)域合作則相對更容易一些。
從稅收競爭的影響因素來看,在動態(tài)空間杜賓模型的估計結(jié)果中,人口規(guī)模、工業(yè)化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對地區(qū)稅負(fù)的影響均為顯著正向影響,均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yàn),并且在地理相鄰權(quán)重下的影響系數(shù)略高于經(jīng)濟(jì)權(quán)重下,這論證了假設(shè)命題3,說明一個地區(qū)人口規(guī)模、工業(yè)化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地區(qū)保持高稅負(fù),緩解逐底的惡性稅收競爭,這種緩解作用尤其對地理相鄰的地區(qū)間競爭更有效。這是可以解釋的,在地理相鄰的地區(qū)間進(jìn)行稅收競爭時更容易以稅收優(yōu)惠為主要籌碼吸引資本,而一個地區(qū)人口規(guī)模、工業(yè)化或者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必然形成除稅收優(yōu)惠外的相對競爭優(yōu)勢,改變單純依靠稅收優(yōu)惠進(jìn)行招商引資的競爭格局,從而使其保持較高稅負(fù)而不擔(dān)心資本外流。經(jīng)濟(jì)相近的地區(qū)間進(jìn)行稅收競爭,如果一個地區(qū)提高人口規(guī)模、工業(yè)化水平或者對外開放水平增強(qiáng)產(chǎn)業(yè)集聚產(chǎn)生相對于競爭者地區(qū)的競爭優(yōu)勢,然而地方官員注重對政治晉升位次的爭奪的稅收競爭更激烈,其在競爭中對競爭對手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和相對稅負(fù)水平仍然保持敏感,人口規(guī)模、工業(yè)化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因素對其影響程度相對弱于地理相鄰的地區(qū)間。
轉(zhuǎn)移支付依存度與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的關(guān)系為負(fù)相關(guān),但是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轉(zhuǎn)移支付依存度與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的關(guān)系并不明晰,一方面因?yàn)橐蕾囖D(zhuǎn)移支付進(jìn)行公共支出責(zé)任的履行,從而在財政自給方面有所放松,降低對企業(yè)所得稅征收的征管力度,又為了發(fā)展地區(qū)經(jīng)濟(jì),大幅度降低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以吸引資本,因此從這方面來說反而越依賴轉(zhuǎn)移支付越導(dǎo)致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的減少。另一方面依賴轉(zhuǎn)移支付越高的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較低,長期依賴轉(zhuǎn)移支付使中央對該地區(qū)提出提高財政收入的要求,導(dǎo)致該地區(qū)對企業(yè)所得稅稅收征管更嚴(yán),地區(qū)的企業(yè)所得稅實(shí)際稅負(fù)增加,因此從長期來看后者因素的干擾導(dǎo)致兩者的關(guān)系雖然為負(fù)但是不顯著;鄰居地區(qū)轉(zhuǎn)移支付依賴度越高,其對企業(yè)所得稅的稅負(fù)將降低,征管寬松,為提高吸引資本的競爭力,本地區(qū)只能進(jìn)一步降低稅率以參與競爭,導(dǎo)致地區(qū)間的惡性稅收競爭。人口結(jié)構(gòu)方面,少年兒童撫養(yǎng)比對稅負(fù)的影響為顯著負(fù)向影響,而老年贍養(yǎng)比則是正向影響但是不顯著,這與郭杰等(2009)[20]的研究結(jié)論一致。這表明地區(qū)的少年兒童撫養(yǎng)比越高,稅收優(yōu)惠力度越大,稅負(fù)水平越低,吸引資本的愿望更強(qiáng)烈,目的可能是通過優(yōu)惠稅率吸引企業(yè)在本地選址解決未來就業(yè)問題。
五、結(jié)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研究中國地區(qū)間以稅收優(yōu)惠為手段進(jìn)行招商引資的稅收競爭行為及其影響因素,基于不對稱稅收競爭理論以人口規(guī)模、工業(yè)化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作為競爭雙方的異質(zhì)屬性,結(jié)合已有理論提出三個假設(shè)命題。以2002~2015年中國除西藏、港澳臺外的30個省級政府為研究樣本,構(gòu)建動態(tài)空間杜賓模型,并在地理相鄰空間權(quán)重和經(jīng)濟(jì)相鄰空間權(quán)重下利用極大似然估計法得到估計結(jié)果,檢驗(yàn)本文的理論假設(shè),得出結(jié)論如下:地理相鄰的地區(qū)間存在稅收競爭,地區(qū)與周邊地區(qū)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具有顯著的正的空間相關(guān)性,多數(shù)地區(qū)的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表現(xiàn)為“低-低”集聚,形成逐底的惡性稅收競爭;經(jīng)濟(jì)相近的地區(qū)間存在稅收競爭,競爭程度比地理相鄰的地區(qū)間更激烈,經(jīng)濟(jì)越相近的地區(qū)間越不容易合作,難以實(shí)現(xiàn)有效的區(qū)域整合;人口規(guī)模增長、工業(yè)化發(fā)展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有助于形成產(chǎn)業(yè)集聚通過集聚經(jīng)濟(jì)使地區(qū)保持高稅負(fù),緩解逐底的惡性稅收競爭。
本研究對規(guī)范中國地區(qū)間不合理不合規(guī)的稅收優(yōu)惠行為具有重要意義,也為建設(shè)區(qū)域性中心城市在發(fā)揮其對惡性稅收競爭的緩解作用方面提供經(jīng)驗(yàn)證據(jù)。區(qū)域性中心城市建設(shè)的目的是在地區(qū)間培養(yǎng)區(qū)域發(fā)展的增長極,促進(jìn)其與區(qū)域之間的互動作用,發(fā)揮其對周邊的輻射效應(yīng),實(shí)現(xiàn)資源的有效配置。本文研究發(fā)現(xiàn)人口規(guī)模、工業(yè)化、對外開放的發(fā)展有助于形成產(chǎn)業(yè)集聚實(shí)現(xiàn)集聚經(jīng)濟(jì),對地區(qū)企業(yè)所得稅稅負(fù)具有促進(jìn)作用,有助于緩解逐底的稅收競爭。中心城市建設(shè)的發(fā)展有助于拉動這三個因素的提高,因此對緩解稅收競爭具有重要促進(jìn)作用。考慮到經(jīng)濟(jì)相近的地區(qū)間稅收競爭更加激烈,阻礙區(qū)域間整合導(dǎo)致資源浪費(fèi),為縮短區(qū)域整合的時間提高整合效率和質(zhì)量,應(yīng)注重整合的地區(qū)之間的經(jīng)濟(jì)水平差異性,帶動整體區(qū)域的經(jīng)濟(jì)增長和資源有效配置。在地區(qū)間建立中心城市正是有利于這種經(jīng)濟(jì)發(fā)展層次性的產(chǎn)生,對于進(jìn)一步的資源整合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