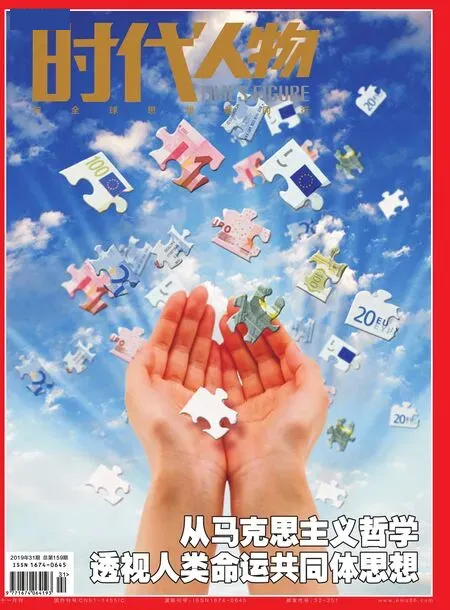女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進路再思考
——試用凱瑟琳·麥金農的法學方法論分析中國當下的女性生育困境
□文|鄭真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凱瑟琳·麥金農教授于1982年和1983年在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al and Society雜志上發表的兩篇姐妹篇論文《理論的議事日程》和《通向女性主義法理學》中,主要采用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階級分析工具來分析社會中的女性問題。這兩篇論文的最主要理論貢獻就是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價值理論運用到性別不平等的分析中,從而有力的發現了女性在社會中被歧視和被剝削的實質。這兩篇文章發表后在西方學術界的引用率非常高,麥金農教授本人也因此成為過去近二十年間北美地區女性主義最主要的學術領袖[1]。近年來,或許是受到后現代女性主義和批判種族主義女性主義的夾擊,麥金農教授的激進派女性主義觀點逐漸淡出了學術熱點。
雖然麥金農教授的激進女性主義若干政治主張已經不再是學術熱點,但她所采用的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女性社會現實的理論路徑仍然擁有巨大的學術意義,不應當隨麥金農教授的激進女性主義政治主張一同成為學術界的明日黃花。本文試圖將麥金農教授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價值分析的學術理路從她的激進女性主義政治主張中剝離開,并初步嘗試運用這個理論分析的路徑對我國當前女性在社會中遇到的最主要矛盾進行分析。
麥金農對于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解構與運用
女性問題是否是社會問題
“性之于女性主義如同勞動之于馬克思主義:最屬于本人的,卻也是被剝削的最徹底的。”這是麥金農教授在《理論的議事日程》一文的開篇之句,被列為麥金農的經典名言[2]。在麥金農教授看來,馬克思主義具有相當深厚基礎的理論,它的分析體系相當嚴密,與女性主義一樣都是關于權力及其分配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關于權力及其分配的理論,主要關注著這一過程中存在的不平等性問題。馬克思在批評資本主義的時候曾尖銳指出,那些認為價值和階級是自然形成的看法,以及把階級產生看做是自發形成的自然法則的理論,只是為了證明社會不公正現象的合理性。
然而,在分析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時,馬克思則“犯了與他所批評的人同樣的錯誤......即認為婦女天生地屬于社會生活給她們安排好的位置。”[3]既然是自發形成的,那么也就不存在不公正不合理。這正是麥金農教授對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時抨擊最猛烈的一點。
麥金農教授在著作中將《資本論》相關價值分析的理論概念與女性問題的概念做了一一比對,工作-性,工人-女性,資本家-男性,商品-性/女性,價值-女性的性吸引力,資本聚集-男性性欲,階層-性別,資金-性別/家庭,生產-生育,等等。當馬克思的權力對抗分析模式被運用到性別分析中,當資本家對勞動者的鉗制和剝削的關系界定被運用到分析男性對于女性的控制時,男性話語體系下隱形的問題便凸顯出來。
女性問題是否涵蓋女性共同利益體
在階級分析的理論中,勞動創造價值。馬克思發現了工業革命后無產階級被資產階級剝削的剩余價值,從而創立了剩余價值的學說。由此,無產者在工業化大生產中作為貢獻勞動力而同時被剝削剩余價值的群體,因為共同的遭遇和利益,形成了天然而強大的聯盟,具有自己的無產階級政治訴求。
同樣的,要想實現女性的解放,首要問題是發現女性在社會中具有共性的遭遇,提出女性所共同具有的利益,女性才可以是一個共同體,才能具備擁有共同的理論和共同政治訴求的前提。
而馬克思主義在女性問題這一點上的關注度與分析力度相比階級斗爭和剩余價值剝削的分析顯然是不足夠的。馬克思主義用男性的眼光來看待社會發展與階級矛盾,在其中卻忽視了女性的感受,沒有能夠在對社會制度的概括中給予女性以獨立的地位。克思主義中的女性總是被其他身份所概括,“馬克思主義的典型做法是用階級的概念來覆蓋女性群體”或者“除去階級的分類以及生理的事實,女性作為女性本身是完全不必考慮的”[4],比如作為工人的女性被稱為“女工”,并因此而被歸為工人。女性存在的價值在于向男性一樣創造價值。比如在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無產階級的女性比中產階級的女性更有價值、對社會作出了更多的貢獻,原因在于她們在工廠里象男性一樣的勞動。這種觀點看似賦予女性以價值,給與女性很高的評價,其實在忽視女性獨特性的同時,也再次張揚了一種男性價值觀。
發現女性集體利益并不容易,如何從跨越不同階級的女性中尋求共同的利益基礎,如何從跨越不同地域與文化的女性中尋找真正屬于女性的共同訴求,女性主義一直在做各種嘗試。
什么才是女性最根本的利益共同點
馬克思主義和麥金農教授的激進女性主義都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探討,但在當下看來,結論并不是很具有說服力。
在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這一問題被絕對化,從壓迫女性的一個極端走向了否定女性特質、強調男女絕對平等的另一個極端。女性為了尋求社會地位和社會價值,就必須走出家庭,走上工作崗位,通過參與社會勞動來體現價值,呼吁“女性能頂半邊天”,而家務勞動和女性的生育義務則有意無意被忽略了。
這樣的變革貌似取得了一些成效,女性的能力也可以在社會中嶄露頭角,但其實對于女性而言,著實是有苦難言的。雖然她們通過額外參與社會勞動創造的價值,獲得了回報和認可。但當她們在工作場所完成和男性一樣的勞動任務,回歸到家庭后,仍然需要肩負女性所特有的工作,比如家務勞動、生養后代,而這些工作依然不會獲得商業社會中的商品或者服務那樣可以量化的價值評價,她們因為身為女性而被剝削的情況并沒有任何改變。
在這一問題上,金農教授嘗試運用了意識覺醒(consciousness)的概念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女性主義者通過這種意識的分析來辨識男性主導的強烈影響,也就是說,通過這種分析來界定哪些社會現象是女性自身特點的反應,哪些社會現象是男性意識的強加。懇切地說,意識覺醒只是一個方法,賴以尋找女性共性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問題本身。
方法本身沒有問題,不過麥金農教授本人依據這一方法所找到的女性受壓迫的核心問題放在當下,卻差強人意。麥金農教授基于這種理論,分析而得出的結論是,“性成為了權力的一種形式。”男性與女性之間性別的差異是自然存在的,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一種權力體系正是性別壓迫的根本所在!“社會對異性性行為的需要,而這恰恰是男性的性統治和女性的性服從變得制度化了。”眾所周知,麥金農教授首先提出了性騷擾的概念,并為了反抗她所發現的男性對于女性的壓迫,花了很多精力分析色情文學問題,因為她認為,“在這種性權力之下的女性既沒有自己的思想,也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甚至女性對于性快感的概念都被偷換為男性對于興奮的需求。”
本文無意探討這兩個議題是否足以代表八十年代美國社會的女性所遭遇的最主要矛盾,但當下中國,女性所經歷的最普遍的、制度化的剝削,不在于此。本文第三部分將對此稍加展開討論。
兩個理論在分析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本文題為再思考,本意是對于對問題進行雙向的梳理,會同時關照到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以及麥金農教授的激進女性主義;既有延續麥金農教授對于馬克思的解構,也有對麥金農教授本人分析過程的批判繼承。
社會主要矛盾的無謂之爭
馬克主義與女性主義(非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都是關于權力以及分配的理論,因此二者之間具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同時也決定了他們之間矛盾的互不相容。其實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最根本的爭論在于階級壓迫與性別中間的壓迫何者才是社會的最基本矛盾。
馬克思主義認為女性主義將性別矛盾凌駕于階級矛盾之上,從而貶低了階級矛盾的重要性,也導致忽視了很多社會問題,低估了階級之間的利益沖突,從而造成自己理論上的疏漏。馬克思主義認為女性主義者們以及她們所組織的婦女運動其實僅僅代表了中產階級女性的利益,而并未將全體女性的利益納入考慮,比如無產階級婦女以及少數民族婦女。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女性主義其實是打著全體女性的旗號,而為中產階級的女性謀取集團利益,而實際上還是在為資產階級服務,而并未跳出階級界限。而女性主義者們所聲稱的能夠在資本主義內部完成所謂解放女性的任務,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眼中其實也是無法實現的,因為爭取中產階級女性的利益而忽視無產階級女性的利益實際上也是也種階級壓迫,是資產階級男性的“女人們”對于無產階級的“女人們”的壓迫。”[5]
麥金農教授承認女性主義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承與借鑒,但同時認為,女性主義應當取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而用自己的性別歧視理論來承擔起當代的社會矛盾分析任務。女性主義認為階級矛盾總試圖用階級的概念來涵蓋性別的概念,她們害怕馬克思主義為之所斗爭的利益并不是女性的利益,害怕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實踐中仍然會存在對于女性的歧視。
這兩種理論在社會根本矛盾問題上的爭論,并沒能產生更大學術價值。這種理論的對立過于強調事務的二元對立性,而忽略了之間的融合,而且是在用靜態的觀點去看問題,因而在應對和解釋社會現象的時候得出了偏離正常的結論。本文開篇便提出,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生活組織形式會不斷發生變化;同時,不同的社會會有不同的組織形式。這所有時間、空間的因素,都會對結論產生千絲萬縷的影響。社會的根本矛盾是階級矛盾還是性別矛盾,這不應當是理論之爭,而是由社會現實而決定的,而理論必須忠實于現實,而不可以本末倒置。最好的方法,就是將理論的基本分析原理加以運用,用以觀察和分析每個目標社會,而非將對某個社會的觀察結論當做通用的定律推廣適用到所有社會。
對女性受剝削根本原因的追溯不足
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追索差強人意。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女性的問題始終被概括于其它問題之下,而不被看作獨立的問題來尋求獨立的解釋。對女性問題的分析都從屬于對階級問題的分析,女性的獨立地位也在階級斗爭的框架下,隨著本階級的男性,被拆解到各自的階級中,因而女性問題再次回歸到階級斗爭中。例如,工人的概念被運用于分析從事工廠勞動的那一部分婦女,將她們稱之為“女工”,這樣,女性的概念被模糊了,而在分析勞動婦女的問題時,能夠套用馬克思主義關于工人的分析思路來解釋女工問題;女性所承擔的生育責任也被用“再生產”一詞來代替,因而對此的分析仍然落腳于勞動;女性與男性的對抗也被以理解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理解,但同時卻是比階級矛盾要低的一種次等社會矛盾。
在麥金農教授看來,要獲得女性的解放,一個單獨的努力是必要的。所謂單獨的努力就是專為女性解放而做出的努力,而不是借助于其他革命或改革而獲取女性的利益與福利。但她基于此主張而發現的女性最亟需改善的主要問題,現在讀來,總覺未撓到癢處。麥金農教授最引人注目的學術主張,除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繼承之外,便是她提出的性騷擾概念,以及在色情文學中女性的他者角色。我們無意去論證這些問題是否就是八十年代初美國社會女性最首要最根本的問題,但至少直接嫁接這個當年的熱點話題到當下的中國,怕是會嚴重水土不服。
所以,我們承認需要為獲得女性的解放而采取單獨的努力。以下一節,便是我們此次的初步努力。
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進路對當下中國現實問題進行分析
我們今日分析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和麥金農教授對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批判與繼承,不但是理論發展的需要,更具有現實的意義。其實自女性主義自產生之初,其對于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便大于純理論發展的訴求,始終致力于改善社會現狀。這一點也可以從女性主義三次浪潮中所關注的不同社會問題予以驗證。第一次浪潮指向公民權和政治權,包括反對一夫多妻制、家庭勞動與社會勞動等價、反對貴族特權等政治權利;第二次浪潮指向男女同工不同酬現象;第三次浪潮指向性更加多元化,通過全面識別父權意識形態和男權的視角,徹底消除女性被歧視的狀態。
生育問題是當下中國女性面臨的所有問題的核心
當代中國女性的社會現狀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如職場困局、弱勢的家庭地位等。在職場中,女性從最初錄用到干部選拔過程中都會受到區別對待,在于男性同等條件下,無法獲得更好的工作,在工作中無法得到平等的提拔和任用。[6]在家庭中,因為往往是收入較低的一方,在家庭事務中的議價能力低,無法在家庭決策中作出更有利于自己偏好的決策。在生育問題中,女性承擔全部的育兒成本及無償照料責任,導致家庭議價能力更低;且中國傳統價值觀仍然受傳宗接代、重男輕女等思想影響,導致女性在壓力下被迫選擇非理性多生育。[7]最極端的表現是販賣育齡婦女,女性僅僅因為擁有生育能力,便淪為嚴重刑事犯罪的受害人。
上述所有問題,核心都來自于女性所承擔的生殖繁衍人類后代的任務,以及社會對于這種任務的忽略。套用麥金農教授那句名言:“性之于女性主義如同勞動之于馬克思主義:最屬于本人的,卻也是被剝削的最徹底的。”此刻我們也可以借用這種說法:“生育子女之于女性主義如同勞動之于馬克思主義;最屬于本人的,卻也是被剝削的最徹底的。”
女性承擔了繁衍人類后代的重要任務,但卻恰恰因此而導致自身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的貶損,這是一個極其荒謬的狀態。具體來講,女性在職場錄用和選拔中會遭受區別對待。無論某個女性個體是否有生育的意愿,女性作為一個群體,需要承擔生殖繁衍后代的普遍責任。所以,在同等情況下,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創造的價值相對小于不承擔或較少承擔生育責任的男性,導致直接收入的減少,社會再分配過程中也并未充分考慮女性在生育中所創造的價值,而給與女性更多認可和回饋。經濟收入的損失導致了女性社會地位低下。另一方面,在家庭中,女性也并沒有因為承擔了生育義務而鞏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反而因為在勞動力市場難以獲得更高的薪酬和社會地位,無法為家庭創造更高的直接經濟收入,導致女性在家庭事務中的議價能力普遍偏低,無法通過自身能力確保在家庭決策中獲得平等對待。導致女性家庭地位低下。
需要全面重新評估生育行為的社會價值
對女性而言,生殖繁衍后代的義務與生俱來,其價值也因此至今被全人類社會所忽視。因為女性進入育齡期后生兒育女在全人類看來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如同陽光、空氣和水樣,是不可缺少卻又無處不在的。早在近兩百年前,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便指出,“生命的生產,無論是通過勞動而達到自己生命的生產,或是通過生育而達到他人生命的生產,就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8]
而長久以來,女性只具有生育的能力,卻無法選擇生育的自由,所以生育變成了一個如同陽光、空氣和水一樣可以供全人類社會(男性社會)無限攫取的資源。從避孕技術的不斷進步、到對禁止墮胎法律的解除,女性逐漸從被動的生育中解脫出來,可以自主選擇自己的生育,從技術上實現了女性的生育自由,生育不再是一個“無限量”供應的資源。逐漸,決定女性是否生育的不再是他人,而是女性自我的生育意愿。是否生育,如同是否進行社會勞動一樣,變成了一個待價而沽的選擇。
在此,我們需要引入政治經濟學中另一個概念——資源的稀缺性。資源的稀缺性是西方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如何在稀缺條件下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是經濟學的根本任務。當生育是一個“無限量”供應的資源時,不存在稀缺性。而當生育是一個根據社會價值(市場價值)進行判斷的選擇性行為時,就變成了具有市場價值的社會稀缺資源。
如果不能正確衡量“生命的生產”——即生育的社會價值,女性在生育中所創造的價值無法獲得正確的社會價值衡量,就會導致女性而放棄生育行為,轉而選擇其他更能夠創造社會價值的行為,于是才產生我國當下社會女性生育意愿下降的普遍現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社會的主流生育觀仍然停留在原有的社會認知。例如,我國婚姻法第十六條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作出這樣的條款規定,基于一個不言自明的事實判定,就是(女性)公民普遍具有生育的意愿。社會現實已如前所述有所改變,而法律內容卻仍然沒有相機而動,這次是法律滯后性的鮮明體現。重新認真考量女性生育問題在整個社會中的作用、稀缺性,是我們分析當下其他各種女性問題的依據和出發點。
注釋
原文"Sexuality is to feminism what work is to marxism:that which is most one's own, yet most taken away."Catharine A Mackinnon,“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Sighs: Journal Kate Sutherland, "Marx and MacKinnon: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Marxism for Feminist Legal "Science & Society,of Women in Cultural and Society, vol. 7(1982, no. 3).
Mackinnon, Catharine A.,“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521.
Mackinnon. Catharine A.,“Feminism. Marxism.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4, 1982, 517-18.
“城市的女性與男性平等接受教育已經不成問題,但是就業機會上拉開了距離,機會不平等,將來的干部選拔使用,距離更大,機會更不平等”。原文發表于見李慧英,2002中共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的“政府官員社會性別意識培訓手冊”,轉載于《現階段中國社會分化與性別分層》張宛麗《浙江學刊》2004年6期。
卡爾·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第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