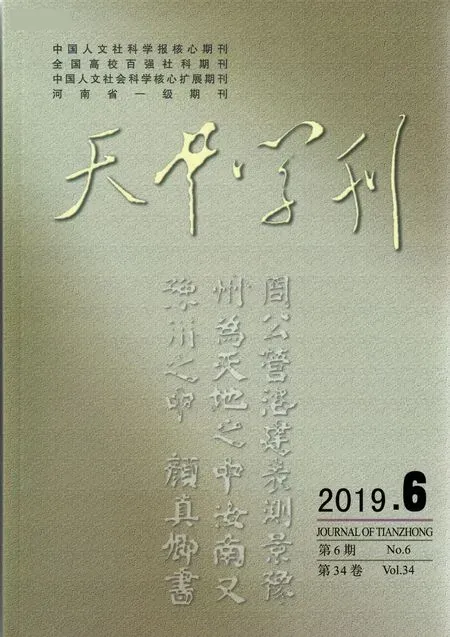《論語》“言教”思想的核心語義及其啟示
朱榮英,譚 琳
(1.河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開封475001;2.許昌市魏都區實驗學校,河南 許昌461000)
《論語》的言行觀教育即“言教”思想,可謂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如,強調君子應力戒空談浮言、非禮妄言,反對巧言令色、言過其實,主張慎言敏行、言信行果;認為當言則言、時而后言,懂得辟言、厲言,可從知言、慎言、辟言過渡到知仁、知命、安身,可從靜修之“言道”過渡到不言之身教,做到言行合一、踐言力行,如此等等[1]。本文詮釋《論語》“言教”思想的微言大義,對破解當代語言學中言與仁、言與信、言與行、言與默等一系列難題,以精美的藝術語言把握存在之真諦,頗具理論意義。
一、《論語》“言教”思想的核心語義
(一)君子應“知言”“慎言”“厲言”“放言”
孔子認為,“與師言之道”,也就是“相師之道”(《論語》季氏第四十二),君子出言吐詞要合乎言道,有序有禮,特別注重對弟子及大眾進行言傳身教、仁德感化。孔子主張君子立身處世要懂得“言教”禮數,具體要做到:“知命”“知禮”“知言”。如果不懂得對“命”和“禮”的默而知之、自我把握,當然就不能安身立命、建功立業;而如果不能“知言”,不善緘言,即不善于分辨和把握人們言談的技巧與時機,就“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第三)。為何憑“知言”就可“知人”呢?這是因為,“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從一句話中就可以弄明白這個人的智慧與否,因而“言不可不慎也”(《論語》子張第二十五)。君子之言,既要“言中倫,行中慮”,即言談話語要遵循社會倫理,符合世道人心,也要懂得有時應該沉默寡言,“隱居放言”(《論語》微子第八),即過隱居生活,收斂自己,莫談時事。真正的君子之言,不僅要謹言慎行而且要“厲言”“厲己”,話語嚴正而精當。“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論語》子張第九)君子講話時,要莊重威嚴、和藹可親,言語深沉而富有魄力。當然,除遵循“言教”外,君子也要善行不言之教、述而不作。譬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第十九),上天以其風生水起、日夜循環的各種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降神圣之諭。對此,君子雖然言不能及,但應畏天畏命,“畏圣人之言”,而小人肆無忌憚,做不到這一點,常常“侮圣人之言”(《論語》季氏第八),失口猖言,遭人詬病。
(二)君子應“以言踐仁”“行修言道”
因天人合一、言行不二,故而盡心、知性可知天,知言、踐言而知人,行修言道、踐仁知天。易言之,人在說話,話也在說人。所以《禮記》上說:“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2]君子要淡泊功名利祿,不語怪力亂神,不言稼穡捕獵等鄙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第一),少談論財貨與利祿,多贊頌天命與仁德。儒家認為“立言”即是“言仁”,“學仁”才可近道,而循序至精謂之學、受之于師謂之傳、三省吾身謂之悟,此三者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言教”之本[3]。如何“言仁”“學仁”呢?言在利仁、其言若拙,言行一致、質樸無華。相反,若花言巧語、工于辭令,則“鮮矣仁”(《論語》學而第三);若心口不一、空談浮言,則違于仁。孔子一向恥巧言、倡訥言,認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治長第二十五)。對此朱熹注曰,君子傳習仁道、講究“言教”,應力戒以言代行、妄滕口說,應“好其言,善其色,致飾于外,務以說人”[4]。若“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論語》陽貨第十四),不假思索、直言不諱,就會遠離仁德;君子“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第十三),不學習詩詞禮法,就不要空發言論,而要言必有理,言必有據,出言有章,放言得體。
(三)君子應“言而有信”,以誠立身
孔子主張,君子“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第七),言語要恪守信用、一言九鼎,人而無信,豈能立身行事?君子之言,要“言善信”,信不足則言不行,貴言事隨、希言取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5]。“主忠信”(《論語》學而第八),必須“言必信,行必果”(《論語》子路第二十),謹遵“言教”、安仁利仁,這是孔門“言教”之要旨,也是修身立德之根本。對于察人、知人,不能“聽其言而信其行”,而要“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治長第十),言顧行、行顧言,言行不二,言揚行舉。人“無信不立”,但“信”不是盲目的愚信,不是遠離仁心的偏信,而是傳習仁義的篤信,“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行恭敬誠信,即使是到了蠻貊荒野之地,仁道也行得通;“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靈公第六),若言行相悖、自食其言,即使是在本鄉本土也不能“踐言”行世。而那種“言思忠,事思敬”(《論語》季氏第十),言語誠懇、嘉言善行,因“信近于義”,其“言可復也”(《論語》學而第十三)。朱熹批注說,“言可復”就是說其言不虛,言近于禮,能夠以行“踐言”,言亦可宗,遠離恥辱,安身立命。從謹遵禮制之“言教”過渡到言之可復的身教,以身作則,言行相稱,君子有所不言,言必切當,有所不為,為必志成。若是那些語言上的君子、行動上的矮子,勢必一事無成。故而,君子要言出必行,以行踐言,談言微中,言芳行潔[6]。
(四)君子還要訥言敏行、言信行直
君子“言前定則不跲”,三思后行,敏學訥言則行事無不順。衣食住行,無非是隨遇而安、素位而行,要重視聞道樂行、閎言崇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學而第十四)。“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第二十四),不能口不擇言、行不副言,要善于以禮義來匡正自己的言行,力行其言,說到做到,不能徒托空言、吞言咽理。君子還應“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第十三),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要言出必行,以行踐言,勿輕易允諾、輕言寡信。孔子告誡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第二十二),以不能踐言為恥,不能兌現其言,悖言亂辭、言與心違、言不顧行、言不及行,就會言多傷行,成為無稽之談。所以,“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第二十七)。若“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論語》憲問第二十),大言不慚、言之過甚,必失信于人,處處為難。若身居高位,更要“多聞闕疑、慎言其余”,這樣就能夠“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為政第十八)。要多聞多見、隱而不言、言信行果,就會減少過錯。
(五)君子要“以言見禮”、德言容功
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強調“以言見禮”,善于察言觀行、恬淡少語,認為君子要善于“辟言”(《論語》憲問第三十七),躲避難聽的話,因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鄉黨第二)。言談舉止,一言一行,舉手投足,都要符合“言教”的規定,在不同的場合,方言矩行、情見乎言、合乎禮制。善言者,因人而言。如:在同鄉人面前,言語要溫和謙恭,表現出不善言談的模樣,“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在宗廟祭祀或者面見君臣時,要表現出既善于辭令,又健談而慎言的樣子,“便便言,唯謹爾”(《論語》鄉黨第一)。每當上朝,與同僚或下屬講話時,要溫和持重、從容不迫、不卑不亢、理直氣壯。“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地位較高的上級官員談話,要和顏悅色、中正誠懇,“與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在君主面前言語,要恭恭敬敬、謹慎小心,“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論語》鄉黨第二)。在經過國君的座位時,要臉色莊重,腳步加快,出言慎重,顯得中氣不足的樣子,“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論語》鄉黨第四)。在進食或休息的時候不要言談,“食不語,寢不言”(《論語》鄉黨第十)。而到了太廟,每時每刻都詢問禮義以顯誠敬之心,“入太廟,每事問”(《論語》鄉黨第二十一);在車中,也要按禮行事,不要高談闊論,“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論語》鄉黨第二十六)。對舊的禮法,雖然非常熟悉,也要有一種求實態度,因資料有限、不足為憑,“吾能言之”而“不足征之”;若文獻足夠,則“吾能征之”(《論語》八佾第九),等等。
(六)君子注重“時而后言”,言行相顧
孔子講究言而有道、言而有禮,不能口無遮攔、胡言亂語,特別強調“時而后言”“義而后取”,認為若“時而后言,人不厭其言”(《論語》憲問第十三),輪到自己發言,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人們不會厭煩。要“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即使是天長日久,也要信守諾言、仁義當先。朋友之間的好言相勸,即使是肺腑之言,也要講究言談技巧,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也”(《論語》顏淵第二十三),若多口多舌、詭言浮說,就會自取其辱、徒增煩惱。要善于觀察人言談時的特殊表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論語》顏淵第二十),就會聞達天下、言行相符。孔子認為“君子之言”與“小人之言”有別,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切切偲偲,怡怡如也”(《論語》子路第二十八),良言近仁,言必有中,小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論語》衛靈公第十七),閑言閑語,不著邊際。君子“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憲問第三),小人多言數窮,“巧言亂德”(《論語》衛靈公第二十七),“詞不達意”“過而不改”。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第二十三)”,可與之言則言,不可與之言則不言,就“不失人,亦不失言”(《論語》衛靈公第八)。若“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論語》季氏第六),不當言則言,就是浮躁;當言不言,就是隱言、失言;貿然而言,就是瞎了眼的失禮妄言。
(七)君子強調“名正言順”,言默自如
對于言什么、如何言的問題,君子還要謹記“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論語》公治長第二十一)。有道時則盡顯才智,一般人可做到;木訥裝愚,是常人學不到的。君子懂得審時度勢,言默自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7]。唯君子能善行言道、言而有度,言與不言、言什么、如何言,皆中規中矩,合于禮法,深諳人間睿智、“言教”之妙。君子學以致用、言行合一,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若紙上談兵、溢于言表,不切事理、言之無文,雖言之鑿鑿,又有何用呢?“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第五)孔子特別強調君子應該“名正言順”,認為這是從政之要,“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一事無成必然就會“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第三)。所以,君子必須重視正名與正言,不能妄言非議,不能和盤托出,“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論語》子路第三),君子需要一個值得稱道的正當名分,更要把握一種立得住、講得通、用得上的“言教”之道。怎樣才能避免以言賣禍、言多必失?孔子說,“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論語》子路第三)。君子之所以講究言道,主張規訓言談、出言有法,是由于“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喪邦”(《論語》子路第十五)。這樣說雖然有些言過其實,“言不可以若是”,但歷史上的確頻發因一言不當而導致興衰的事。君子要言不煩,寡而實;小人巧言如簧,多而虛。君子之言,言而有宗,確能一言興邦,一言濟世;小人之言,僭而無征,言悖而出,亦悖而入。
二、《論語》“言教”思想的當代啟示
顯然,語言是用來表達思想感情的,尋聲定墨,立意運斤,這是《論語》“言教”思想的根本旨趣。子曰:“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第四十一)語言只要能夠傳情達意、表達流暢、通曉易懂就行了,不必刻意追究文思奇巧與字句艷麗。若一味滯留于字句的凝練與潤色上,刻意追求“拍案叫絕”“語不驚人死不休”那樣的效果,就會成為字句的奴隸,死于古人的句下,甚至會陷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的窘境。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第十八)文采與質樸必須妙合無垠,不能流于粗俗,也不能虛偽浮夸。劉勰在其《文心雕龍》中認為,“立文之本源”在于,“以文附質”“以質待文”,喪言不文、正言不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君子常言,未嘗質也”,“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8]330。但是,語言之“達”,又有上下之分、雅俗之別。“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論語》憲問第二十三),積極向上、日進高明為“上達”,沉淪平庸、日究污言為“下達”。君子“上達”要通于雅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第十八)。“雅言”也就是“正言”,讀詩書禮義,注先王經典,必正言其音,謹言表達。真正切當的、無傾向性的藝術語言,猶如“一種神話”[9],巧妙而藝術地運用語言,在匠心獨運、反復斟酌下,就會達到文思神遠,視通萬里,字字珠璣,吐納珠玉,言為心聲,神與物游。語言呈現是“一種生命的形式”[10],要反復錘煉,“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8]338,務求“以一字為工”,這種“煉”“是往活處煉,非往死處煉也”[11]111,妙筆生花,盡顯生命之美,情動言外,隱含文理神韻。古人詩句中雖不言高遠靜閑、灑掃應對,而在文中卻能以少總多、萬取一收;對于景外之意、韻外之致、味外之旨,不事雕琢確能活靈活現、自然貼切,可謂文之精華,有隱有秀;言不在多,盡得風流。
《論語》倡導的“言教”,還有另外一種含義,即著書立說,以言行世,“出‘言’如‘筆’,‘筆’為‘言’使”[8]413,因字生句,聯句成章,積章成篇,連篇為著,表面看似乎是一種文字游戲,實質上表達的卻是人的內在神韻、風骨情志,揭示的是一種有深度的思想,語言就是思想表達本身。易言之,語言本身是思想的直接現實,語言是一種現實的思想,是能夠被人直接感受到的思想。馬克思說,“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12],它所呈現的不僅僅是僵死的外在符號而是生命的深度即“靈魂的深度”[13]35。以理論的方式把握世界,須借助嫻熟巧妙的語言藝術。理性語言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用語,是一種驚艷妙心的學術語言,具有自己特殊的性質與方法,最能體現人的自由自覺活動,黑格爾講它是“訴之于心靈”[13]44并“經過心靈化”[13]49的東西。列寧說,決不能“機械劃一,強求一律”,“在這個領域里是最來不得公式主義的”[14]。藝術地運用語言去駕馭思想,必須推敲文字、凝練語義。古人早就說過,“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詩改一字,界判人天”。而創造性地使用語言藝術,更要重視合理表達那些突然涌現在意識內的東西,“惟陳言之務去”,摒棄一切文法理障,“不涉理路,不落言荃”,“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才能在吟詠性情的微妙處,顯得“透徹玲瓏”,“言有盡而意無窮”。用最明確的科學術語來表達最真切的思想,確能深入揭示人的心理過程及其發展規律,學術語言的這種修辭方法“就是心靈的辯證法”。當然,我們不應該為了觀念的東西特別是語言上的東西,而忘掉現實主義的東西,學術語言所表達的都是具有真情實感的東西,語言藝術說到底是生活的藝術,學術話語所表達的都是人民的思想,要做到“心既托聲于言,言亦寄形于字”,屬意為文、心與筆謀,趣幽旨深、內明外潤,“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還要做到以“言教”蕩滌世人渾濁之心,提振民族精神,凈化人的心靈,開闊人的視界,“納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于圣賢,此救人道于亂世之大權也”[15]。
現代西方哲學中有所謂“語言學轉向”之說,論述的是語言所具有的本體論意義或存在論功能,強調語言作為思想交流的手段不僅能夠指涉事物、傳達思想,更能開顯世界之本體與存在之真諦,甚至能夠構造物質世界和人的存在的多種可能性意義。存在主義者認為,世界就是語言所及的世界,世界就寓于語言之中,而人的存在意義也是語言所構造的,語言是存在的家,唯有借助那種詩意的言說才能揭示人的本真之在。中國古代哲學也重視語言的工具妙用,從言與物、言與意、言與道的關系上看,語言不僅具有指涉作用,可“言之有物”“直言其事”,而且能夠傳達思想、言說道理,可“言以表意”“辭以達意”。但中西哲學也都談到了語言的局限性問題。的的確確,語言有時也會束縛思想,窒息靈性,會抵達那種言不盡意、詞不達意,不可說、不能說的地步。對那些在語言之外的、不可說、說不出的“非言之在”“不驗之詞”“不思之說”,西方哲學強調“沉默是金,語言是銀”,認為能說的就要說清楚,不能說的就要懸置語言。唯有在語言的破碎處,隱秘的存在才真正開敞,唯有在語言休息時,真正的哲學才開始了言說。所以,語言只能說那些可說的,不可說的就不要說,“說不可說”非語言所能及,只能依靠非理性的臨界體驗即“畏、煩、死”的內在啟示,或者借助類似于中國古典詩詞的超越想象、詩意傳達,或者干脆依靠神的召喚,才能聆聽到那些神秘之在所傳達的靈異之音等。西方的這種語言觀與中國儒學“反巧言”“倡訥言”的“言教”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古代哲學也認為語言不是萬能的,人們常常需要借助“非言”的物指、神諭、棒喝、敲擊,去體悟那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因“言不盡意”之故,才“立象盡意”“得意忘言”;由“正言若反”“大辯若訥”,才主張“寄言出意”“得意忘荃”;因“言語道斷”“思維路絕”,才強調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直指心體、默然心會。筆者認為,古代先賢憂之也深、言之也切,“文思極則奇,極深而研幾”,那么言與非言的界限如何把握,“言”與“默”的矛盾該如何處置,如何“以意新而得巧,憑理趣而顯奇”[16]?細究《論語》關于“言教”思想的核心要義,對破解這一難題或許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