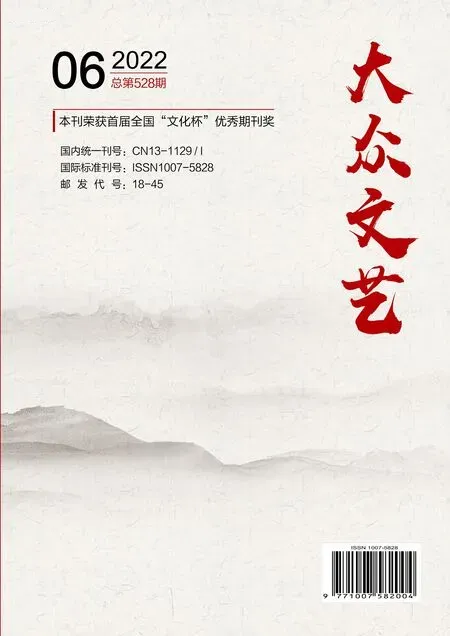試析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創(chuàng)作中的形式構(gòu)成問題
(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博士 100029)
新時期初始,再一次的西學(xué)之風(fēng)席卷美術(shù)界,“徐蔣體系”1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樣式跌下神壇,不再一枝獨(dú)秀。在經(jīng)歷了一段彷徨徘徊之后,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家吸收形式構(gòu)成等西方現(xiàn)代繪畫語言和理論以適應(yīng)當(dāng)代新文化語境,使寫實(shí)水墨煥發(fā)新的生機(jī)。
早在20世紀(jì)初林風(fēng)眠就將形式構(gòu)成理論應(yīng)用于中國畫,但由于新中國成立后的文藝政策等多方面原因,這種“中西融合”的方式受到了較大的限制。而將形式構(gòu)成系統(tǒng)地引入中國畫創(chuàng)作實(shí)踐與教學(xué)體系的是盧沉。盧沉作為新時期中國畫革新派的杰出代表,將西方現(xiàn)代繪畫語言與理論體系引入水墨人物畫創(chuàng)作與教學(xué)實(shí)踐,并在中央美院開設(shè)了“水墨構(gòu)成課”,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這對于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的突破與發(fā)展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形式構(gòu)成引入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無疑對增強(qiáng)畫面視覺張力和感染力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為藝術(shù)家擺脫刻板描摹、充分發(fā)揮主體的能動性、探索個性化的形式語言提供了巨大空間。但同時還要看到,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實(shí)踐中對于形式構(gòu)成理論的應(yīng)用,具有很大的矛盾和問題需要面對和解決。
形式構(gòu)成引入中國畫語言體系,仍然是“中西融合”的問題,“中西融合”是20世紀(jì)繪畫史的重要語匯,這一命題一定是建立在外來繪畫語言系統(tǒng)和價值體系的侵入和固有語言系統(tǒng)和價值體系的消解之上。“把中西兩種繪畫形式語言融和為一,經(jīng)常會使探索者步入進(jìn)退維谷之境。形式語言與欣賞習(xí)慣連在一起,又與相應(yīng)的內(nèi)涵和文化結(jié)構(gòu)不可分。如何融和而不是拼合,如何選擇與棄取,如何與內(nèi)在的統(tǒng)一性相符,實(shí)是極困難的事。”2此外,形式構(gòu)成引入水墨畫,在以筆墨語言為主、本就強(qiáng)調(diào)形式趣味的山水、花鳥畫中或許更容易找到契合點(diǎn),但在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中應(yīng)用這種抽象性的語言,問題就會十分復(fù)雜。
深入到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的內(nèi)部語言系統(tǒng),造型與筆墨的矛盾和兼容持續(xù)了近一個世紀(jì),直至今日仍然是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創(chuàng)作中不可回避的問題,而在這一系統(tǒng)中引入形式構(gòu)成這一新的西方繪畫語匯,面對寫實(shí)、寫意、抽象等諸多異質(zhì)的命題,勢必帶來更為復(fù)雜的問題。
首先,抽象的形式構(gòu)成與寫實(shí)的造型語言本就具有矛盾,寫實(shí)造型是一種再現(xiàn)性語言,強(qiáng)調(diào)的是客觀物象的具象表達(dá),而形式構(gòu)成是一種表現(xiàn)性或抽象性語言,強(qiáng)調(diào)的是形式規(guī)律的體現(xiàn)和藝術(shù)家主觀的表達(dá),兩種語言的表現(xiàn)方式和價值標(biāo)準(zhǔn)的不同直接構(gòu)成了二者的對立與兼容的難度。實(shí)踐過程中必須需要一個將寫實(shí)的物象造型經(jīng)由藝術(shù)家主觀地加工、組合、排列,以契合整體的形式結(jié)構(gòu)的過程,但其中如何能夠兼顧個體物象的具象再現(xiàn)和整體的抽象形式結(jié)構(gòu),如何能夠做到真正的融合而不是拼合,是實(shí)踐中十分復(fù)雜和困難的問題。
其次,源于西方現(xiàn)代繪畫的形式構(gòu)成語言與中國畫傳統(tǒng)筆墨語言構(gòu)成了更為復(fù)雜的矛盾,筆墨強(qiáng)調(diào)書寫性與寫意性,其與寫實(shí)造型本就已經(jīng)構(gòu)成了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正所謂“蓋畫至人物輒欲窮似,則筆法不暇計也。”3,而下筆之時不僅需要考慮造型,還要考慮畫面整體的形式結(jié)構(gòu),筆墨則會更不“不暇計”。更為重要是,構(gòu)成與筆墨的矛盾其背后是中西方繪畫價值體系的異質(zhì),正如盧沉所說:“對筆墨趣味,已深入到品茶一樣的程度,而這與現(xiàn)代欣賞趣味有差別,現(xiàn)代趣味不求微妙過渡,而注意整體結(jié)構(gòu),黑白、色彩之強(qiáng)烈對比,這其中有很大矛盾需要我們?nèi)パ芯浚ヌ剿鳌!?。強(qiáng)調(diào)筆墨韻致會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弱畫面的整體構(gòu)成性,而過于強(qiáng)調(diào)構(gòu)成就有使筆墨淪為純粹形式要素的風(fēng)險。如何使作品兼顧整體的畫面形式感而又不失筆墨趣味,這就更需要藝術(shù)家兼顧深厚的傳統(tǒng)筆墨素養(yǎng)和駕馭整體畫面的能力。
新時期以來,眾多藝術(shù)家歷經(jīng)幾十年的消化吸收,形式構(gòu)成逐漸合理地內(nèi)化于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語言之中。80年代,周思聰、方增先、楊力舟、王迎春等藝術(shù)家初步將形式構(gòu)成原理用于水墨人物畫實(shí)踐,使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的面貌為之大變。周思聰?shù)摹兜V工圖》率先進(jìn)行了形式構(gòu)成引入水墨人物畫的探索,畫面打破了過去情節(jié)敘事的固定模式,運(yùn)用重復(fù)、透疊、拼貼等手段,將不同時空的物象并置在畫面之中,同時運(yùn)用黑白灰構(gòu)成原理營造了壓抑、扭曲的視覺感受,與苦難的民族歷史相契合;方增先作為浙派人物畫的代表人物,1983年調(diào)入上海圖畫院后接觸到大量西方現(xiàn)代繪畫的信息,繪畫風(fēng)格面貌隨之改變,1984年創(chuàng)作的《帳篷里的笑聲》巧妙利用幾何形狀的概括將諸多物象整合起來,兼顧形式意味與酣暢淋漓的筆墨趣味;楊力舟、王迎春夫婦的《太行鐵壁》用滿構(gòu)圖的形式使太行山占據(jù)整個畫面,運(yùn)用象征的手法,將軍民百姓融入畫面的整體形式分割之中,筆墨也策略性地采用側(cè)鋒皴擦的形式,使畫面具有紀(jì)念碑式的崇高感。
90年代,趙奇、李伯安、劉國輝等藝術(shù)家將形式構(gòu)成逐漸內(nèi)化于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固有的語言體系,實(shí)現(xiàn)進(jìn)一步的兼容而不過度顯露于外。趙奇1994年創(chuàng)作的《京張鐵路》將眾多人物進(jìn)行了大體面的概括,呈現(xiàn)了一種平面化、幾何形化的轉(zhuǎn)換,運(yùn)用刀劈斧鑿般的線條和巧妙的黑白灰處理,將筆墨、造型與畫面整體的形式構(gòu)成統(tǒng)一起來,用獨(dú)特地方式營造出宏大壯闊的場面;李伯安的史詩巨作《走出巴顏喀拉》第二部分《開光大典》創(chuàng)作于1991至1995年,這一巨幅畫面將人物膚色與寬袍大袖的衣著加強(qiáng)了黑白對比使得整體效果氣勢恢宏,同時從《八十一神仙卷》中獲得啟發(fā),將傳統(tǒng)的線描技法與畫面整體的構(gòu)成結(jié)合起來,營造出一種 “天衣飛揚(yáng)、滿壁風(fēng)動”的視覺效果;劉國輝作于1998年的《三秦父老》基于傳統(tǒng)的筆墨語匯,通過筆線的穿插關(guān)系、墨色的濃淡干濕,將形式構(gòu)成暗含于筆墨語言表現(xiàn)之中,既充分表達(dá)了傳統(tǒng)的筆墨韻致,又使畫面富有形式趣味。
新世紀(jì)以來,袁武、趙建成、陳玉銘等藝術(shù)家體現(xiàn)出更多個性化的嘗試,使形式構(gòu)成更加自然地成為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形式語言的一部分。袁武2004年作品《抗聯(lián)組畫》對筆墨與造型進(jìn)行了大膽的提煉、整合,運(yùn)用濃重的墨色將人物造型整合成大的團(tuán)塊,同時將這些物象整合成點(diǎn)線面的抽象形式因素,合理的布置安排在畫面之中,使畫面具有渾厚的分量感與視覺沖擊力;趙建成2004年作品《西部放歌——靈光》首先將畫面進(jìn)行分割并進(jìn)行黑白布局,并將光影、體積、轉(zhuǎn)折巧妙地轉(zhuǎn)化為黑白構(gòu)成,筆墨語言隨之轉(zhuǎn)變?yōu)槠矫嫘缘臉?gòu)成要素,使畫面具有一種光影陸離的形式美感;陳玉銘在駕馭大場面巨幅創(chuàng)作方面具有超強(qiáng)的能力,2009年作品《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運(yùn)用了近乎版畫語言的黑白灰布置,將現(xiàn)實(shí)縱深空間轉(zhuǎn)化為畫面平面空間,尤其是對于布白的處理獨(dú)具匠心,使畫面富有視覺沖擊力又靈動自然。
在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中融入形式構(gòu)成,經(jīng)過眾多藝術(shù)家?guī)资甑奶剿鲗?shí)踐,其脈絡(luò)逐漸清晰。形式構(gòu)成引入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不可忽視其中的矛盾與問題。不論是20世紀(jì)初寫實(shí)造型的引入,還是新時期形式構(gòu)成的引入,其本質(zhì)都是外部繪畫語言系統(tǒng)與中國人物畫本土語言系統(tǒng)的沖突與兼容,外部語言的侵入是否會帶來固有語言與價值體系的缺失,或者說“中西”之間到底能不能兼容,這些問題是自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誕生以來就面對的問題。在當(dāng)下水墨人物畫多元發(fā)展的語境中,能否“兼容”或許早已不是問題,而如何“兼容”無疑是當(dāng)下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家思考的問題。筆墨與造型的兼容,以及形式構(gòu)成的兼容等“中西融合”命題還會延續(xù)下去,其中的矛盾和問題更是需要更多個性化的解決方案,仍具有寬闊的研究空間和實(shí)踐空間,需要的無疑是藝術(shù)家更加全面的文化修養(yǎng)、杰出的藝術(shù)智慧以及高超的藝術(shù)技巧。
注釋:
1.“徐蔣”即指徐悲鴻、蔣兆和。1993年劉驍純在《論蔣兆和》一文中首先提出“徐蔣系統(tǒng)”之說,即徐、蔣二人所倡導(dǎo)、發(fā)展的寫實(shí)水墨人物畫體系。(載《中國畫研究·蔣兆和研究專集》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1年版).
2.郎紹君.《創(chuàng)造新的審美結(jié)構(gòu)——林風(fēng)眠對繪畫形式語言的探索》,《文藝研究》,1990年第2期.
3.文徵明,《衡山論畫人物》,載俞劍華編《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頁.
4.盧沉、劉繼潮整理《盧沉論水墨畫》,安徽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