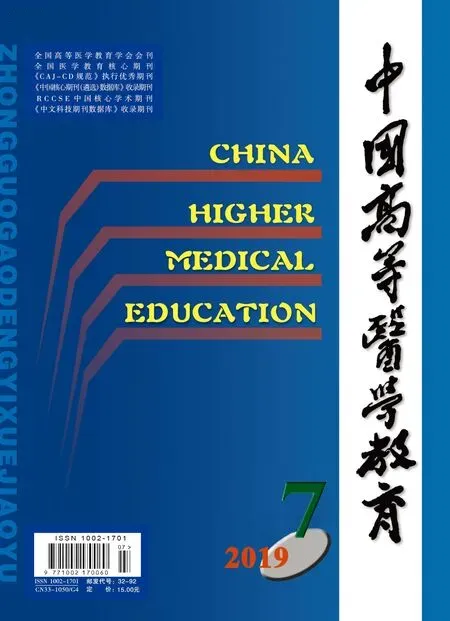我國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四證合一”培養模式的探討
李 成,應令雯,周 健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六人民醫院,上海 200223)
2015年5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布了《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指導性培養方案》,并全面啟動了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實行與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并軌培養,即通常所說的“四證合一”[1]。
具體而言,“四證合一”指的是臨床醫學專業型碩士在學習專業知識的同時,參加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合格畢業生在獲得畢業證和學位證的同時,獲得執業醫師資格證和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合格證書。該方案以臨床實踐能力培養為重點,在所選三級學科基礎上,加強了各科臨床知識技能的學習。臨床輪轉和階段考核能夠不斷加強與鞏固專業型碩士的實踐操作能力,帶教老師的指導和交流能夠使醫患溝通技巧的學習具體化,由此,該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專業知識的學習以及實踐能力的培養,然而實施過程中亦發現存在一定問題。本文對“四證合一”培養模式存在的問題、建議與思考等進行了探討,以期為“四證合一”培養模式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思路。
一、“四證合一”培養模式中存在的問題
(一)規范化培訓基地臨床教學質量參差不齊。
首先,醫療資源的不均衡導致各規范化培訓基地臨床教學質量參差不齊。2014年發布的《國家衛生計生委辦公廳關于開展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基地認定工作的通知》有關部署,第一批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基地總數達450個。其中,廣東以40個培訓基地位居第一,北京和上海分別有28家和24家醫院,而在醫療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區,如寧夏、西藏等地,規范化培訓基地只有2家。醫療資源的不均衡導致一部分地區的臨床醫學專業型碩士能夠進行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地點選擇少,相對于資源豐富的地區,病人數量、病種等方面相差較大,學生在培訓過程中得到的實踐與鍛煉也會不同。其次,由于規范化培訓仍在初始階段,部分臨床帶教老師帶教意識不強,甚至出現只讓學生管病人卻缺乏“教學”的現象,這與“四證合一”的初衷不符,對學生的培養和成長也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二)專業型碩士臨床科研能力培養投入時間不足。
在“四證合一”培養模式下,專業型碩士需要進行超過33個月的科室輪轉才能拿到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合格證書。與此同時,學習期間能夠發表學術論文,獨立完成畢業論文,拿到畢業證和學位證,則是對專業型碩士臨床科研能力的要求。在這一點上,許多醫學院校都開設了相關課程,培養學生的臨床研究思維,如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為專業型碩士開設有醫學統計學、臨床研究導論等課程。但事實上,繁重的科室學習以及臨床任務,導致許多學生都未能安排好臨床研究學習時間,無法形成一個較好的臨床研究思維體系。這是臨床醫學專業型碩士學習過程中普遍存在并亟需解決的一個問題。
(三)輪轉制和導師制之間不協調。
由于內外科三級學科劃分較細,臨床輪轉過程中,專業型碩士在三級學科科室的學習時間并不長,這使得學生在其他科室輪轉的時間內,并未能夠與導師保持緊密的溝通,從而導致其對于所選專業的專業知識、臨床技能僅僅是一個“囫圇吞棗”式的學習,這一問題在內外科大類中尤為突出。一項由大連醫科大學開展的調查研究顯示,參與調查在校臨床醫學專業型碩士(n= 200)中,54.3%的學生認為跟隨導師的學習時間不足,導師忽略了對其“研究”能力和思維的指導[2]。由此看來,輪轉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導師制的作用,限制了專業型碩士對所選三級學科的深入學習,這也是在“四證合一”培養模式逐漸成熟的過程中需要完善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四證合一”培養模式建議與思考
(一)完善帶教制度,提高臨床教學質量。
“四證合一”培養模式下,專業型碩士畢業后是否能夠達到獨立行醫的基本要求與輪轉過程中臨床教學的質量緊密相關。在這一點上,我國醫療資源的不均衡所導致的差距在短時間內無法改變,仍需要長時間的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但是,在臨床帶教老師這一方面,各個培訓基地應按照政策要求,發揮主觀能動性,制定相關制度,規范帶教過程,保證教學質量。
首先,對于臨床帶教老師,基地可組織統一培訓,明確在帶教過程中需要傳授給學生的專業知識、臨床技能等,讓帶教老師能夠有的放矢。第二,在組織帶教老師培訓的同時,基地應每隔一段時間(如半年)對帶教老師進行考核,雙向測評的過程能夠使學生和老師共同成長。第三,對帶教老師應進行適當補貼,并對于考核、測評優秀的帶教老師給予獎勵,提高帶教老師的積極性。
(二) 加強臨床科研思維訓練,強調導師制的重要性。
奠定臨床技能基礎是第一步,進一步要培養的則是專業型碩士對于臨床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的研究與思考能力。嚴軍英等[3]認為“四證合一”培養模式要求專業型碩士在畢業時既要達到獨立行醫的基本要求,成為“會看病”的醫生,同時能夠結合實踐提出思考與見解,成為“會研究”的醫生。要達到這樣高的水平,勢必對于培養方式提出更多的要求。
首先,臨床醫學專業型碩士提前入學,集中學習臨床研究相關基礎課程。侯晉軒等[4]認為在強調科研思路與臨床實踐的有機結合的同時,應該注重循證醫學思維培訓,加強臨床試驗知識的學習,并強調醫學統計學的重要性。學生有了一定知識基礎之后,才能更好地在輪轉過程中將研究與實踐相結合。第二,在已有課程基礎上優化課程體系。醫學院校、培訓基地在輪轉過程中,為學生開設系統性臨床研究課程,貫穿整個輪轉過程,并結合互聯網,開設不同類型的課程,加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同時,可開辦高水平講座,拓寬專業型碩士的視野,并鼓勵其參加學術會議。第三,強調導師制的重要性。在保證輪轉時間和質量的前提下,適當調整各個科室的輪轉時間,延長在專業型碩士所選三級學科學習的時間,現今,各個醫學院校在實踐中也已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如導師組制度[5]、雙導師制[6]等,不僅僅在學生的臨床技能學習方面起到監督的作用,在臨床研究學習方面也起到了引導作用。
“四證合一”培養模式的目標不僅是讓專業型碩士會看病,同時也要培養學生對于臨床問題思考和研究的意識,這并不是過分強調科研、發論文的重要性,而這是“研究生”的培養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三)“四證合一”培養模式的一點思考。
曾任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院長的沈曉明教授曾指出我國醫學教育體系學制的混亂,而“四證合一”培養模式的改革使“七年制”已經取消,可以說是醫學教育體系學制的規范的第一步。殷峻[7]通過我國與國外醫學教育體系的對比提出了統一學位、學制的建議。在英國,五年制畢業后學生將獲得醫學學士、外科學士學位,六年制畢業后學生可同時獲得文學士或理學士;美國的醫學教育一般在本科之后開始,學制為四年,畢業后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總體而言,國外的醫學教育學制時間長,學位較統一,對于醫學生的培養有較為成熟的體系和規范,值得學習和借鑒。
不可否認,“四證合一”的培養模式實現了專業型碩士研究生教育與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有機結合,為臨床培養了一批專業的應用型人才,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醫療資源緊張的壓力。但同樣,在其實踐過程中,依然存在著需要各方繼續努力解決的問題,不斷提高臨床教學質量,優化培養體系,才能更好的推進“四證合一”培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