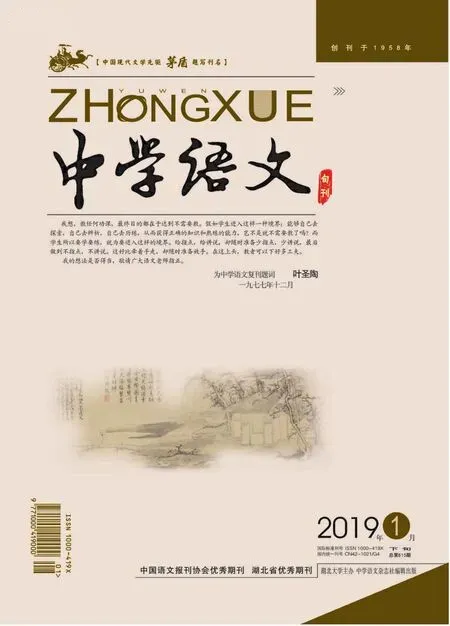《記承天寺夜游》的文化底蘊探尋
孫雅融
婉約凄清的文字,像“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像“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哪怕是春花爛漫陽光普照之時,信手拈來讀過,也總覺得幾分凄涼涌上心頭,彌久不散。但凡蘇軾這樣的文字,都讓人有一種渺茫的痛感,似乎這樣我們可以更清醒地看待人生的多變與缺憾。可就在邂逅林語堂先生所著的《蘇東坡傳》后,我驀然發現,語文課堂上呈現的蘇軾,讓學生學到的蘇軾其實更應契合于東坡那快樂明亮的笑容,那慈仁純真的心境,那渾然天成的文字,那卓然于世的風骨。
一、陌上花開為君顧——與明月對話
中國古典詩詞意象中,出現頻率最多的是“月”。明月既是自然的明月,又是文化的明月。關于明月,蘇軾還有“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記承天寺夜游》中,蘇軾解衣欲睡,因月色入戶,而欣然起行。作為文化意象、文化基因的“明月”一直傳承至今,沒有中斷過。這就是中國人特有的精神現象和心理特征。一提起它,自然要思鄉懷人,循著這樣一條情感邏輯線,《記承天寺夜游》的月色之美的分析便有章可循。月色是醉的,情境是美的,自然,情感的曲線變化隨著月的推移,而清晰可表。這一意象,又有月背后的情感寄托,體會“閑”中清閑賞月的意境。其實,還有諸如此類的很多意象,“風”“花”“雪”“柳”“雁”“橋” ……在文言文教學中,充分抓住特定含義的意象,帶著學生層層解讀,不失為體會感知文章情感的好辦法。
從這個意義上講,文言文的教學是一種文化的傳承。儒家講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文言文的教學,需尋找文化的根基。馮友蘭先生曾在其后加了一句:“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也許,這樣的境界,確實是一個理想,對于語文教學的潛心鉆研,實在是接下來要不斷走下去的道路。
時光推著齒輪碾過,這一片天地,花開又謝,已不知多少輪回;人來又去,恍惚間已過了萬代。東坡本人早已消散于時光的洪流之中,但他的靈魂,卻如同一縷虹光,照亮著一輩又一輩的后來者。正如林語堂在結語中寫道:“在讀《蘇東坡傳》時,我們一直在追隨觀察一個具有偉大思想、偉大心靈的偉人生活,這種思想與心靈,不過在這個人世間偶然呈形,曇花一現而已。蘇東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個記憶。但是他留給我們的,是他那心靈的喜悅,是他那思想的快樂,這才是萬古不朽的”。
二、向青草更深處漫溯
翻開文言文的單元,不禁讓人想起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文學史上誕生的“尋根文學”,因為從他們身上,我們多多少少都可以找尋深植于民族傳統文化中那絲絲縷縷的源頭和痕跡。正如王君老師曾經說過:“學習文言文,可以讓我們找到回家的路。”
中華民族的文化源遠流長,古文詩詞的數量浩如煙海,對古文進行詞法句法的精講細解,是腳踏實地地踐行讀誦,落實文言文基礎知識的必須環節,對于文言文的教學,要達到讓學生“多角度、深層次品味意蘊豐富的文言文”的效果,更有必要用文化的底蘊,支撐課堂的顏色,這樣,我們和學生才能一起漫步在獨具韻味的古文之路上。
每一個人都是一本書,一個故事。《記承天寺夜游》這篇文言文要贈予學生的,也遠遠超乎想象。生命是剎那芳華,可以多姿多彩地活過。人之一生,最重要的就是過程。蘇東坡不做作,愛恨明于心即顯于形;是非功過,但憑后人蓋棺論定。而接受知識的十幾歲的孩子們,慢慢懂得珍惜生活、用心活過每一刻便好。“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是東坡的行文之道,亦為他的處世之道。他并非不省而游樂,而是知天下、憂天下卻樂天下。這種胸懷與氣魄源自他對生命的尊敬。他做的是自己,而不是別人眼中,別人口中的什么人。這份氣勢,怕需要我與學生們相遇了這樣的人,寫出的這樣的文才可以如此震撼罷。
一篇課文,一個文本,一個人物,一節語文課堂,都需要文化的浸潤。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觀念,不同于西方主客二分的文化意識,更講求物我兩相融。漢字就是傳遞自然指征、表達人文情感表意文字的例子。同樣,對于《記承天寺夜游》這樣一篇文言文,沒有從深度的維度品讀蘇東坡這樣一個人,沒有從文化的廣度探索中國古典文獻中特定意象的文化內涵,我們就不能更真實地走近文本、更深刻地解讀文本。蘇軾自提“閑人”的理解,林語堂先生洋洋灑灑的《蘇東坡傳》。文言文的魅力,不僅僅在于文言知識的扎實落實,還能在其營造的遼闊意境中,讓學生輕觸從古至今萬千靈動的真實生命,關注這個細膩溫潤的世界,走出自己的一片星空。
《記承天寺夜游》中蘇軾的“閑”,便不難理解。作者的“閑”是“清閑”以及月色不期而至的快樂;是作者與朋友漫步的悠“閑”,以及朋友相知之樂;是體會賞月時的陶醉以及賞月時的意外之樂;作者于困境中的“閑”情,以及自我排遣,豁達之樂。在這樣悠閑的漫步中,正是在這樣安閑寧靜欣賞月光澄澈的夜晚,也正是這個胸懷大志卻被閑置一隅的文學偉人,選擇了承天寺,夜游,并留下這膾炙人口的名作。